文/刘龙
“谁将引领中国艺术的新方向?”这是在伦敦海沃德(Hayward)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变化的艺术——来自中国的新方向”所希望回答的问题。
背景
本次展览的主办方海沃德美术馆在伦敦向来以学术性和挑战性而闻名。在此之前,他们刚举办了一场名为“看不见的艺术”的展览引起了伦敦观众的颇高关注。这回首次试水中国当代艺术,就以“变化”、“新方向”这样的具有挑逗性和指向性的词语来为展览命名,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观众对公共美术馆的兴趣点,另一方面足见海沃德美术馆对此次展览的学术性所抱有的期待和野心。
近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热,曾有许多国外的画廊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但因缺乏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深入了解,展览质量参差不齐,针对性和学术性薄弱,多给人以大拼盘的众生相之感。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8年10月英国著名当代艺术收藏家查尔斯•萨奇在伦敦切尔西萨奇新画廊举办的“革命在继续:来自中国的新艺术”,展览邀请到包括张晓刚、方力钧、曾梵志在内的24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创下了52.5万人次的参观记录。
而此次“变化的艺术”区别于其它海外展览的关键在于展览摆脱了以往海外对中国固定的符号化认知,在严谨的学术梳理过程中关注到了隐藏在市场明星们身后的艺术瑰宝——曾经不被官方认可,很多只能活跃在地下的行为和装置艺术。经过美术馆和策展人长期对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梳理和考察,最终选择以装置和行为艺术的不同阶段转折的变化关系为切入点,并邀请了在各个阶段最具深度和代表性的行为与装置艺术家参与此次展览。
九位艺术家——陈箴、段英梅、顾德新、梁绍基、孙原/彭禹、汪建伟、徐震、没顶公司被选为此次“来自中国的新方向”,展览现场囊括了他们各自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最具影响力的装置和行为作品。沿着艺术家的创作轨迹,可以感受艺术家创作关注方向的逐步变化。而各自不同的变化也汇聚成此次展览的主题——“变化的艺术”。围绕“变化”这一古老东方哲学,展览将转化、不稳定性及非连续通过不同材质和表现方式的作品淋漓尽致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现场
你是否有被跟踪过的经历?并且是那种如影随形却又若即若离的古怪的跟踪?如果没有,当你走入海沃德美术馆时最好做足心理准备,因为将有一个沉默不语,面无表情的人等在门口与你一同进入展厅。不管你是厌恶、恐惧或是愤怒,这些拒绝任何沟通,身着中国精神病人服装的人都会正大光明地跟踪你,不在乎你的感受。然后,当你醉心于展览作品,渐渐习惯他的存在时,他又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离开。此时你会作何感想?松一口气?高兴?还是难过?怅然若失?这是徐震在本次展览上的新作品《March6》所表达的,作品继承了徐震一贯的讽刺、诙谐的风格,且隐含一定的政治寓意。
徐震的另一件作品《只要一瞬间》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一位站立者身体倾斜,似乎马上就要跌倒,但却又像被凝固般一动不动。尽管可以猜出这个幻觉的产生靠的是靠藏在衣服中托住这些站立者的金属支架。但这件作品依然可以让观众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产生一种焦虑感。人们需要作出这个一瞬间的决定。这些作品中的人会站立起来还是会跌倒呢?亦或者他们将永远以这种方式凝固在那里。瞬间的抉择、快速的情感体验成为了解徐震艺术的关键。
长期旅德的艺术家段英梅的作品则在情感冲突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行为过程中的能量传递。爬过美术馆墙上的一个小洞,你便会看到段英梅的行为作品《快乐的英梅》。艺术家蜷缩在一个树桩上,周围尽是光秃秃的树枝和满地的枯叶,她嘴上哼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无言曲调“La,la,la,la;oo-oo-oo-ooo”。随后,当她发现你的注视后,她会光脚踩着枯叶,笑着向你走来,并递给你一些纸条,上面可能会写有诸如:“你知道留守儿童吗?”或者“你是否发现一些以前的熟人现在已经非常陌生?”等信息。面对如此诡异的状况,你应如何面对?是应该笑着跟她交谈,还是摇摇头走开?这场表演将你带到这里,并让你无法抵抗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段英梅1969年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大庆市,小时候的她因为腭裂受到了许多人的嘲笑。她的艺术是一种在不真正开口的情况下进行的表演艺术,而她的“说服力”也正是依靠这种深刻的无言状态,她让观众变成参与者,从瞬间的体验和临场反应中体会此间的情感和力量。
中国的行为艺术历史不长,直至八五时期的厦门达达出现才初见端倪。在1989年中国政治局势紧绷的局面下,八九现代艺术大展中出现了具有政治挑衅意味的行为作品,导致此后行为艺术被明令禁止,从而逐渐成为远离官方艺术机构的地下艺术。但这种政治的高压也催生了艺术家们更为激烈、更有创造性的抗力。他们不再只关注艺术品最终成形的是否是一个完整的结果,而是专注于实验的过程。如同策展人StephanieRosenthal在采访中所谈到的:“在中国这个艺术急速发展的国度,行为和装置艺术常常是引发艺术变化的开端。他们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而我对艺术作品形成的过程非常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作品常常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有些甚至背离艺术家最初的构想,但因此也可能会产生许多令人惊喜的杰作。”
另一组动人的现场作品来自梁绍基。他将蚕丝附着于物体的表面,用柔滑、纯洁的蚕丝包裹铁链、椅子、石头、老窗等毫无生机的物体。甚至还邀请人们倾听蚕咀嚼和吐丝过程中的声响。全部作品中的蚕都是活体,观众在观看的同时,作品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蚕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含义,不仅自身象征着轮回新生,还与丝绸之路,“残”、“禅”等传统文明符号有深刻关联。梁绍基说:“我把养蚕的过程当做参禅的过程,我所有作品的核心就是时间与生命的流动性,时间不停流逝,生命也在成长、轮回中不断变得更强,蚕丝赋予没有生机的物体以生命的希望,有一种轮回的意志蕴含其中。”
变化是一切创新的前提,穷则变,变则通。从参展艺术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不同于上几代中国艺术家的思维特质、艺术方向和创造性。艺术对于他们不再是教条式的关于“艺术”的定义,而是一种机智的视觉思考。艺术创作也不再是工作室里的闭门造车,而是关于组织、融合不同境界的力量所进行的纠结于现实政治和平凡生活的思想探索与实践。同时也是他们认知世界的疆域,探寻自我生命建设与艺术的关系的现场。通过工作他们试图弥合一些艺术之间的对立,同时搅动生活,在变化中寻求突破,开创一种新的局面。
争议
极具噱头的命题为“变化的艺术——来自中国的新方向”带来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对西方观众而言,中西文化、社会、思维间的巨大差异,让他们想要深入了解这些作品变得不那么容易。《theartsdesk》的SarahKent评论指出这场展览令他难以琢磨。他在报道中写道:“可以参考的东西太少了,尽管徐震的作品《只需要一瞬间》是不言自明的,但其他作品还是需要阐释,信息的缺乏可能会挫伤观众去了解其中一些重要展品的积极性。”《卫报》LauraCumming的评论也强调了这样一种距离感,她认为只有陈箴的贫穷艺术作品具有强烈西方风格,几乎其他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次新的邂逅。
现场观众的反应,也体现出艺术接受过程中的阻碍。比如一些观众对徐震的作品《饥饿的苏丹》,彭禹和孙原的《文明柱》作品表示难以接受。因为前者涉及到艺术作品对儿童的使用以及儿童权益;后者涉及到对人体脂肪的使用。另有一些观众则认为展出作品与西方流行的艺术形式过于相似,难以看出中国艺术的特色何在。
而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则给出了更为猛烈的批评,他于9月10日在英国《卫报》上评论该展览为:“我不认为‘新方向’在中国艺术当前的语境中是值得讨论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出现旧的方向,中国艺术也从未有过明确的方向。而且,像这样一个没有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怎么能称之为中国当代艺术展?我非常熟悉这些人的作品,他们的确来自中国,但这就好比中国城的餐馆卖宫保鸡丁和咕噜肉,虽然食客知道这是中国菜,但仅仅是消费主义时代一个标准化的产物。无法借此理解当今真正的中国生活。”
面对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参展艺术家之一的汪建伟表示:“我从不去思考西方观众或东方观众的问题,因为所有来看展览的人都是同样的观众,我从不追问他们的性别和文化。而且我认为这种差异很正常的,差异就是现存的,是基础。但我也不想过度强化这个差异,强化这个差异并把它虚构成问题去获利,其本质是很腐败的。试图用差异来获得利益的任何事情,都是想在政治上获得一种正确性。而且有些时候,作为艺术家思考的问题,不能陷入简单的社会正义里去。”
结语
“变化的艺术——来自中国的新方向”比较集中地呈现这些装置和行为艺术家的思想动机和创作状态,他们的艺术也许并不是要观众同意什么,而是让观众分享他们的情绪、经验和思维模式,进而共同探讨在今天的现实中,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如何思考被称为“艺术”的事情。他们所构思的关于“知识分子”及“介入”社会的主张,如何能在当下的艺术实践中展现出不一样的形态?中国艺术展里的中国何在?中国艺术家如何在“本土”和“国际”这个长期困扰着艺术创作的语境中,从艺术史、艺术界的影响的惯性中,实现一种创新的可能性?在市场力量出现松动的节点,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又进入了如大家所期待的又一个新的转型期?这可能是此次展览在定义“中国艺术新方向”的基础上更想探索的深层次问题。

![借《赵飞燕玉印》谈文物真伪评定[图文] 借《赵飞燕玉印》谈文物真伪评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l13qiqavhj.webp)
![康良河:从银幕背后走向台前的书法家[图文] 康良河:从银幕背后走向台前的书法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mwita4frgt.webp)
![文物修复:为历史缀补碎片[图文] 文物修复:为历史缀补碎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ffhubqxm3e.webp)
![退步与荒废:陈丹青的绘画[图文] 退步与荒废:陈丹青的绘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pxpiqdbdq3.webp)
![王隽语:闲来无事话夜白[图文] 王隽语:闲来无事话夜白[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lvx5hnpnde.webp)
![当代艺术如何品牌化[图文] 当代艺术如何品牌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pwm2diw4yp.webp)
![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图文] 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kmt1vfewnn.webp)
![刘洪郡:相对中的笔墨[图文] 刘洪郡:相对中的笔墨[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dedt1csxoe.webp)
![谁是艺术家?[图文] 谁是艺术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5vdu2ccxjs.webp)
![李叔同和西画东来[图文] 李叔同和西画东来[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vuejt1w54e.webp)
![著名油画家张万东[图文] 著名油画家张万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lkxpk5dml5.webp)
![英国大学博物馆状况:精英性与公共性的博弈[图文] 英国大学博物馆状况:精英性与公共性的博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x0c2zbpaal.webp)
![评论:文化传播,要肯下笨工夫[图文] 评论:文化传播,要肯下笨工夫[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1yeh0ljvt5.webp)
![谭平:时间——我的创作方法[图文] 谭平:时间——我的创作方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ucbwqipydt.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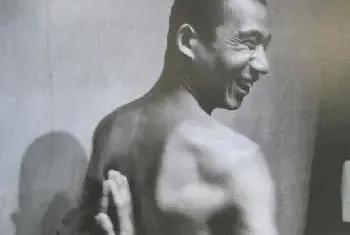
![青花居士收藏杂谈:关于收藏的“胡说八道”[图文] 青花居士收藏杂谈:关于收藏的“胡说八道”[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z2gsbumpya.webp)
![崔岫闻:大于艺术的是什么[图文] 崔岫闻:大于艺术的是什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s1m5yaf5pa.webp)

![展览为何日趋乏味平庸[图文] 展览为何日趋乏味平庸[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naa30tdfv3.webp)
![溯源法古 独树一帜开新篇——记感应书法和梦幻画风创始人宋草人[图文] 溯源法古 独树一帜开新篇——记感应书法和梦幻画风创始人宋草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a3z0jomhfm.webp)
![荷由心生——读韩志冰先生的水墨画[图文] 荷由心生——读韩志冰先生的水墨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hoxrsod3aj.webp)
![玉雕的变革:从金蝉奖的设立看蒋喜的创新之思[图文] 玉雕的变革:从金蝉奖的设立看蒋喜的创新之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cmch4fzu1u.webp)
!["地下"文物应不应合法化?[图文] "地下"文物应不应合法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wapisuzg5y.webp)
![对上海博物馆藏赵佶书《千字文》的质疑[图文] 对上海博物馆藏赵佶书《千字文》的质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v4meau0fd4.webp)
![文革时山水画怎样画:画成壮丽山河[图文] 文革时山水画怎样画:画成壮丽山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mxsfy3zfpy.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