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自我组织并不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个新现象。文革后的各种画会,’85时期的各种艺术群体,90年代开始的实验艺术团体、艺术家的自营空间与自主的展览实践,2000年以来的各种非盈利空间的尝试,这些都可以纳入自我组织的概念下,甚至还可以包括“画家村”与“艺术区”。[1]
但严格地说,“自我组织”一词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第一次使用是2005年的广州三年展,展览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做“自我组织”的单元,并安排了两场以“艺术的‘自我组织’”为主题的讨论。“自我组织”被描述为“一些存在于传统的艺术体制之外的艺术组织、艺术机构、艺术社区”,而参与这个单元的有机构,小组,也有各种性质的艺术区。[2]
不过“自我组织”的话题并没有在随后深入下去,在艺术市场异常繁荣的2006、2007这两年,当代艺术圈更关心的话题是拍卖价格、市场操作,以及对这种异常现象的怀疑与批评。直到2010年,“自我组织”这个概念才真正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关注与讨论,主要是一些年轻的艺术评论人与艺术媒体开始用这个概念来提示2008年以来各地广泛出现的,尤其以相对年轻的艺术家为主的群体实践。
这些笼统地叫做自我组织的群体实践,可以分为四种形态,或者说,可以用四种理想类型来观察不同的自我组织群体:艺术群落、艺术小组、独立项目与自主机构。艺术群落如绿校、N12和北村独立工场,艺术家之间有着艺术理念上的基本认同,但又没有到合作创作作品的程度,他们更多是基于某个网络社区空间或现实展览场所,或者自然形成的地缘与人缘关系来形成日常交流与组织集体展览,艺术家个体都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艺术实践。
艺术小组则要更进一步,小组内的成员共同创作作品,成为了一个创作主体。但不同小组内部的合作紧密程度以及艺术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又有区别,如双飞、GUEST小组的成员在集体创作的同时依然保持着个体的艺术家身份,而TOF小组、乌托邦小组、细胞小组的艺术家则只以小组的名义参加展览活动,更为极端的是和谐巴洛克,他们有意地匿名,彻底切断了艺术家个体与小组集体之间名义上的联系。
当艺术群落的集体实践形成了某个共同的主题与方向,并希望更多的参与者加入的时候,自我组织的独立项目就出现了。独立项目虽源于艺术群落,但却更强调具体的问题研究、理念建构或行动指向,如“未知博物馆”、“未来的节日”有着明确的理念建构性,因此理论讨论成为了这些独立项目的重要一维,而实验工作坊则偏重于社会考察与研究,“外省青年”也有着理念建构性,但更着重的是行动,“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则完全是一个社会介入性的行动。
与以上类型相比,器Haus空间,非艺术空间、观察社、箭厂空间、上午空间、腾挪空间、扬子江论坛、录像局、分泌场、二楼出版机构等自主机构是相对建制化的一种自我组织形式,有着相对固定的人员、场所与一贯的出发点与目标。但与典型意义上的替代空间不同的是,他们提供的是一种中性空间,即重要的不是针对美术馆-画廊的“替代”或相对于主流的“另类”,而是一种能够容纳自主性,并促使其生长的“空间”。[3]在很多案例中,自主空间都是在独立项目中逐渐形成的,最典型的就是从“长征计划”生成了长征空间,而艺术群落与自主空间之间互相生成的关系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特别要强调的是,自我组织的不同类型之间有着很大的跨越性与流动性,大部分自我组织群体都处在某种临界状态。除了前文已有所提及的自我组织之间的生成性,更深层的原因是自我组织实践的诉求之一就是要打破既定观念与制度的规约,去呈现一种体制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异质且混杂,亦始终处于一种形成与转换的过程中,因此常常无法做惯有的框定,简而言之,临界性既是自我组织的某种诉求,也是自我组织实践的一种自然状态。如名义上的“双飞艺术中心”事实上更像是一个艺术小组,其基础是美术学院中当代艺术群落的形成,而在以中国美术学院为基础的艺术群落中,也同时生发了“小制作”这样近于独立项目的自我组织实践,而“小制作”的参与者则有不少来自其他地区的艺术群落,而同样是源于中国美术学院同学关系的无关小组则是在北京才重新聚集的。在重庆,家M公社、H2空间、器Haus空间、“外省青年”与8mg小组之间也有着这种共生、派生与转换的关系,这样的例子在其他的城市也并不少见。这种临界特征也体现在自我组织的参与者那里,很多人跨越了或经历了多个自我组织群体,实际上,因这种跨越性,自我组织的流动性也很强,经常是突然产生,然后渐渐消失,或者转换为别的形态与方式。
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自我组织现象并非只是一个偶然,自我组织的普遍发生,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大量出现是有其背景的。为什么会从2008年开始,有多重的原因。最外层的原因是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艺术市场的突然休克使亢奋地连轴转了好几年的艺术圈终于获得了一个空窗期,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些别的事情,包括早已展开的非市场系统的艺术实践。但要强调的是,自我组织并不是金融危机下的条件反射行为,而有其更为深层的背景,很多自我组织实践在2008年之前早就开始了,不过这场金融危机确实促使了很多之前只停留在讨论层面的反思开始了付诸实践。
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当代艺术内部反思的出现,在艺术产业极速发展的同时,对艺术系统越来越产业化、景观化(这两者常常是一回事)的厌烦与警惕实际上也一直在积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各种批评、反思的态度与实践早就存在,尤其是在那些相对成熟的艺术家那里。如箭厂空间创办者们的回顾:
箭厂空间成立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当时的气氛热烈而兴奋,举国上下都关注着这个盛况空前、规模巨大的体育盛会,并且沉浸在伟大祖国胜利的喜悦当中。就当代艺术界而言,当时正值艺术市场迅速扩大,个人标志的风格美学日趋盛行,各类和商业紧密结合的“创意产业园区”纷纷建立。这些情况引发了我们的反思,促使我们构思一种与之不同的艺术场景:在一个远离各大艺术区的超小空间中展示当代艺术家的作品。[4]
箭厂空间的创办与运作出于自觉的制度批判意识,他们因此拒绝商业化运作、拒绝主动的媒体宣传,拒绝加入那个产业景观。相比而言,同样是始于2008年的“小制作”这个基于年轻艺术家群落的自我组织实践体现出的则是一种自发性,他们不强调,甚至试图刻意避免某种立场化、策略化的表述。虽然“小制作”朴素的出发点是激活当地的艺术氛围,但在“疯狂”的艺术市场与模式化的画廊展览制度这些现实背景下,却生成出了一种不自觉的策略:低成本、轻松化、高频率,以及展示空间的非正式,这都是在“以自身所具有的有限资源为前提来保持创作状态”[5]。如果把箭厂空间与“小制作”视为自我组织实践的自觉性与自发性这两种典型状态的代表的话,那也需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性。
箭厂空间与“小制作”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体现了“小”及当地性,前者空间小、预算少,但强调与当地社区环境的关系,后者体现在作品与展览的“小”(轻松、低廉、迅速),以及与当地艺术群落、艺术生态的关联。这种“小”与当地性都有其制度反思的背景及策略适应的条件,箭厂所针对的是大艺术区里的“那些将艺术生产的数量凌驾于质量之上的超规格的画廊空间”,以及“那些随处可见的‘白盒子’式的,用一种事先规划好的形式来对待当代艺术的艺术空间”,其目的是“将艺术放在一个去神话的,不是美术馆和画廊的情境中去展示,尝试让艺术性的参与,探索和实验直面每日生活中的社会和政治现实”。[6]而其小空间、少预算既是条件限制使然,也能够保持一种灵活的运作。“小制作”则显示了年轻艺术家对画廊体制,尤其是对自身的某种画廊依赖症的厌倦与警醒,发起人之一张辽源曾反问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画廊,所有的艺术家就要停止工作吗?”[7]“小制作”也警惕那种江湖化的体制,防止主观上的小圈子化,因此不设门槛,谁都可以参加,不审核作品,什么作品都可以参加,是不是作品或展览都无所谓,也不强调“小制作”的概念所有权,谁都可以去使用这个名字,甚至主观上回避去做总结。这都是在强调及维护其纯粹自发的属性,以此区别于那种常常是僵化的艺术生产状态。[8]
对已经渐显模式化的当代艺术系统的反思,对固化的艺术权力体制的反动,以及对体制外力量的推动,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内部的某种反思性实践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组织已经构成了一种从中国当代艺术内部生成出来的自我反思场域。当然,不必把所有的自我组织实践都上升到这个层面上来讨论,对于艺术家来说,自我组织在大部分时候是本能而日常的,那种体制批判意识也常常是消极性而不是积极性的,实际上,很多艺术家都把参与自我组织实践视为进入稳定的画廊系统的预备阶段,尤其是在尚未被艺术市场接纳的年轻艺术家那里。但即使是这样,自我组织这种体制外实践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立并平行于官方、学院、画廊等主流话语的生态层。因此,一些有着稳定画廊合作关系的艺术家依然会投入在自我组织实践中,正如未知博物馆的组织者邱黯雄所说“做自我组织的时候,是从这个角色里拔出来了,就是说你站在系统之外,建立自我主动的方式去做艺术”。[9]在理念上自我组织实践与画廊-美术馆系统中的工作并不是对立的,但在具体的现实状况下,自我组织的主动状态则显然是区别于画廊-美术馆制度下的“被组织”状态的。
自我组织的背后是一种制度反思与批判,也是一种自主意识与诉求,亦是一种策略与应对,因此在不同语境下,自我组织的诉求内容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在面对画廊-美术馆体制的时候,自我组织诉求的是艺术家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在面对艺术的产业化、资本化、景观化的时候,自我组织诉求的是艺术实践的社群性与当地性。而当面对艺术话语权力的中心化的时候,自我组织的实践者对某种地方身份的强调与侧重即会出现,例如,重庆“外省青年”的自我命名是在借用“外省”这个法国文化概念来强调地方与中心的差异,武汉的“扬子江论坛”的命名也强调了这种地方文脉关系。[10]
这种对当地性的强调,在很多自我组织实践那里都能见到,在实验工作坊那里,当地性不仅体现为地缘身份,也体现在艺术实践与社会的具体关系中,他们的“昆山再造”与“梁山路径”等艺术项目都是以对身边乡城结合部的社会研究,但他们不预设城/乡、现代/传统、政府/民间这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强调艺术介入社会的命题落在具体的问题与社会肌理中。这也体现在对具体社会事件的介入上,如扬子江论坛就曾举办过夏健强[11]画展,虽然不可避免涉及到社会事件背景,但这个活动并没有过分强调某种政治正确的姿态,而是使它更像是一个亲友派对。
但社会介入性的自我组织有时也是社会遭遇下的具体回应,2009年底北京艺术家的“暖冬”艺术计划就是一场面临强制性拆迁的自我组织事件,而2010年中武汉的“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则是针对公共环境资源遭受侵占的自我组织行动。虽然这类自我组织的诉求并不是艺术系统中的主体性,而是社会领域中的公共权利,但艺术作为一种修辞力量参与其中,有效地引起了更多层面的社会关注。
一个值得注意的相关背景问题是,随着艺术产业化的逐渐升级,艺术区也渐渐由最初单纯的艺术家聚居,变成了政府政策下的产业配套开发,政府权力与地产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艺术家则从最初的自我组织状态变成了“被组织”状态。这种状态转换可以从侧面说明艺术家自我组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上出现的。一方面是艺术体制内部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外部社会的张力,2008年以来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呈现与各种民间权利的诉求发声,也使得艺术家们作为社会人被裹挟进了这类问题及事件之中。他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艺术介入社会”的命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系统已经介入了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也不再是艺术家们唯一的艺术实践方式,对艺术制度的自觉意识与行动已成为当代性的某种条件,在这个语境下,自我组织的制度反思意识体现出了更深的含义。
自我组织中也不乏有着主动而具体的出发点,可以是某种艺术媒介或类型,如绿校是一个专门的漫画社团,三分钟小组专门讨论与实践影像创作,“庆典”则是一个行为艺术实验项目,南山绘画小组则关注绘画问题。自我组织中也有很多都设定着明确的艺术系统中的着力点,录像局把注意力集中在录像艺术的档案收藏与整理上,“二楼”把当代艺术的出版作为其主要工作,青年折扣店则是在尝试建立一种艺术家自主经营的艺术品销售方式,而由一部分年轻评论家组织的“金棕榈+金酸梅”奖年度评选所针对的则是日益被垄断的媒体话语,而希望提出一种不同的公共意见。
而对美术馆-画廊系统的反思,则也体现为主动地选择户外与公共的环境,如雄黄社组织的“骄傲”、“风流”、“天涯”等展览,forgetart策划的“龙泉洗浴”。这种远离正规展览空间的态度与箭厂、观察社等远离产业化艺术区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其中都隐藏着某种制度批判意识,实际上,雄黄社与forgetart后来都分别组织了更为明确针对的活动,如“春秋”是要把艺术行动安插在美术馆-画廊的展览中,forgetartfair则是对博览会展览形态的某种戏拟。
在分析自我组织的批判意识的同时,亦不能忽视很多自我组织所表现出来的自足性,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阿掉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娱自乐的自足性,其中含有的对制度化的警惕,以及对自主状态的敏感,依然可以放在制度反思的心态中去讨论。正如阿掉队的成员梁硕的话:“一个艺术家得对周围盛行的现象保持审慎批判的态度,而不是大拨哄得跟着干,这个态度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这是对的,但你要是非得跟别人对着干这么走下去就会陷入到另一种模式里,那又不是自由,所以我觉得掉队运转的核心就是‘通行无碍’,随时都调整,随时都对周围做出反应,没什么东西值得坚持。”[12]其核心是对自主性的强调,但自主性又得通过不断地自我反观才能获得。与这种自主状态敏感性相关的是很多自我组织内部的去权威化态度,自我组织的制度批判意识面对的是制度化本身,因为正是制度化带来了话语与权力的中心,这本来就是自我组织实践所警惕与反思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近几年来的当代艺术自我组织与’85时期的艺术群体有着关键的区别,’85的艺术群体有着明显的党派性,有宣言,也有“英雄化”的核心人物,讲集体意志,更重要的是有着运动化的话语方式,总是力图把某个艺术理念普遍化,强调其权重性。在这一点上,高名潞概括的很好:“’85群体不仅是一种组织形式,也是一种精神,他们很像一个个小型战斗队,而且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鲜明的主张和观点。”[13]而当时各地的艺术群体都总有几位领袖人物,他们基本控制了群体的话语,而艺术群体也把自己区别于群体外的大众,如舒群就曾说过:“我们自视为‘超人’,而称一般知识大众为羊群。”[14]而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如对权重性的极力强调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在珠海会议与“89现代艺术大展”这样的中心化的展览中。[15]
相比之下,2000年之后的自我组织群体就要松散的多,他们不强调中心,即使是有发起人或组织事务的负责人,但都不强调这种身份,更是避免“策展人”等制度化的叫法。尤其是他们都不认为是在,也不打算去推出一种整体性的艺术理念,非运动化且去权重性,这与’85时期的群体运动化的做法有着最关键的不同。与此相关的是,大部分艺术小组也都不以某个明确的艺术理念为基础,这一点在小组名称的任意性上即得到了体现,如TOF小组的名称既是指TimeofFlying,也是小组工作室的门牌号码215(TwoOneFive),8mg小组的名称则是来自某种香烟的焦油含量。很多小组的成立是基于对目前的展览体制与工作方式的应对,其中包含着很强的应变性,如GUEST小组就是在一次驻留计划中即兴成立的,细胞小组则源于细胞式生产方式(CellProduction)中的有机合作的组织模式,大项目小组也是基于这种合作才成立的。这些小组都以艺术项目为其主要的工作方式,强调的是内部的平等与合作,而不是中心化的个人。甚至,和谐巴洛克小组保持着成员的匿名状态,这使得任何的个人中心都不太可能,也不再有意义。
自我组织突然大量的出现,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年轻艺术家的成长与成熟。2000年以来的当代艺术产业暴涨式发展,恰好与年轻艺术家接受教育并逐步进入艺术生涯的过程是同步的,而几乎是同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更提供了一种有力组织平台与沟通工具。当然,自我组织并不是一个只属于年轻艺术家的或者一个现今才出现的新现象,但2000年左右及之后毕业的这一代年轻艺术家所置身其中的逐渐成型的也逐渐固化的当代艺术系统使他们一开始就面对着一种制度化的压力,因此可以说,这一代年轻艺术家普遍参与到自我组织的实践之中,或许正是对这种状况的回应。年轻艺术家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艺术产业与市场的结构,还包括与其纠缠同构的各种艺术话语,如何处理这些话语的影响并获得独立意识也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某种艺术态度与观念转换的诉求亦是自我组织实践的动力之一。
不能忽视的是90年代以来及2000年代初的艺术自我组织实践对这一代年轻艺术家的影响,如大尾象工作组、博尔赫斯书店、艺术家仓库、后感性、比翼艺术中心、长征计划、维他命艺术空间、联合现场等小组、机构与艺术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有些甚至构成了引发后来的自我组织实践的具体环境。在描述这种自我组织的“传统”的时候,得意识到自我组织状态实际上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常态,它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特别是画廊-美术馆大量出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当代艺术展览都是在自我组织的状态下完成的。但这也正说明了画廊-美术馆占据当代艺术系统的主导地位之后的自我组织实践是不同于之前的,现在的年轻艺术家置身其中的是一个新的背景。[16]
实际上,’85时期的艺术群体也是由当时的青年艺术家组成的,’85新潮被叫做“青年美术运动”,其各种艺术群体也被叫做青年美术群体,人们现在习惯说的“珠海会议”的正式名称是“’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暨学术研讨会”。[17]但重要的并不是艺术家年龄上的年轻,或者青年艺术家的人数比例,而是自主意识的形成,当时的青年艺术家与批评家对这种自主意识尤为强调,即使这种强调是以某种权力诉求的面目出现的。[18]就字面而言,“自我组织”就已经包含了两个重点,自主性与群体性,但自主性所面对的既定制度与观念在不断转变,因此自主性的应对与诉求,以及群体性的性质与策略也始终在变化。对于’85时期的艺术家来说,他们面对的是美协-美院体制及与之同构的美学与意识形态,所依赖的却是少数几本美术杂志,因此那种运动化的群体策略即应运而生。
而到了90年代,这种群体策略的背景就发生了变化,当时作为青年艺术家的邱志杰描述了当时他眼中的状况:
20世纪90年代初,批评家们在中国美术中呼风唤雨,艺术家们在理想受挫时求告于自己信赖的批评家,而青年艺术家的成名,也要依赖于批判家的赏识提携。批评家们在1992年通过和发表了一个类似于行业公会的收费标准的公约。这份文件表明,那时人们普遍相信,艺术创作现象,必须通过批评组织成话语,然后向艺术市场“推出”。这种信念到九十年代中期导致了若干次“批评家提名展”。[19]
与这种批评家占据话语主导权的状况不无关系的是“后感性”展览实践,它可以视为是一部分青年艺术家针对这种批评家话语权的自我组织实践,并且从反对批评家的主导权力到了反对艺术的知识论化,邱志杰认为这种知识论正是批评家权力的话语所在。也就是说,即使在“后感性”这样的艺术实验的背后,当代艺术场域主导权转换的背景依然是清晰的,甚至“实质是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的权力斗争”。[20]饶有意味的是,批评家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场域主导权力的转换:
批评家提名展试图通过纯学术的“集团批评”方式的持续运作来影响当代艺术的发展,同样是一种文化理想。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既难以做到学术应有的纯度,更难以做到运作上的“持续”。因为批评的话语权最终还是操控在出钱人的手里。[21]
如果把90年代初的批评家提名展也视为批评家们的自我组织实践的话,他们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新出现的资本权力,因此他们强调“文化理想”与“学术纯度”。可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市场的出现则给了他们相对于批评家话语的某种自主权,但仅仅依靠市场是不够的,而且容易被资本权力同化,因此后感性这样的由艺术家发起和组织的当代艺术学术场域的艺术实验很自然就出现了。当然,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场域关系要远远比这个复杂,本文举出这一对例子是为了说明自主性的诉求内容在不同的视域下是不同的。[22]
2000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场域的背景发生了整体性的转换,当代艺术从“地下”走到地上,当代艺术市场系统的建立与“繁荣”,画廊-美术馆系统的初步形成,学院对当代艺术的逐步开放,公众与传媒对当代艺术的日渐接纳与消费,政府在艺术产业上的加大扶持与文化上的加强管控,以及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深地被卷入整个国际当代艺术系统之中。这种转换的实际上是政权、资本、媒体与话语构成了一个综合景观(IntegratedSpectacle),艺术制度与话语都成为了这个景观的一部分。在这个背景下,艺术自主性面临着彻底丧失的可能,同时任何对象化的批判都已不再有效,艺术实践需要落实到对自身的制度反思中去,缺乏这种制度反思性的艺术实践——不管是何种立场与姿态——都难免被吸纳为景观的一个部分。
通过这个问题场域转换的背景来观察和讨论2000年以来的自我组织实践,能够发现其呈现出的自主性诉求的针对点越来越从某种公共权力或某类群体与身份的权力,转换为某种抽象的、匿名的、制度化的权力,即景观统治本身。这种景观统治的具体表现并不是一种外部的压迫与规训的强力,而是一种内化于观念与实践之中的无形力量,因此,自我组织实践的制度反思意识更大程度地体现为内在的自主性与自反性,而不是外部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组织已不只是对美术馆-画廊系统的替代与补充,不是一种依附性的实践,也不只是某种艺术生态的完善,抑或某种弱势者的权宜之计,实际上,自我组织自身就是一种自足的实践,亦构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独立生态。更重要的是,自我组织所触及到的是一个核心问题:制度批判意识已成为当下的艺术实践的前提,所谓的“当代性”只有在对既定的艺术生产、流通、消费与接受机制的自觉批判意识下才是可能的,在这个层面上,自我组织则构成了一种基础性实践。在今天的状况下,要讨论中国的当代艺术,以一种开放而审慎的态度去面对自我组织的一系列议题已成为必须。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已跻身于世界大馆行列[图文]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已跻身于世界大馆行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s5xfumupih.webp)
![吴为山:好的雕塑蕴含人类的灵魂[图文] 吴为山:好的雕塑蕴含人类的灵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gbdjnu1awe.webp)
![回望青山 返本开新[图文] 回望青山 返本开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alfph0fwoj.webp)
![自画像的对话[图文] 自画像的对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30orw5op1y.webp)
![让·波德里亚:作为摄影师的哲学家[图文] 让·波德里亚:作为摄影师的哲学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wl2blrcinm.webp)
![潘家园书画市场的艺术坚守者[图文] 潘家园书画市场的艺术坚守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jgzue0jztc.webp)
![盗墓:文学之热与现实之殇[图文] 盗墓:文学之热与现实之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cdqfop4ibw.webp)
![刘玉来:齐白石心理三探[图文] 刘玉来:齐白石心理三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uqcq2euvr3.webp)
![贝尔提叶·巴克的艺术:当代社会中的游民部落[图文] 贝尔提叶·巴克的艺术:当代社会中的游民部落[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uyxza0vmum.webp)
![雕塑家创作毛主席雕塑经验:右兜大些因为装着烟[图文] 雕塑家创作毛主席雕塑经验:右兜大些因为装着烟[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s31mgvsx3h.webp)
![水墨在新加坡:南洋画风是否后继无人[图文] 水墨在新加坡:南洋画风是否后继无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oiycrr1smu.webp)
![从细节中洞悉80年代的媒体与文化[图文] 从细节中洞悉80年代的媒体与文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i1fo2o04lt.webp)
![袁运甫:中国艺术要有中国气派[图文] 袁运甫:中国艺术要有中国气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od2m1ncdrk.webp)
![中国艺术家威尼斯披麻戴孝哭孔子[图文] 中国艺术家威尼斯披麻戴孝哭孔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sftiqlk50d.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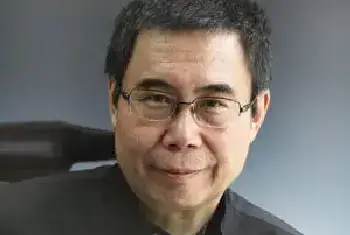
![展览为何日趋乏味平庸[图文] 展览为何日趋乏味平庸[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naa30tdfv3.webp)
![最后的Art HK 最好的时代[图文] 最后的Art HK 最好的时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e0mz0e5aiz.webp)
![十年磨一剑——陈鸣楼和他的《南宋皇城图》[图文] 十年磨一剑——陈鸣楼和他的《南宋皇城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id3zyqld34.webp)

![欣赏裸体艺术是靠情欲还是依赖品味[图文] 欣赏裸体艺术是靠情欲还是依赖品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ztdrfzqaev.webp)
![中国实力派山水画家--闫祖智[图文] 中国实力派山水画家--闫祖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jjiuoiprje.webp)
![周明智——墨舞神韵 自出一宗[图文] 周明智——墨舞神韵 自出一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twk2tqzi5r.webp)
![毕加索与中国艺术的两次相遇[图文] 毕加索与中国艺术的两次相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z5eqnpzhbk.webp)
![陈丹青:怎么看懂毕加索[图文] 陈丹青:怎么看懂毕加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3rsqrvzcua.webp)
![土著艺术家不想让西方来规定艺术的好与坏[图文] 土著艺术家不想让西方来规定艺术的好与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1cqqayasok.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