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轶:这几天在看您写的文章和访谈,里面提到“民间”。我发现:我们现在说“古”或者“复古”,一般容易想到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流那么一个模糊的范围。说“当代”或“现代”,一般容易想到的是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影响下的主流意识。“民间”似乎可以划到上述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如果被看作是古代传统可以对应民俗艺术,如果在当代艺术里出现往往体现的是一种后殖民的心态,是在资本主义文化吸纳异质因子以维持其政治正确的逻辑之下。谈复古者,往往基于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的不满,谈当代者,又往往基于对古典规则固步自封现实的不满。在上述两种划分状态里,“民间”始终是作为被压制被统治的角色出现,而且都被局部的、表面的使用。那么,“民间”里面,真正的那个更复杂矛盾、更具有批判精神的东西是什么?
郭海平:我理解的民间力量,是指那些不知道和不能接受主流文化控制的人的力量,这是一种自发和自觉的力量。今天的主流文化已显得越来越数字化、专业化、技术化和权力化,这种数字、专业、技术和权力化对人精神生存与发展的伤害很大,因为它固化了人的精神,使人的精神丧失了自由的属性。一个个天生具有自由精神的人最后都被改造成了塑料人、金属人、电子人、数字人和精神奴隶。不过,在主流文化控制之外的民间我们仍能找到自由精神的存在,它们一方面拒绝接受主流文化的主宰,同时又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当然,在这种民间力量中的成分很复杂,在我看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力量是指那些不愿放弃自己天性的人所拥有的一种意志,我们可以称这种意志为生命意志、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这种意志就是我说的那个“批判精神”。
宋轶:而“民间”的力量系觅流我们如果要深入研究,又有哪些点可以切入呢?
郭海平:在不断的反思中,我认为从被主流文化贴上“精神病人”标签的人创作的原生艺术切入是一条比较理想的途径,因为这类艺术从它的降临到生长完全不依赖于任何主流文化,它是野生的,它依靠的是人的本能、天性和自然,它有自身一套独立完整的循环系统。所以说“精神病人”创作的原生艺术与其它艺术种类相比更能反映人的生命意志、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而这些作者又恰恰是存活在主流文化之外的民间之中,对于这些原生艺术作品和作者,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人的生命意志、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而且也可以了解到人的生命意志、自然意志,以及自由意志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
宋轶:您所指的个性的力量、潜能的力量、身体的力量和自然神秘的力量等,分别指什么?是否能详细描述一下?比如您的艺术中心里哪些画能体现神秘力量,可以怎么分析?又从中如何去解读这个世界?
郭海平:不论是对于自然还是社会,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与不同生命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分不开的,否定这种差异就是对生命存在的否定。所谓潜能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我们后天接受的社会文化教育在很大程度抑制了这些能力,如我们原本可以感受到的世界,却由于受到社会文化的抑制,使我们难以感受到那个世界的存在,这时,我们只能依靠那些专家专业知识的支持,但所有专业知识反映的只能是一般的、概括的知识,这些知识忽视了每个生命个体的差异性,所以当有差异的个体应用这些没有差异的一般知识时必然会因为缺失而损伤到人自己生命的完整性,而这种缺失又进一步导致人的很多需要被忽略,久而久之人的很多功能便会出现衰退。
所谓身体的力量是针对大脑思维的力量而言的,人脑与人身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依存的,人脑是为人身体服务的重要器官,同时,人脑的活动又是依照人身体信息的反馈做出各种反映,但从另一个再度看,人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也是人脑的延续。但我们今天人为改变人恼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将人脑当着实现社会目的的机器,而人的身体又被视为维护人脑高强度工作的载体。今天人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就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原有的条件和目标都发生了更本性的改变,由此而导致人与自然越来越疏远。
我说的自然神秘力量是指超越我们大脑认知范围的一切存在。今天的人过于依赖知识,这使我们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封闭和狭隘,解放我们的个性、大脑和身体,让我们的精神获得更多的自由,只有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存在价值才能显现出属于它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我们艺术中心发展的目标就是通过丰富的艺术形式展现那些被大家忽视的人的生命和精神的存在。我希望通过视觉和互动让大家去感受和体验这些存在,而不是去进行分析,就像儿童乐园一样,如果有人愿意分析和解读,我们也不反对,但我希望这种分析和解读的最终目标是逐渐解除分析和解读。所以在选择作品时,我希望被选择的作品尽可能无需文字的解读便能传递它的精神力量,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宋轶:您也提到人的自然意志,这该怎么去具体理解呢?
郭海平:谈自然意志如果不谈疾病就会空洞抽象,因为只有在疾病中才能让人生动地体验和感知自然意志,我在新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我病故我在》文集,里面不少文章都谈到自然意志与疾病的关系。我认为我们今天用化学手段去解决人的疾病问题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些化学手段的过度使用让我们失去了许多认识生命和自然的机会,传统中医理论中“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已经很到位了,我再说都是多余的。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早已超过了文化的承受能力,过头了,所以我很理解西方的解构主义。我之所以推崇原生艺术,就是希望艺术能还原到它最初的功能,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大多数都是披着艺术外衣的伪艺术。理解自然意志在今天最好的方式我认为就是体验,而在疾病折磨中的体验是我们更不应该错过的机会。
宋轶:您说中国古人“即使有时也会出现对自然的向往,那也是用来避难的,一旦获得机会,中国人又会立刻返回社会现实,因为中国人的幸福只允许立足于世俗的社会。”这正是很多现在在“复古”的人所没有看清的问题,你们,我们又可以如何立足于自然呢?
郭海平:中国人的人生哲学都是经世致用的哲学,世俗功利是中国人很难超越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教育中,一切都是以皇权为中心,皇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始终将世界规定在他们的权力控制范围之内,正如《诗经》中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皇权控制范围之内的世界就是我们所说的世俗世界,对一切异己的力量受到皇权的排斥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所谓“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都没有超越过皇权的权力控制,在皇权控制下的“自然”是被规定为“逃避”、“养生”和缓解社会冲突,超越了这个规定是被严格禁止的。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会说出“中国至今没有一个天才”这样的话,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被称为“天才”和“天子”,再多一个“天才”和“天子”,“天下”就会“大乱”。
宋轶:如果说,中国古代主流文化教育中经世致用的逻辑对“自然”是一种阉割,但与之对应的,它也发展出一条清晰的中国美术史的发展线索,有相对比较明确的审美趣味。那么,能体现自由意志、体现身体的力量、自然神秘的力量的美学在哪里得到比较多的体现呢?
郭海平:自由意志、身体的力量、自然神秘的力量在人类的原始艺术中反映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但因为时间过于久远,我们只能从祖先留下的较少遗迹中找到一些线索,另外在近一两百年幸存的原始部落遗迹中也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家们保存了不少文献,澳洲原著名民文化应该算是保留较完整的,但眼下也正在受制现代文化的污染。
进入到文明社会,尤其是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西方的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其实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向人的自由意志、身体力量、自然力量的回归,今天当代艺术中的很多装置、行为艺术作品同样也是向原始文化的回归,而且比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更彻底,如波依斯被称为当代艺术中的萨满师就是最好的例证,我最近看到一个基弗尔创作的录像,在我看来与原始巫术没有什么不同,这既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轮回,我认为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出现回归是不可避免的,遗憾的是中国艺术界仍在那些世俗的经验里转来转去,无法实现超越,很悲哀,如要改变这种局面,我认为找到“神性”至关重要,但神性在中国人意识中被抑制了几千年,但在精神分裂者中常常还会复活。
宋轶:从远古时代的原始艺术到今天的原生艺术,可以理出一条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么?或者说您能发现所存在的哪些变化?
郭海平:我是当代艺术家,不是考古学家,所以我关注原生艺术与考古学家不同,甚至与杜布菲也不同,半个月前我在瑞士洛桑原生艺术馆与他们的国际交流中心主任露希安娜交流,她也是这个艺术馆的前任馆长,我们在原生艺术的认识上有很多分歧,我坚持认为要开放地看待原生艺术,让原生艺术与更多的学科交叉,尤其要发挥原生艺术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我的观点也得到了法国原生艺术研究学者罗亨的支持,当然,我很理解露希安娜,因为洛桑原生艺术馆毕竟有它特殊的历史使命。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原生艺术在欧美国家又重新受到关注,尤其是受到他们政府的许多支持,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今天的主流艺术离自然和人的心灵越来越远,甚至背离了艺术发展的初衷。其实这个问题中国比他们更严重,他们毕竟还经历过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的繁荣期,原生艺术在西方艺术发展中的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在中国,艺术界一直都未能超越自身的文化经验和西方的文化经验。
美国学者约翰·麦基高出版过一本《发现精神病人艺术》(TheDiscoveryoftheArtoftheInsane),这本书对精神病人艺术如何影响西方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你可以在其中了解到不少原生艺术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本书我们已经翻译完,正计划在中国出版,同时我也正在写一本《中国原生艺术手记》,明年七八月份出版,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梳理,我希望今后中国艺术的发展能真正发挥解放人精神的作用,尤其是在如何解放个人的精神方面发挥作用,今天中国人精神和社会出现许多严重的问题,都与个人精神的丧失有关。
宋轶:原始艺术和今天的原生艺术作品还算比较容易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而在3000多年的古代社会里,似乎可供参考案例比较少,您觉得如何去分析那个时期的案例呢?应该是有的吧。还是说,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人为造成的一段美术史的断裂,我们无迹可寻?
郭海平:你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心理学家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研究成果中找到一个比较系统的答案,还有一些人类学家也有不少成果,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原始思维》(布留尔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原始文化》(泰勒著)等可以告诉我们不少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应该还有不少,至于他们的成果是不是人为制造我无权下结论,不过,结合我自己的实践,我认为认识原生艺术是不能忽略对人原始思维的研究,我一直希望在中国能有人愿意做原生艺术方面的研究,我只是一个艺术家,我能做的只能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离开了具体的实践,书本上的那些理论永远是说不清的。
宋轶:您曾说“开放多元的思维与视角……如果难以体会和感受,我们则可以尝试从不同视角去认识和欣赏,如心理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等方向和视角。一旦进入那个世界,我们便能获得一种精神自由的体验。”从其他学科进入,很容易掉进一个封闭式的专业学科知识,如何建立这些学科和视觉材料的关联呢?您是否有过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
郭海平:今天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将人的精神分化瓦解成无数的碎片,以至于我们对自己衣食住行都不得不依赖于专家,而专家们一旦占有了自己的领地又会抵制与外界的联系,结果导致人精神更进一步的分裂。这几年我一直在寻找推动中国原生艺术发展的合作者,如希望有精神病学、哲学、艺术、人类学领域的专家介入,让各种学科建立联系,只有这样,原生艺术的价值才有可能获得全面完整的体现,但在中国的现实中似乎很难实现这个愿望,如很难找到既了解艺术又熟悉精神病学、哲学、人类学的跨学科的人,结果,我们看到的原生艺术评论总有严重残缺的感觉,相比之下,在西方,如果没有弗洛依德、荣格、布列东、雅斯贝尔斯、福柯、德勒兹这样的跨界学者的介入,我们很难想象西方艺术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对于今天的当代艺术就更是如此,跨界、跨学科在中国十分少见,仅仅用美术史的经验去评论当代艺术和原生艺术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当代艺术这几年的停滞不前,我认为与中国艺术家、理论家们超越不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惯性是分不开的。

![无酒不能画的傅抱石[图文] 无酒不能画的傅抱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dmvzywki0w.webp)
![不可尽信印也不可不信印[图文] 不可尽信印也不可不信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tt3epe44pk.webp)
![画家张大千艺事问答录[图文] 画家张大千艺事问答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rgebukrwyn.webp)
![千年墨脉:中国五代宋元翰墨魂脉探析[图文] 千年墨脉:中国五代宋元翰墨魂脉探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deilaqe1ny.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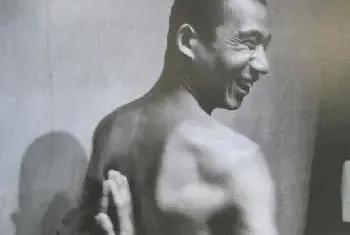
![飞行员褚铭泉的别样书法[图文] 飞行员褚铭泉的别样书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3hzhvzdrl0.webp)
![水墨动画面临无以为继的尴尬[图文] 水墨动画面临无以为继的尴尬[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wlkgzi0yxt.webp)

![师造化·得心源[图文] 师造化·得心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f0mdosjlpg.webp)
![丁方:大师杰作引我们重返正途[图文] 丁方:大师杰作引我们重返正途[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f3i250zmqb.webp)
![马兴文访谈:从“心”开始[图文] 马兴文访谈:从“心”开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myiwkka4y0.webp)
![安迪·沃霍尔的生活与艺术[图文] 安迪·沃霍尔的生活与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jwwti4tcjd.webp)
![东昌木版年画作坊减少 部分版式面临灭绝[图文] 东昌木版年画作坊减少 部分版式面临灭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np20qbgtpe.webp)
![留在记忆里的纯净——刘成湘儿童画赏析[图文] 留在记忆里的纯净——刘成湘儿童画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hcp0numdes.webp)
![身在书生壮士间[图文] 身在书生壮士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virygnm1v1.webp)
![历数全球最大胆的裸模 艺术献身or出位炒作?[图文] 历数全球最大胆的裸模 艺术献身or出位炒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4ekwubmka0.webp)
![传统文化复兴:李文培以水墨抒京剧魂[图文] 传统文化复兴:李文培以水墨抒京剧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xzaoct0xax.webp)
![欣赏裸体艺术是靠情欲还是依赖品味[图文] 欣赏裸体艺术是靠情欲还是依赖品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ztdrfzqaev.webp)
![人之初:西方艺术史中的儿童形象[图文] 人之初:西方艺术史中的儿童形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04vqb2r1ne.webp)
![许仲敏的艺术场域[图文] 许仲敏的艺术场域[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gn0kjnztpx.webp)
![英国模式下的中国评选:约翰·莫尔绘画奖[图文] 英国模式下的中国评选:约翰·莫尔绘画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h13kh21msd.webp)
![书画临摹作品有无著作权?[图文] 书画临摹作品有无著作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25ovvj5uff.webp)
![周明智——墨舞神韵 自出一宗[图文] 周明智——墨舞神韵 自出一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twk2tqzi5r.webp)
![荷由心生——读韩志冰先生的水墨画[图文] 荷由心生——读韩志冰先生的水墨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hoxrsod3aj.webp)
![对上海博物馆藏赵佶书《千字文》的质疑[图文] 对上海博物馆藏赵佶书《千字文》的质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v4meau0fd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