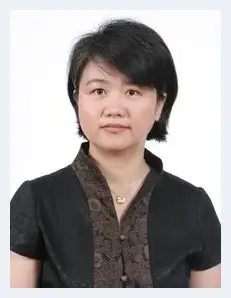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系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虻的书能够在这个时候出来,也是和这个时代的一个对话。今天的纪录片导演应该都去看看这个曾经拥有的传统,今天能不能再发扬光大,重新播撒一些种子,重新唤回纪录片人的那种坚守理想的精神。”
东方早报:陈虻的理念影响了一批体制内纪录片人,你觉得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什么?
吕新雨:就是自觉和不自觉的问题。如果你不自觉,你就会按照模式走。体制内纪录片最大的问题,就是模式化。而纪录片一旦栏目化、市场化,就必须配方化。配方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就按着这个走。陈虻是通过大量的实践,能够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把纪录片表达出来。陈虻会让你进入一个自觉的状态,而不是被动地按照一个什么标准走。
陈虻当时处在中国电视的黄金时代,是第一批制片人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在当时,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来招收最优秀的编导,用自己的方式去培养他们,这在今天是很难的。当然更重要的是,陈虻自己当时也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他与很多主流媒体之外的纪录片导演都有很好的交往,这是很难得的。那时候,没有明确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对立,恰恰相反,这两者之间有非常多的联系和渗透。在这样的环境下,才使得体制内的纪录片有了一个非常开放的维度,我个人认为,他是在体制内推广纪录片理念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而最可贵的是,他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认知,而是不断地放开自己,不断地去思考,再不断地把思考表达出来,这种特性让他获得了这样一个地位。
东方早报:陈虻很推崇你提出的“纪录片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理性到场”的观点,当初你是怎么提出这个观点的?
吕新雨:上世纪90年代,我们都还处于自我摸索的阶段。我当时提出“理性到场”这个观点,是把纪录片区别于故事片,故事片诉诸感性,让你进入到氛围中不能自拔,获得快感。纪录片恰恰是不能走这条路的。纪录片其实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一个回响,不能光是迎合快感,而是要把你的理性思考包括对现实的理解放在里边。我当时拿这个理念去和陈虻碰撞,他当时就非常认同。
东方早报:他进而把这个观点发展成为:“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观众理性到场,如果达不到理性到场,就达不到利用电视播放纪录片的目的,就是娱乐。”
吕新雨:是的,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把各种吸收来的想法在头脑中进行碰撞,然后产生出新的创造。
东方早报:如果纪录片的本质不该诉诸感性,那强调“好看”的纪录片是否偏离了纪录片的本性?
吕新雨:纪录片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所以就很难说用单一的要求去面对所有的纪录片,当时对于陈虻来说,他是做社会类型的纪录片,是和中国社会建立一个紧密关系的栏目,并且当时中国的广电体系还没有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市场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允许他能够保留他的一些思考和追求在里边,所以他用了理性思考这样的理念,而不是迎合观众的快感。
东方早报:崔永元说,“每每打开电视,就感觉失去了陈虻”,你怎么理解陈虻的消失?
吕新雨:对啊,真的看不到了,今天纪录片的格局已经有了新的变化,我们现在在主流媒体看到更多的是人文历史类的,很难看到现实题材的纪录片。虽然人文历史类的纪录片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在任何国家的纪录片版图里,如果你缺少对当代社会的解读和观察的视角,都是不完整的。
东方早报:今天回过头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它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为什么它没有了延续性?
吕新雨: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从工农兵学商这样一个分类里走出来,“老百姓”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有亲切感的词,这是个具有共识的名词。所以一出来就不胫而走,成为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到了1990年代后半期,经济市场化改革迅速发展,这个词就产生了破裂,“老百姓”越来越少用,纪录片里越来越多出现的是“边缘人”。大家都会说,主流媒体为什么总要拍“边缘人”?所以主流媒体就渐渐放弃了“边缘人”,而“边缘人”就渐渐消失在《生活空间》这样的节目里,更多的是在法制节目、社会新闻里,成为贫穷、落后、流血犯罪的代名词了。到今天,我们干脆用“底层”来称呼他们。今天的中国媒体的困境是,社会已经产生一个结构性的断裂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弥补它,这就使得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亲和力下降,所以使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没有办法有延续性。
在陈虻时代,主流媒体和体制外导演还有着一个很好的相互合作的状态,互相吸收营养。而现在,体制外导演都在拍底层社会,主流媒体都在拍上层社会。
东方早报:所以拍什么才是今天纪录片的困境?
吕新雨:没错,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记录,我们不缺记录手段和方法,而缺记录的理念——你为什么要记录?记录不应该是一个被动的行为,而应该有主观判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共信息的保护,比如说高端人士,你基本没办法真实记录,底层人士的伦理问题,你也不能够直接触碰。中国纪录片的确是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
东方早报:从书里可以看出陈虻一直在强调要和拍摄对象保持“平视”的关系。
吕新雨:没错,我经常用他的这句话,陈虻说,“如果拍摄对象在你摄影机面前发抖,不是他不行,是你不行,因为他在她老婆面前是不发抖的”。你不要以为你是电视台的,你就可以有优越感,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让你的拍摄者认同你也是个老百姓,那你就失败了。包括他提到的选材,虽然题材一样,但是每个人拍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样找到选题的最佳视角,就像钻石在阳光下,你转一下,那个光芒就会出来,你不转,那个光芒就会看不见。
东方早报:《生活空间》开播于1993年,到今年20年过去了,你认为中国纪录片有了哪些变化?
吕新雨:今天媒体格局的发展,都已经与陈虻那个时代有所不同,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回到那个时代了。但我认为,很多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像央视的《舌尖上的中国》,理念还是从人物上来的,每一集都有人的故事。它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因为它的精神血脉还是来自上世纪90年代那一批人的理想,以老百姓为主体。
新媒体的出现,也是变化之一。新媒体也开始搭建平台,也许突破需要时日;主流媒体更多是做人文历史类纪录片,这样也不错,但是一定要想,中国历史、人文传统这么丰富,我们的纪录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呈现出来?如果你看过BBC的片子,你会发现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这个也是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主流媒体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话,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操作。
在今天只要拍摄小人物的故事,就很难不触碰社会问题最敏感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努力。比如说上海电视节也会容纳主流媒体之外的导演的作品,他们也会和这些导演合作来拍片,包括央视纪录频道,还有民间影展、学校咖啡馆、收费电视等等都在推动。我们有多元化的发展,最后能走到什么程度,我认为还是值得期待的。
东方早报:你如何推荐这本书?
吕新雨:关于陈虻的书能够在这个时候出来,也是和这个时代的一个对话。体制内的导演应该都去看看这个曾经拥有的传统,思考一下他的理念,今天能不能再发扬光大,重新播撒一些种子,重新唤回纪录片人的那种坚守理想的精神。

![詹建俊:选择绘画一生理想[图文] 詹建俊:选择绘画一生理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orlpea23aw.webp)
![20世纪上半期女画家现象研究[图文] 20世纪上半期女画家现象研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2uwu3zgfxr.webp)
![书坛翘楚亦斵轮[图文] 书坛翘楚亦斵轮[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30g1aa0awu.webp)
![姜节泓:让艺术走进生活[图文] 姜节泓:让艺术走进生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ebummt34bt.webp)
![动漫是否会成为下一代的艺术表达[图文] 动漫是否会成为下一代的艺术表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vial44qpjz.webp)
![王羽佳:游走中的钢琴家[图文] 王羽佳:游走中的钢琴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rg5zvbdomz.webp)
![姜宝林既要笔墨又要现代 曾与香榧树结深厚感情[图文] 姜宝林既要笔墨又要现代 曾与香榧树结深厚感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ldm3b3xerr.webp)
![徐渭晚年高傲孤僻 《水仙图》缺乏豁达感[图文] 徐渭晚年高傲孤僻 《水仙图》缺乏豁达感[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rrpo00rxo4.webp)
![“黑白”世界写情缘--女画家阚玉敏印象[图文] “黑白”世界写情缘--女画家阚玉敏印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1lpbdq0ir1.webp)
![寇克让:不书写就不要谈书法[图文] 寇克让:不书写就不要谈书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bktnzowbq4.webp)
![严师与高徒[图文] 严师与高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siwei51iks.webp)
![郭庆祥:谈吴大羽的绘画创新精神[图文] 郭庆祥:谈吴大羽的绘画创新精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05qbvgejsv.webp)
![村上为什么没获诺奖[图文] 村上为什么没获诺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rbrtffizr4.webp)
![行为艺术遭遇现实围剿[图文] 行为艺术遭遇现实围剿[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bj10wyixvt.webp)
![李叔同:培养后人严肃教育 博学善导遗世独立[图文] 李叔同:培养后人严肃教育 博学善导遗世独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zy1xtk2mef.webp)
![笔挟风雷起狂涛——陈求之“水墨文字”之意义试解[图文] 笔挟风雷起狂涛——陈求之“水墨文字”之意义试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kjr2jitcgk.webp)

![国画不当代何谈中国当代艺术[图文] 国画不当代何谈中国当代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jujjnox4ee.webp)
![文人画的文化价值正在回归[图文] 文人画的文化价值正在回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ara4lj140t.webp)
![欣赏裸体艺术是靠情欲还是依赖品味[图文] 欣赏裸体艺术是靠情欲还是依赖品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ztdrfzqaev.webp)
![对上海博物馆藏赵佶书《千字文》的质疑[图文] 对上海博物馆藏赵佶书《千字文》的质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v4meau0fd4.webp)
![英国模式下的中国评选:约翰·莫尔绘画奖[图文] 英国模式下的中国评选:约翰·莫尔绘画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h13kh21msd.webp)
![文革时山水画怎样画:画成壮丽山河[图文] 文革时山水画怎样画:画成壮丽山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mxsfy3zfpy.webp)
![陈丹青:怎么看懂毕加索[图文] 陈丹青:怎么看懂毕加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3rsqrvzcua.webp)
![许钦松:我们的画是画给当代人和后世看的[图文] 许钦松:我们的画是画给当代人和后世看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mvpuuakmyf.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