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多个公开的场合讲过同一个话题:在当下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周围,并不缺少所谓的“美术家”(还可包括所谓的“大师”和“名家”在内)。这类靠画画而名利双收的所谓“美术家”不少于十万数,乃至百万数。有的“画家”干脆就把自己的画室说成了“印钞间”。于是乎,粗制滥造的各种“名画”、“佳作”漫天飞舞,并充斥于各地的画廊和拍场,还包括见不得人的“地下买卖场所”。所缺少的是艺术家——他们是真正以艺术为生命,而不以名利为鹄,且可以长期地坚守一份寂寞、孤独,又有一定的创造性潜能的人。他们的人数虽少(最多以百、千计,超不过万数),但却是一批特殊的人材,堪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笔宝贵财富。再进一步说,真正缺少的也不是艺术家(至少还可以举上一长串的名字),而是个案——能面向世界、且具有了相当说服力的创造性案例。这就少之又少了,几乎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可也正是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中国——在回应世界、在向世界“说话”、并展示着中国新艺术的风采!
李华生就是具有了这等水准的个案之一。
想要成为个案的难度在哪里?为什么许多人成不了个案?我的回答是,难点有二:一是要找准思路;二是要把精神与语言都提炼到位。李华生的成功正好印证了我的判断。
所谓“找准思路”,首先是要重视思路。所谓思路,就是按什么样的总体构思来做今天的艺术。我一向以为:思路决定了格局大小,格局大小又决定了个人成就的高、低、多、寡,故选择总体思路不可不慎之。百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历程中出现过了三个大的发展思路:传统主义、中西融合(或结合)和西方主义。可这三个发展思路都是亟须我们去加以深刻反省的(此处不便讨论)。
李华生在四十岁以前(当时还在重庆),一直就迷恋于古代传统绘画,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写意山水,浸淫日久。到了成都以后,还曾几次面见山水名家——陈子庄(虽称不上是其学生)。1987年,他在去美国前、后,一直都在创作具有文人意境的“新文人画”。著名中国美术史学家——苏立文曾推举他为国内“新文人画”的“典型”,香港“汉雅轩”的掌门人——张颂仁还称他为“野逸画家”。他在多年以后,还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传统”对我不薄啊!我如今有了车,有了房(一处晚清宅院),还不都是靠了“传统”吗?!事实也正是这样——他手里的“新文人画”作的行情在当年可谓是一路走俏。
可就在此当儿(从美国回来的头些年),他却对自己来了个急刹车!那些“新文人画”不再画了,已画好的也被扔进了废纸堆。用他自己的话说:去了美国,看了许多20世纪大师的作品,我被震惊的腿都发软——站不住了。他还突然发现:自己不会画画了!可在同时,他又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对我们中国艺术家抱有希望!
怎么办呢?在对自己实行“休克”疗法之后,他深感苦闷、焦虑,同时也在思索、试验。几年以后的一天,他在百无聊懒之中随手画出了一条横线,顿时便悟出了新的突破点——画那些单纯的,呆呆木木的“线·格”。“线”是做了“减法”的,采用小尖毛笔画出的“中国线”;“格”则是从中国建筑中体悟到的小方格。千条万条的横竖线(其实也就是一根线),密密匝匝的小方格(一格是空,格格都是空),剔除了意象,剔除了一切与“物”相关的世欲符号,收敛了激情和世俗欲念,张扬了理性和控制力,最后只剩下了“一无用处”、“一无是处”的象征“天地骨架”的“线·格”。令他所想不到的是,这“一无用处正是它的伟大用处!”(莫言语)
这一次突变,犹如由蛹而化蝶,实在是高,也实在是妙。高就高在它既不是传统的山水、花鸟、人物,也不是西方的表现主义抑或抽象主义的简单模仿,甚至也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它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当代(或曰文脉当代)。表面上看,它是国际化了的抽象符码,趋向了极简主义,因而具有了国际性。实际上,它所依托的却是儒、释、道三家的智慧和精神含量,而这也正是它的妙处和丰富性所在。
论儒: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积极态度,支撑着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克服寂寞、孤独、无聊感,以“游于艺”的态度,坚守于“线·格”无限重复、单调乏味的创作生涯,一件作品常常须劳作半个月时间,可谓甘苦并尝,故而“线·格”一如人格。与此同时,方方正正、至善至真、抱素怀朴、思无邪的儒家审美理想也被他一起融入了“线·格”之中。我们从“线·格”中所感受到的方正、雅致、纯粹、高贵品性正源于此。

![童真世界中的文化呈现[图文] 童真世界中的文化呈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mxmvyogqnv.webp)
![高科技破解蒙娜丽莎微笑之谜[图文] 高科技破解蒙娜丽莎微笑之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kbkqth1yo5.webp)
![王鑫小事记:艺术家也有真性情[图文] 王鑫小事记:艺术家也有真性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g05l51g4md.webp)
![书画家:汉字草写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正脉[图文] 书画家:汉字草写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正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1ee2mb2u4t.webp)
![鲁明军眼里的沈爱其[图文] 鲁明军眼里的沈爱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cqd125lxwu.webp)
![神秘面纱下的朝鲜当代艺术[图文] 神秘面纱下的朝鲜当代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ze5li4sjzk.webp)
![身在书生壮士间[图文] 身在书生壮士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virygnm1v1.webp)
![徐文生:牡丹文化与绘画[图文] 徐文生:牡丹文化与绘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w5fjulyeh2.webp)
![最后的Art HK 最好的时代[图文] 最后的Art HK 最好的时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e0mz0e5aiz.webp)
![雕塑家的艺术跨界实践[图文] 雕塑家的艺术跨界实践[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nsap5f0aet.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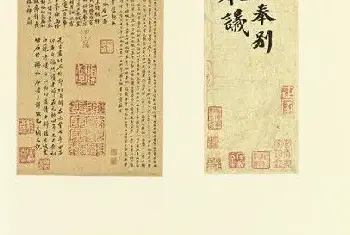
![且读且画[图文] 且读且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dh3jfcmugy.webp)
![王林:我为什么要做“未曾呈现的声音”? [图文] 王林:我为什么要做“未曾呈现的声音”? [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rc0paja1i2.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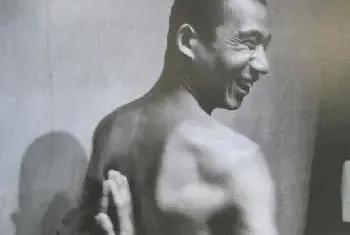
![严克勤:遇到一位好老师比一个好学校更重要[图文] 严克勤:遇到一位好老师比一个好学校更重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4xwutv10dx.webp)

![展览为何日趋乏味平庸[图文] 展览为何日趋乏味平庸[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naa30tdfv3.webp)
![许仲敏的艺术场域[图文] 许仲敏的艺术场域[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gn0kjnztpx.webp)
![石湾公仔黄:用中国画技法捏陶瓷[图文] 石湾公仔黄:用中国画技法捏陶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ayd5sjt54r.webp)
![十年磨一剑——陈鸣楼和他的《南宋皇城图》[图文] 十年磨一剑——陈鸣楼和他的《南宋皇城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id3zyqld34.webp)
![回归自然的心灵--栾可新山水画色彩浅谈[图文] 回归自然的心灵--栾可新山水画色彩浅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svsplj1e5f.webp)
![中国画当如何写生?[图文] 中国画当如何写生?[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jxlkzddxw0.webp)
![中国实力派山水画家--闫祖智[图文] 中国实力派山水画家--闫祖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jjiuoiprje.webp)
![张晓刚:川美现象在走下坡路[图文] 张晓刚:川美现象在走下坡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zfqojnvshb.webp)
![比利安娜:艺术可以改变世界[图文] 比利安娜:艺术可以改变世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3i15ex3dpd.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