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点拥有太阳的形状,这是世界和生活力量的象征;它也有着月亮的形状,这意味着宁静。圆形、柔软、色彩斑斓、无知无觉、不可捉摸,波点成了一种运动。波点是通往无限的方式。
 1969年3月17日,草间弥生与一些艺术家在纽约中央公园
1969年3月17日,草间弥生与一些艺术家在纽约中央公园
83岁时,草间弥生再次来到纽约这座对其影响至深的城市。她一生的作品,从她尚未到达纽约的上世纪40年代,到其离开纽约的70年代之后,被精心挑选,以回顾展的形式,陈列在纽约惠特尼美术馆——一个以“美国艺术”为名的美术馆中。
在长达八旬的人生中,草间弥生在美国只生活了15年,但在这段旅居岁月里,她创造了其艺术生涯中最为人知的作品。多年以后,当她回到纽约,这座城市在她眼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芒:“没有变化,乏善可陈。”这种差异因为观察者自身的改变,也因为城市的不易改变。
人们谈论草间弥生的生涯,通常会从她那“不堪回首的少女时代”开始。1929年,她出生在日本长野县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的家族“做了一个世纪的种子生意”。在一张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一个手捧菊花的短发女孩儿,面容清秀、神情严肃。这个10岁的女孩儿遭受幻视和幻听的困扰,而在其父母看来,一切不过是孩子的胡闹。“我的父母是一场真正的痛苦,他们传统、守旧。”草间弥生说。在她幼年的涂鸦中,母亲通身布满圆点——这样的圆点出现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段惨淡岁月成为她艺术的源泉:“我常常会跑到我家后面的河岸平原,盯着一个景象任时光溜走,在那个画面当中,亿万颗粒粒分明的白色小石头,吸饱仲夏的阳光静静‘存在’——那是我画这些画的神秘根源。”
1957年,草间弥生来到美国,开始人生新征程,这一年她28岁,在日本已有了一些名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人海外旅居并非易事。日本政府控制外汇流出,为了让一切顺利,草间只得在衣服的内衬里也塞上钱。她在西雅图待了一年,最终来到了心中的目的地——纽约。这个城市让她兴奋,在回忆录中,她如是写道:“从世界第一的摩天大楼俯瞰凡间,就像是观望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野心的战场。虽然现在两手空空,可是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在纽约随心所欲,掌握自己向往的一切。激烈的人情在我内心发烫,我下定决心要改革艺术,全身的热血为之沸腾,连自己肚子饿都忘了。”
纽约的第一年远称不上美妙。实际上,只身在外的姑娘遭受着经济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她的公寓没有暖气,一到冬天,便成为“人间地狱”。为了抵抗严寒,草间只得通宵作画。但城市给予了她别的快慰——她遇到了艺术家的最好时代,此时的纽约是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的,这是马克·罗思科、威廉·德·库宁和安迪·沃霍尔的年代,也是所有来纽约的艺术家的时代。年轻的草间弥生身穿和服,却已将自己当成一个美国艺术家。“纽约滋养了我。”她对日本的杂志说,她要创造一场艺术革命,“将震惊整个纽约艺术界”。
 以“美国艺术”为名的美术馆
以“美国艺术”为名的美术馆
“无限的网”是这个日本艺术家纽约“艺术革命”的第一步。这密集如蕾丝的绘画在年轻艺术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草间绘制的无限繁衍的“网”之中,他们看到了“新与旧、男性气质与女性主义、单一性与多重性之间的融合”。60年代初期,草间弥生开始制作一种被称为“软雕塑”的艺术作品。这些“雕塑”的原型是一些日常用品:沙发、楼梯、鞋子……她从日用物什下手,在其上附加白色柱状物,称之为“堆积”,将其当做战后美国生活的一种反讽。
60年代兴起的“偶发艺术”(Happening)让草间感到了莫大的兴趣——这是一种突出偶然性和组合性的艺术形式,艺术家构造一个特别的环境,同时让观众参与其中。为了抗议“越战”,她策划了一系列“裸体偶发艺术”——这给了她至高的知名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名声。她在报纸与杂志上刊登广告,召集参与者。在草间弥生的带领下,这些赤身裸体、画满波点的人,出现在纽约著名的公共场合:纽交所、华尔街……在华尔街的游行中,草间弥生还发放了媒体通稿,其中用大写字母醒目地写着她的目标:“波点占领华尔街。”
这是草间弥生为整个纽约知晓的时期。她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在某一段时间里,她出现在报纸头条的频率,甚至超过了媒体宠儿安迪·沃霍尔。她还发行了一本属于自己的杂志,名为《KusamaOrgy》,但只维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尽管媒体乐于刊登她的照片,却并不等于他们赞赏这个“自称爱与波点女王的人”。在部分保守的公众看来,草间的某些举动是在哗众取宠。她给此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写公开信,要求停止越南战争。在信中,草间弥生称其为“亲爱的理查德”,并表示,如果总统先生愿意阻止这场不义的战争,她可以与其发生性关系。
人们无法分辨,草间此时的所为,究竟是出于对艺术的执念,还是为了获得名声所作的个人宣言;恐怕连她自己也无法言明,这些近乎疯狂的举动,是有意识的精心布置,还是一直困扰她的精神疾病作祟。但“爱的夏天”是短暂的,波尔多圆点,就像“花童”和“纸裙子”一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草间弥生必须忍受盛名过后,纽约对她的冷遇。1973年,她离开美国,回到日本。她面临着十分困难的情境。在其家乡,她像一个外来的闯入者,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也没有任何关系。更为糟糕的是,她的精神状况已经很坏,需要治疗,而她身上没有足够的钱。
 2012年7月11日,草间弥生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办自己的回顾展
2012年7月11日,草间弥生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办自己的回顾展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草间弥生扮演着“外来者”的角色。在上世纪60年代,当她雄心勃勃地来到世界艺术的中心纽约,开始与唐纳德-贾德、安迪-沃霍尔、约瑟夫-康奈尔、克拉斯-欧登柏格等人接触,并卷入波普艺术的大潮中时,她便被打上了“外来者”的印记——男权社会里的女艺术家、西方艺术圈里的日本人、正常人中的精神病患者……作为一名女性,她本可选择更婉转的方式与这世界周旋:通过进入一个男人的世界,将自己纳入整个男性世界的话语体系——就像同在50年代到达纽约的小野洋子所做的那样。毋庸置疑的是,年轻时代的草间弥生并不缺乏她同胞具备的那种“日本女人特有的色情天赋”,但在那段时间里,她没有遇见另一个“约翰-列侬”。
更重要的是,她从来也不是外部世界的“融入者”,而是一个“闯入者”——她与世界沟通的方式,是向其呈现一个完整的自造世界,诱人走入,并成为这世界里的一部分。她将作品、作为创作者的自己,以及任何一个走入其间的人,消解于同一件作品之中——这是她的艺术,也是她的处世方式。1967年,草间弥生在纽约第二大道的剧场里呈现自己的作品《消灭自己,一场声光电的表演》。《纽约客》的记者前去观看,发现她将自我、作品与周遭环境融为了一体。她说服购票进入者,“消灭自我,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为了配合灯光效果,所有观看者被强制穿上了波点服。
草间人生中另一件著名的“闯入”事件,是1966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在未获邀请的情况下,草间弥生“闯入”了威尼斯。她穿了一件金色的和服,在展亭外的草坪上布置了1500个镜球,每个要价1200里拉。她的举动遭到了展览方的禁止,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将艺术当热狗和冰淇淋一样贩卖的行径”。在评论家看来,这是她“对于名声的贪欲”,有人将之与安迪-沃霍尔比较,但她要获得认可是更为困难的,因为她是“女性、以外语争辩且生活在一个对日本的偏见有待改观的战后社会里”。1993年,草间弥生重回威尼斯双年展,这一次是以官方邀请的身份,《纽约时报》揶揄地写道,“日本被它曾排斥的艺术家所代表”。在这次展览上,草间弥生布置了一间镜屋,填满了南瓜。如今,她的银质南瓜一个可以卖到50万美元。
“现在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刻。”面对日渐增长的名声,草间弥生如是说,她毫不讳言地表示,她想变得“更有名”。“我总想向尽可能多的人传达信息。我的主要信息,是‘请停止战争、精彩地生活’。我希望能保持尽量高的形象,哪怕是在死后。”在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她已经创造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她所期望的名声,却晚来了几十年。在旁观者看来,十几年的光阴,只是80年人生道路中的短暂片段。在大众的记忆里,60年代属于唐纳德-贾德、约瑟夫-康奈尔和安迪沃-霍尔——他只活了50多岁,永远留在上世纪的纽约,而在那个年代里,曾与之一起联展、同是城中话题的日本女性草间弥生,却已从纽约的记忆里淡去,成为当下的、前卫的“日本怪婆婆”,她还在持之以恒地画她的圆点——那无穷无尽的圆形图案,繁衍的是一个阐释不尽的60年代:爱与欲、和平与战争、自我世界与外部冲突,以及这一切的最终结点:死亡。
“我相信,艺术创作的构想终究是出自于孤独沉思。那是一股由心平气和的宁静,绽放出来的斑驳彩光。现在我的创作概念主要与‘死亡’相关。”在自传《无限的网》中,草间弥生这样写道:“科学、机械万能导致人类妄自尊大,这不但让人类失去生命的光辉,也让大家的想象力变得贫乏。资讯社会越来越蛮横、文化单一、环境污染,在这地狱般的景象中,生命的神秘力量已经停止运作,我们的死亡也放弃自身的宁静庄严。我们正一步一步失去那种静谧的死寂。”

![李宓:对我影响最大的艺术品[图文] 李宓:对我影响最大的艺术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mkbh1mmjgm.webp)
![宫崎骏:融合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大师[图文] 宫崎骏:融合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大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bhpgsblaqy.webp)
![中国画不能转基因[图文] 中国画不能转基因[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5t33cyovul.webp)
![颜长江:当代艺术应着重于现实问题[图文] 颜长江:当代艺术应着重于现实问题[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03i25rhcdj.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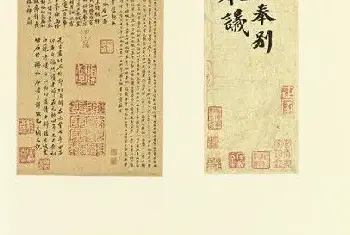
![郎绍君:寄情边塞心胸阔 兹游奇绝冠平生[图文] 郎绍君:寄情边塞心胸阔 兹游奇绝冠平生[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k4bduf3y1e.webp)
![刘玉来:人体艺术一波三折说[图文] 刘玉来:人体艺术一波三折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w44kpk1nwk.webp)
![中国近代美术史——作为标本的北平艺专[图文] 中国近代美术史——作为标本的北平艺专[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b3mbeip5ei.webp)
![谈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美学视角[图文] 谈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美学视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420wdsgccd.webp)
![谁把“莫言热”引向荒诞?[图文] 谁把“莫言热”引向荒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ztgyjhqcn1.webp)
![叶欣谈绘本:接近于人文传统的“第九艺术”[图文] 叶欣谈绘本:接近于人文传统的“第九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pxeebpi5xc.webp)
![冯梦波:倾心传统不太晚[图文] 冯梦波:倾心传统不太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4aplh1bfxt.webp)
![微中藏世界,石上谱华章——张学东平刀微刻[图文] 微中藏世界,石上谱华章——张学东平刀微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y3p1mr3jsp.webp)
![殷双喜 毛泽东关于人体写生模特儿批示始末[图文] 殷双喜 毛泽东关于人体写生模特儿批示始末[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mw3sj2ghtd.webp)
![朱万章谈美育:意在山水诗画间[图文] 朱万章谈美育:意在山水诗画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0ltpozmr0z.webp)
![石湾公仔黄:用中国画技法捏陶瓷[图文] 石湾公仔黄:用中国画技法捏陶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ayd5sjt54r.webp)
![青花居士收藏杂谈:关于收藏的“胡说八道”[图文] 青花居士收藏杂谈:关于收藏的“胡说八道”[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z2gsbumpya.webp)
![最后的Art HK 最好的时代[图文] 最后的Art HK 最好的时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e0mz0e5aiz.webp)
![历数全球最大胆的裸模 艺术献身or出位炒作?[图文] 历数全球最大胆的裸模 艺术献身or出位炒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4ekwubmka0.webp)
![原研哉:无印良品美学炼金师[图文] 原研哉:无印良品美学炼金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ma0hjh2fmw.webp)
![中国雕塑院长:没有文化自觉中国不可能崛起[图文] 中国雕塑院长:没有文化自觉中国不可能崛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o123pprm5x.webp)
![张远:放弃高薪回乡搞起葫芦烫画[图文] 张远:放弃高薪回乡搞起葫芦烫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s4l235lu5f.webp)
![女艺术家裸睡铁丝床:庆祝无意义[图文] 女艺术家裸睡铁丝床:庆祝无意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mxrnrlqdkc.webp)
![中国实力派山水画家--闫祖智[图文] 中国实力派山水画家--闫祖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jjiuoiprje.webp)
![张晓刚:川美现象在走下坡路[图文] 张晓刚:川美现象在走下坡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zfqojnvshb.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