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尚辉
但这百余年的中国油画,既是一个不断深入研习欧洲油画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用油画表现中国人的精神情感、塑造中华民族的人文形象、不断探求油画的东方文化审美品格的创造过程。中国油画语言,毫无疑问,一方面要在造型、色彩及表现形态等方面呈现出属于这种绘画媒材属性的艺术独特性,因而中国油画语言的历史演进必然会以欧洲原发油画的历史积淀与艺术传统为研习模仿的典范;另一方面则因民族审美心理、创作方法及价值观念而对这种舶来的油画语言进行本土化的创造,形成东方民族的油画语言体系。移植油画的难度,在于把此种绘画语言以及掩藏在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观念与传统积淀能够在东方文化的谱系里进行转用、嫁接和增生。显然,只有不断深化对于欧洲油画艺术传统的研究,才能更深刻地创造油画的中国风采。这个展览试图从中国油画艺术语言的历史演进中,探讨油画本土化的审美意蕴。
第一部引进与起步
伴随着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汹涌澎湃,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学习油画的高潮,从而彻底改变了此前由外籍传教士和职业画家单向输入的模式。对于西方文化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对于油画的学习与研究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引进。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引进油画的路径主要是欧洲的法国、比利时、英国和东洋日本。其时,在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之后的法国,业已成为欧洲绘画的中流砥柱。除了艺术理念与文艺思潮的不断更迭,油画语言也因材料的工业化革命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20世纪初走进欧美或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所学习的油画,是在欧美经历了印象派与后印象派洗礼、直接画法已被普遍运用的时代。因而,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引进的油画,在艺术观念上以学院派写实油画为主,兼及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等新派绘画,而且享用了工业革命成果的直接画法。
1887年考入英国阿灵顿美术学院的李铁夫,是中国第一位进入西方美术学院学习油画的留学生。毕业后,他移居美国并深受威廉•切斯和约翰•萨金特的影响。他的《未完成的老人像》造型单纯而严谨,粗厚的笔触果敢、准确而有力。这幅未完成的习作,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于形象体量感的概括性,另一方面也不乏萨金特用笔的法度与神韵。在这一代画家中,继李铁夫之后,造型严谨而又能体现直接画法稳健厚重笔触的画家当属徐悲鸿。他于1920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进入弗拉孟画室,并深受其时法国学院派写实油画的代表高尔蒙和达仰的影响。改良中国画的主张使他始终尊崇精深宏博的写实油画,他的油画丝毫没有受到其时流行的外光影响,而是以直接画法表现具有古典主义庄重儒雅画风的室内光。画面的阴影部位常用灰绿显现出与受光面土黄色系的冷暖对比,直接画法改变了亮而厚、深而薄的古典技巧,他暗部的用色同样显得粗朴厚重。徐悲鸿是这一代中对于素描造型理解最为深入、最为概括精微的画家,这种深入使他去掉了外在用笔的所谓洒脱,而专注于用笔的力道与形象内在结构关系的表现。艰深质实的肯定,宁方勿圆的果敢,形成了他的写实油画凝重朴素的画风。
除了徐悲鸿,在留法的油画群体里,常书鸿、唐一禾、司徒乔、秦宣夫、周碧初、颜文樑等几乎都是出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偏重于写实性的油画家。他们以自己的个性研习并掌握其时学院派教授的油画技巧,人物写生多半具有室内光的特点,并结合一定程度的古典写实基调,静物和风景写生则具有一定的外光特征,但并不像印象派那样纯粹,而是室内光、外光和古典基调的混合。早在国内就自学油画的颜文樑,他赴法留学的路途画的几帧海景颇得印象派神韵,但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反而趋向库尔贝厚塑堆贴的写实画法,湿压干的反复堆塑增添了油彩的层次,暗部也较多运用赭褐色调。他的米点式笔触,贴、糅、敷的直接笔法,为他的风景增添了古朴而隽永的意蕴。吕斯百是留法这一群体中少见的追求造型洗练而又显得朴素的画家,他的洗练不仅体现在对于形色的高度概括上,也体现在概括之中求得的深入与细微的表现。他用笔用色都极其沉稳,绝不夸饰浓烈,以土红、土黄、土绿、赭石为基色,追求朴素而优雅的画风。在赴欧留学的油画家中,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吴作人、张充仁学到的是具有北欧传统的油画。相较于留法学生那种塑、堆与贴的画法,吴作人学得的是油性更加圆润的扫与糅的技艺。他善于表现女性裸体富有光泽的肌肤,相对于留法画家,他的色层并不厚堆,但色层的薄透仍然给人以丰腴感。擅长采用调色油改变色彩的厚薄,不仅有助于色彩间的自然衔接,而且有利于发挥轻松洒脱的运笔。这种油色圆润、在薄透之中显现油画厚实感的画法,是北欧油画传统的精髓。
如果说,写实性的直接画法因留法与留比而显现出中国引进欧洲油画所产生传统渊源上的微妙差异,那么,其时在法国学院派油画以外盛行的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派的油画所展示的直接画法,同样吸引了众多的中国留学生。曾和徐悲鸿一样师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高尔蒙教授的林风眠,最终还是因弟戎国立美术学院院长杨希斯的教诲而转向对于塞尚和卢奥的研究。出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并专注于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的还有吴大羽、方干民、常玉、潘玉良等。其时,吴大羽、方干民的人体都偏重于强调简约的结构,常玉学得马蒂斯粗简的笔法却更加平面化,而潘玉良则把后印象派的光色加上了中国的草书线条。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运动中,刘海粟、庞薰琹都是影响很大的标志性人物。创办上海美专、并撰写出《石涛与后期印象派》的刘海粟,巧妙地将中国书画用笔转用到油彩与画布上,简化了油彩铺设中间色调的过程,通过直接画法的一次性完成和厚薄不等的油色,极大地发挥了线条与色块的独特作用,并由此体现出碑学线条苍茫浑厚的意蕴。而庞薰琹的油画始终具有一种平面装饰性,空间的扁平化以及平涂笔法,赋予他的立体主义结构以优雅的审美性。
在20世纪上半叶油画的自主引进中,还有一条路径,这就是从东洋日本学得的油画。1906年李叔同考取东京美术学校,成为中国较早赴日学习油画的留学生。此后,陈抱一、许敦谷、胡根天、王悦之、汪亚尘、关良、谭华牧、卫天霖、丁衍庸、廖继春、颜水龙、陈澄波、许幸之、倪贻德、关紫兰、赵兽、宋步云、王式廓等先后赴日留学,在抗战前夕形成高潮。他们大多出身于川端美术学校(洋画研究所)和东京美术学校,几乎同出于近代日本引进欧洲油画的代表——黑田清辉、藤岛武二和冈田三郎的门下。黑田、藤岛、冈田的油画渊源虽来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这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赴法留学的中国油画家在学派渊源上也仅仅存在20余年的时间差,但赴日留学生学到的油画毕竟已是再传性的法国油画,而且,这种再传已经加上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理解与人文创造。因而,中国留日学生学习的油画都具有某种共同性,即写实能力被弱化了的写实与表现的混搭。尽管在他们那一代的油画理念中,他们追随的是外光油画的新艺术,但他们的油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光色彩,在印象派的外光与野兽派的表现性上,他们的油画实践更偏重于表现性。
其实,正像东方人再传欧洲油画一时还难以深刻理解写实油画的真谛一样,他们对于外光的油画实践总是滞后于他们对于这种新艺术的认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油画学习中进行个性化与民族化的创造。譬如:王悦之的画法十分独特,他的有些像中国画条幅的竖构图,往往也强化了中国式的黑色勾线,画面既没有整体色调也没有中间色铺垫,排笔式的平涂使色块与线形成一种衔接。陈抱一学得的是马蒂斯式大笔挥扫的画法,薄透的色层往往呈现出粗硬笔触洒脱的动感,色彩的反复覆盖较少,白底细布、无油光感的画面显得素朴而生动。卫天霖、李瑞年是留日生中较为写实而追求厚重感的画家。卫天霖的笔法颇有法度,色彩亦注重贴、敷、堆和塑的色层变化,厚实的色层与离乱的笔法使他的作品显得凝重而古朴。李瑞年的则是在厚实中透露出一种鲜有的清新,其笔法并不张扬,而是在塑形中稍露灵巧,其色彩也非浓烈,而是在内敛里显出优雅。倪贻德和关良都偏向立体派的结构,拆散固定视点的形象使画面的线条与色块获得了重新组织的契机,他们都注重平涂色块与线条之间那种有意味的关系以及力度感的传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赴海外引进的油画,是其时以法国为中心的学院派写实油画与印象派之后新艺术运动的油画。处于中西美术碰撞第一波的中国油画家,既在他们的油画作品里显现出东亚民族对于油画造型观念与空间色彩较为深入的理解与掌握,也在他们运用油彩的过程中加入了许多没有被完全转换成西方造型观念与空间色彩的那些东方元素,意象造型、平面性与写意化——这些中国艺术的基因,都在影响中国油画家对于纯正的欧洲写实油画造型与色彩的理解,但恰恰是这些基因构成了其时中国油画向印象派之后艺术的引用,也恰恰是这些基因开始促进中国油画语言某些自身特点的成型。第一代中国油画家承担了油画移植中国的启蒙与教育使命,并在归国后进行了艰辛而漫长的油画本土化摸索。
第二部现实主义与写实方法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对于欧洲油画的学习与引进是从一个历史的切面上对于欧洲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油画艺术全方位的移植,那么,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油画则是单一地引进苏俄具有外光艺术特征、以表现历史与现实为主题的油画。就中国油画艺术史的演进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30年间,中国油画虽然远离欧洲原发油画的艺术传统,但苏俄油画在写实造型与外光色彩的伟大成就仍然深刻地推进了中国油画对于油画本体语言的认知与掌握。
写实造型与空间色彩是欧洲油画语言的精髓,而建立这种语言体系的价值核心则在于再现求真艺术观念的确立。其时,中国向苏联引进的油画主要是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批判现实主义和苏联卫国战争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油画。19世纪后期兴起的巡回展览画派,无疑是俄罗斯油画形成自己民族风格的标志。在思想内容上,这个画派的创作素材取自于民族历史与底层社会的现实生活,并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对俄国底层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艺术语言上,在经历百余年移植文艺复兴以来西欧各国的油画之后,这个画派终于摆脱了欧洲古典主义的束缚,把严谨的写实主义与表现外光的印象主义融为一体,并因北方民族特有的豪放而形成粗犷厚重的画风。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偏重于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精神激发与歌颂,将“批判现实主义”对于民众疾苦生活的揭示转换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精神面貌的颂扬,经历过残酷卫国战争的艺术家以极大的热情创作出表现卫国战争和恢复生产建设的主题性作品,这些作品构图恢弘、基调明朗、富有雕塑感的形象塑造,和新中国建立那样一种时代精神产生了强烈共鸣。应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油画对于苏俄的引进与学习,促使了中国油画从油画语言层面的“写实主义”向艺术观念上的“现实主义”的转换,没有这种强烈而深刻的表现现实与历史主题的创作诉求,没有这种现实主义创作观念与创作方法的确立,写实油画就不会如此广泛地形成中国油画的主流,写实油画语言也不会如此深入地在中国油画历史演进中获得完善与发展。
现实与历史的主题性创作无疑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油画发展的具体表现。仅“马训班”毕业创作涉及的历史题材就有冯法祀《刘胡兰》、侯一民《青年地下工作者》、秦征《家》、王流秋《转移》、王德威《英雄姐妹》、于长拱《洗星海在陕北》等,而涉及现实题材的则有詹建俊《起家》、汪诚一《远方来信》、靳尚谊《登上慕士塔格峰》、任梦璋《收获季节》、高虹《孤儿》和俞云阶《炼钢工人》等。在主题性创作的写实方法上,这些作品注重情节展开瞬间的选择、注重事件发生人物间关系的暗示、注重场景对于事件叙述的烘托与设计,而其中一些作品也不难看出苏俄油画对于这些主题性创作的启发。这些历史与现实题材的表现,并不完全是现实的真实再现,而往往被涂满了理想主义的光环,无不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情怀,“美就是生活”成为这些作品挖掘生活诗意的注释。而体现在主题性创作的视觉方法上,则往往采用仰视的视角、纪念碑式的塑造感以及单纯概括的艺术语言。王文彬的《夯歌》用仰视的视角所描绘的打夯姑娘,传递的正是一种新农民的英雄形象;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通过纪念碑式的构图和雕塑般的人物形象塑造,激发人们崇高的精神体验;朱乃正的《金色季节》以单纯概括的语言所提炼的藏女筛谷形象,表达了丰满的收获主题。
苏俄油画不仅在上述写实方法上开启了中国油画主题性创作的发展,还在本体艺术语言上深刻地推进了中国油画在造型、色彩方面的认知与掌握。民国时期的素描教育,主要承传的是法国学院派的素描理念,这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注重解剖学分析的单纯而简练的素描。苏联美术对于中国的影响,在更深层面上,是契斯恰克夫素描体系在中国美术教育造型训练上不可动摇地位的建立。契斯恰克夫素描体系是一种严谨而理性的形象塑造训练方法,通过描绘特定光线下物体及其所在空间呈现的明暗差别来理解形体、塑造形象。这种被称为全因素的素描,对于目标对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精确深入的再现,超出了古典主义依赖造型规律表现对象结构的方式。尊重所见,规避概念,鼓励艺术家不断通过写生、依靠自己的眼睛发现对象而进行深入塑造。可以说,这种极尽细腻、层次丰富的素描,较为迅速地提升了其时中国油画家对于造型的认知与能力。许多作品中出现的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生动扎实、富有塑造感的人物动态以及画面整体统一影调的把握,无不得益于这种素描训练对于造型的深度理解。
印象派的外光概念虽从直接画法而引进中国,但在实践上,20世纪前期的中国油画家鲜能画出透明而鲜亮的外光色彩。留苏学生和“马训班”学员接受最难的油画训练,就是学会空气透视中的光色观察方法、理解冷暖色相相互转换的规律、寻找同类色中色相变化的微差。他们学得的“先色块,后形象”的写生法,就是在画面里先寻找色块组合之间的内在规律与变化,然后再落实到具体形象的塑造上。应该说,留苏油画家以及“马训班”学员掌握的“苏派”油画技艺,迅速扭转了中国油画对于光色缺乏理解与掌握的懵懂状态,而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学会了用冷暖色相表现空间深度的方法。留苏学生和“马训班”学员无疑已成为那个时代“苏派”油画的播种者。他们的创作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同代人的创作,都开始显现出外光油画给予他们作品带来的艺术魅力。譬如,詹建俊的《起家》对于整幅画面起到动感和点题作用的白色帐篷的描绘,就体现了直射的暖米色与背阴部位蓝灰色的外光色彩关系;汪尘一的《远方来信》对于傍晚时光的凸显,正是通过斜射在开荒土地上的暖黄色和天空的灰蓝色以及斜斜的倒影呈现出来的灰蓝、灰紫之间大的冷暖关系的准确把握来实现的;王文彬的《夯歌》对于中午直射阳光的描绘,既来自天空灰蓝与白云米紫的对比,也来自画面那些打夯“铁姑娘”背光部位冷暖色变化的丰富表现。应该说,这些作品都是通过对于外光的充分表现而使作品获得了主题的深化。
相较于法国印象派画家优雅而纤巧的笔触,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代表列宾、苏里柯夫、谢洛夫、菲欣到苏联卫国战争后涌现出的涅普林采夫、亚布隆斯卡娅、普拉斯托夫、梅尔尼科夫和特卡切夫兄弟等,莫不显现出俄罗斯油画厚重粗放的用笔特征。这种大色块、大笔触的直接画法,曾深深地影响了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油画家,甚至于在他们这代画家的眼里,地道的油画就是用笔果断、形色一步到位,而且颜料在基底上被堆塑得很厚的绘画。这种粗放用笔的油画特征被这代中国画家所普遍接受,其潜在心理,无疑也是和中国画崇尚的写意用笔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伴随着“油画民族化”被当作一种文艺思潮的提出,从粗放厚重的俄罗斯油画生发而出的“写意性”也成为许多画家的自觉追求。譬如,董希文的《山歌》,不仅用极简略的笔触塑造出那位藏族青年黝黑的面孔,而且藏族青年蓬乱的头发和皮袍都用迅疾的笔触写出,笔意稳健而洒脱。他的《春到西藏》、《千年土地翻了身》也都运用运动感极强的笔触形成意写性的形色关系,从而增添了写实形象与空间再现的“意象”特征。作为列宾美院高级研修生的罗工柳,也是较早注重学习中国画的油画家之一。他在《毛主席在井冈山上》塑造毛泽东形象的同时,于背景井冈山的处理也更为自觉地将中国山水画的皴擦转换为油彩与笔线的写意性。苏天赐的《黑衣女青年》完全不是从写实油画变出的写意性,他对于煤黑与土红的运用也完全不是空气透视中的环境光色表现,而是主观意象的色彩关系,其笔触的运动与流畅正是建基于意象之中的随意书写,其运笔的圆转多变、柔韧弹性也有别于猪鬃扁平笔型的粗硬厚重。从苏派写实油画转向的写意探索的和从现代派对接中国文人笔墨的写意表现性,的确存在语言与意趣的差异。
董希文《开国大典》的问世,向人们展示了主题性的写实油画对于民族气派探索的广阔空间。这幅看似大场面大景深的作品,恰恰通过平面化的方法适度压缩了画面的景深,使人物组合与场景获得了较多平面关系的均衡分割,从而赋予画面以典雅高贵、庄重祥和的审美品格。应该说,“平面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油画民族化”浪潮中与“写意性”相并行的另一种语言追求。“平面化”是东方人观看事物、呈现物象的基本方法,诉诸视觉艺术,便在中国画里消除了空间深度、强化了物象之间轮廓线对于空间关系的区分,线条的作用由此得到空前的独立。写实油画的体量观念、光色关系,其实都是对于“平面化”观念方法的消解。因而,写实油画“平面化”的审美立足点在于如何压缩空间透视的深度,而不是完全没有空间体量关系或完全破坏空间透视体系。如果说靳尚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在主席整体形象的塑造上追求一种简约的体量,那么,这种简约也包含空间压缩的去细节化。他与伍必端合作的《毛主席和亚非拉人民在一起》,更是60年代将写实造型进行浅空间探索的经典,画面群体人物并不因空间压缩而失缺体量感的表达,但画面无疑因浅空间而获得单纯宁静的表现。靳尚谊对于写实油画平面化的追求显现出某种自觉性,他在《傣族妇女》作品里用弱化空间的前后关系换得了那位傣族妇女上半身的概括性处理,线与空间造型的转换显得十分深入。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油画因对苏俄油画的引进和对社会主体精神的表现,而真正形成了中国油画的现实主义主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进了中国写实油画的空前发展,写实造型水平的普遍提高、外光色彩的准确表现,都显现了中国油画在掌握造型与色彩等本体语言规律方面的深化,而建立在油画语言基础上的写意性与平面化的探索,也显得比20世纪前期更能体现油画本身的特点。如果说写实油画的平面化在于浅空间的尝试,那么写意性与平面化也完全可以按照立体派的路子向前延伸,但中国油画这种本土化的语言特征在更深层面显现的是一种优雅的诗性,而不单纯是视觉张力。正像博巴在浙江美术学院举办训练班引导学员自觉融入中国艺术特征那样,现代主义对于空间重新认识的经验,促使更多的中国油画家开始反顾中国艺术自身独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
(文\尚辉)

![选择书法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图文] 选择书法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hhesoynhlz.webp)
![深入生活 绘画当然不是臆造[图文] 深入生活 绘画当然不是臆造[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0xq455z3as.webp)
![趋势:新水墨黑马逐渐成形[图文] 趋势:新水墨黑马逐渐成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xp3tr2drh4.webp)
![艺术家的母亲胸怀和勇气[图文] 艺术家的母亲胸怀和勇气[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ayyfi50fiy.webp)
![专访刘小东:活生生的生命是怎么滚过来的[图文] 专访刘小东:活生生的生命是怎么滚过来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puosxu0afy.webp)
![“今天我们不缺记录的手段,但缺乏记录的理念” [图文] “今天我们不缺记录的手段,但缺乏记录的理念” [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qpf1bs3ecl.webp)
![王鑫小事记:艺术家也有真性情[图文] 王鑫小事记:艺术家也有真性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g05l51g4md.webp)
![“架上写意”解读上海油画[图文] “架上写意”解读上海油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tg5y1f5hxm.webp)
![星云大师说文解字谈“诚信” 重视人格价值 [图文] 星云大师说文解字谈“诚信” 重视人格价值 [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isn0ciwxzo.webp)
![写生还原创作真实[图文] 写生还原创作真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0phmo1x1ch.webp)
![当代影像艺术:挖掘人性才是好作品[图文] 当代影像艺术:挖掘人性才是好作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fcguezjoct.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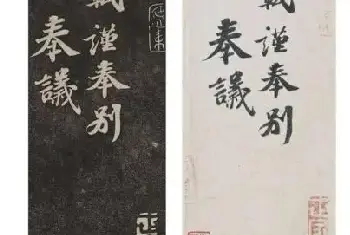
![林容生:动笔先动心[图文] 林容生:动笔先动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5tmmu0trsu.webp)
![作为男性画史附属存在的明清女性绘画[图文] 作为男性画史附属存在的明清女性绘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ecxzjrhvo0.webp)
![吴巍:写书法一定要懂文字[图文] 吴巍:写书法一定要懂文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eusyujoygy.webp)
![中国水墨艺术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图文] 中国水墨艺术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4ouytacrre.webp)
![传统文化复兴:李文培以水墨抒京剧魂[图文] 传统文化复兴:李文培以水墨抒京剧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xzaoct0xax.webp)
![王建勋:徜徉在线条世界里的智者[图文] 王建勋:徜徉在线条世界里的智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rciucl3z0r.webp)
![石湾公仔黄:用中国画技法捏陶瓷[图文] 石湾公仔黄:用中国画技法捏陶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ayd5sjt54r.webp)
![欣赏裸体艺术是靠情欲还是依赖品味[图文] 欣赏裸体艺术是靠情欲还是依赖品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ztdrfzqaev.webp)
![文革时山水画怎样画:画成壮丽山河[图文] 文革时山水画怎样画:画成壮丽山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mxsfy3zfpy.webp)
![中国雕塑院长:没有文化自觉中国不可能崛起[图文] 中国雕塑院长:没有文化自觉中国不可能崛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o123pprm5x.webp)
![回归自然的心灵--栾可新山水画色彩浅谈[图文] 回归自然的心灵--栾可新山水画色彩浅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svsplj1e5f.webp)
![张晓刚:川美现象在走下坡路[图文] 张晓刚:川美现象在走下坡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zfqojnvshb.webp)
![胡智勇:成化斗彩珍品不只有鸡缸杯[图文] 胡智勇:成化斗彩珍品不只有鸡缸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mai4j3zjjn.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