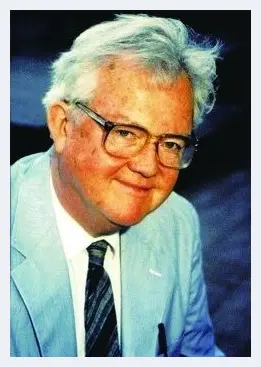
高居翰
本报记者冯智军
高居翰,一位被誉为“最了解17世纪中国绘画的美国人”,当地时间2月14日下午2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家中去世,享年88岁。这位生于加利福尼亚福特布莱格的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留给世人的是一系列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著作和他的艺术讲座视频。
在2013年12月12日的一篇博客中他写道:“并不是我害怕死亡这件事,我害怕的是能力的丧失——不能写博客,不能散步,不能与亲人朋友聊天,不能继续我的工作,尤其是做视频讲座,这是我晚年的主要工作。”这也是他倒数第二篇博客。似乎在他的生命中,工作永远是最重要的,正如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传席谈及他所认识的高居翰时所说:“他就是个著作狂。”
“异端者立场”的艺术研究之路
高居翰,1950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学士学位,1952年、1958年分获密歇根AnnArbor大学艺术史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已故知名学者罗樾(MaxLoehr)修习中国艺术史;1954年至1955年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在京都大学师从岛田修二郎;1956年在斯德哥尔摩协助喜龙仁编写其七卷本《中国绘画:大师与法则》。正是基于扎实的学术训练,高居翰一步步走进了中国美术史,并由此终身与中国美术结缘。
回到美国后,他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担任中国部主任到1965年。之后到1994年,一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艺术史教授。这期间,他曾经谢绝哈佛大学给他最高等级的“大学教授”的聘任,如同他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选择一样,他选择了回到母校,也许正因为他一以贯之的执着,才让他在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中脱颖而出,自成一家。1995年,全美艺术学院协会授予他艺术史教学终身成就奖,该协会在2004年还为他举办了杰出学者专场研讨会,2007年则授予他艺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这个艺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对高居翰可谓实至名归。在他的重要作品中,有1960年的《中国绘画》、1980年的《中国古画索引:唐、宋、元部分》及诸多重要的展览图录。这些费心费神的资料,展示了他作为一名学者踏实的治学精神。此外,1978年至1979年,高居翰受哈佛大学的诺顿讲座之邀,以明清之际的艺术史为题,发表研究和心得,后整理成《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一书,该书曾被全美艺术学院联会选为1982年年度最佳艺术史著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方闻也认为,此书是目前为止有关17世纪中国绘画论著中最具震撼力的一本。1991年,高居翰又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班普顿讲座之邀开讲,《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便是整理后的学术成果。这两部书引进中国后,均对中国的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触动。
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的《隔江山色:元代绘画(1279—1368)》《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1368—1580)》《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是高居翰研究中国绘画史的杰作。对高居翰的著作,现任《联合文学》社社长的蒋勋评价说:“中国美术由于传统太长,无论是资料掌握或观念的自由度,都形成入门的障碍。高居翰的中国美术史,提供了一个新颖而不同的视野,对我们重新面对自己的传统有耳目一新的启发性。”
2012年,三联书店又陆续推出《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等著作。台湾艺术学院教授何怀硕评价道:“(高居翰教授)最可钦佩的特色,一是描述画史的变迁,能扣紧时代、社会、文化、思潮乃至文学的发展脉络来论述,极富深度与广度……另一个特色是对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不是一般概念化的陈述,而是极细腻的鉴赏与分析,不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且这种实证的方法,非常雄辩地印证了他的史观。至于时常以中西艺术史的轨迹来对比说明,对画史、画迹的资料巨细无遗的排比解析,充分显示了作者知识博洽,见解独到,令人击节。”
对他的中国画史研究,高居翰曾撰文写道:“最近几年,我亦开始意识到,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症结在于不愿挑战这些正统观念,拒绝承认和评价各种对立的取向,并且难以容忍不同的声音。正是基于这一看法,我有意地以采取异端者立场,提请人们注意那些被排除在常规之外的艺术家,对那些宏大的‘核心真理’提出异议(它们常被证实是掩盖了另外一些同等重要的价值),并试图揭示那些被刻意遮掩的绘画领域。即便由于语言能力以及作为文化局外人的理解局限,但我仍确信这些工作值得一为。”正是这种“异端者立场”,开拓了中国画史研究的诸多新视角。
1月10日,高居翰在博客中写道:“现在的我只能卧病在床,我也不得不承认未来的日子也会如此。”然而时隔不久,他便辞世,此篇博文也成了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继去年苏立文先生去世,又一位致力于中国艺术研究的学者的谢幕,让人有一种巨大的缺失感。
这些西方学者们对中国美术的研究与中国学者们有何差异,这种不同对中国美术的研究有何助益,为此,本报专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传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请他们来谈谈对高居翰学术价值的认识、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美术研究的视角差异等话题。
薛永年:他开拓了中国画研究新领域
高居翰的老师辈研究中国美术史,多是研究到宋,对元以后普遍缺乏研究,高居翰开拓了对元以后研究的新领域。早期美国对中国画史的研究,普遍的是做通史类、概论性的介绍,后来用西方的方法研究作品的风格形式,再进一步就是结合具体作品和画家做个案研究,往后就出现了两个学派。一个是内向观,从本体来研究,研究艺术规律时注重找内部的因素。高居翰所代表的一派,是研究艺术现象时注重影响艺术发展的外部条件,这是外向观,从作品的外部来解释中国画的发展。
高居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引导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传统的美术史偏重于内向观的研究,内向观的研究注重作品艺术品质以及大画家的艺术个性、艺术特点和艺术贡献与地位等,而高居翰所引导的方向是社会学的方向。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绘画的意义与功能,寻找绘画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反映了西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倾向,把艺术的研究从内部引向了外部,从大家名家引向了无名作品,是对传统研究的一种突破和调整。这种研究,一方面开拓了研究的领域,深化了研究内容的社会性,同时也存在着弊病,对绘画的本体考虑比较少,在作品真伪品质的研究上容易失误。
20世纪以来一直到“文革”,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一般都偏重于宏观上写一部美术史。但是高居翰的研究,既重视宏观,又重视微观,这个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过去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解释绘画的发生发展,往往就讲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如何,所以画就如何,缺乏对每个作品、每个画家、每个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现在我们也认为研究要深入进去,当然要有理论为指针,但要从事实引出具体结论。
高居翰善于将局部的研究成果与全局性的思考结合起来;把资料工作与基础研究结合起来;把个案研究与问题意识结合起来;以及以开放的国际视野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国际交流联系起来。
他还勇于推动学术前进,敢于挑战传统。虽然不是他每一个看法我们都赞成,每一个结论都无懈可击,比如对后期中国的写意画持否定的态度,对于《溪岸图》提出的观点,中国学者普遍都不赞成,但是这个勇气有利于学术发展。前人认为元朝以后的文人画是自娱自乐的,高居翰通过画家书信的来往和记载,写了一本《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研究把画家的生活方式、作品的市场流通结合起来,说明画家还是要卖画的。尽管不是所有的画家都以卖画为生,但他毕竟看到了这种现象,有一定深刻性。
高居翰是西方对元以后的中国画史研究最多,懂得最多的人,也非常辛勤、努力,成果很多。他也很注意与中国学者合作,我上世纪90年代就同他合作举办过“明清绘画透析”特展与研讨会,双方都受益。他是一位值得怀念的同行前辈。
陈传席:治学应“中西结合”
高居翰是我的老朋友,最早认识他是在1984年,我在安徽省文化厅筹备了一个研究明末清初黄山画派的学术研讨会,他也参加了研讨会,当时他的发言还引起了很多讨论。后来我1986年到美国堪萨斯大学做研究员,又有过数次接触。
当时我就发现他是一个著作狂,有点时间就打字写文章。他在美国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中,著作可能是最多的。
他最大的弱点就是不精通中文,研究中国美术史,不懂中文是个很大的障碍。另外他也能看些画,只是看得太好也是不可能,比如《溪岸图》就被他认定为是张大千伪造的。他这个人很聪明,只是对中国文化的先天感觉还是有缺乏。
高居翰写的中国绘画的著作,虽然相对简单,但因为是地道的美国人写作,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所以在美国影响还是很大,另外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也很地道。只是对中国画最后心有灵犀的那一点感觉还是缺乏。毕竟他是外国人,没有中国的文化背景。包括在美国的一批学者,即使是华语学者,因为他们从小就到美国去了,中国文化的底子不厚,谈到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也还是不够。所以,美术史要研究,最后还是要靠中国人。
美国对美术史的研究是用西方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如米芾写的《画史》,就谈这张画是怎么回事,那张画是怎么回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写他看过哪几张画,有哪几个画家。中国古人也只能这样记载,如果美国的科学处于那个阶段也只能这样记载,也没办法再深刻。后来有了照相技术,就可以把画拍下来看,毕竟用文字讲画,怎么讲都是抽象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外国人研究中国美术史最早的是日本,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美术史,其实也是在研究他自己的历史,因为中国文化是它的母文化,而且日本人的研究方法也是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的延续,不过他们又稍微深刻一点。最早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还是西方。
西方的照相技术出现以后,美术史的研究就跨上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欧洲的喜龙仁是西方研究中国画影响比较大的学者,他通过图片给了西方人直接的中国画视觉印象。他的研究虽然是资料性的,但给西方人了解中国美术史打下了一个直接的形象基础,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受喜龙仁的影响。
后来,西方的学者一直是主张在某一个专业当中深入研究,在科学技术上也是,不要求什么都懂。中国民间艺人说“一招鲜,吃遍天”,但中国士大夫是反对这种思想的,儒家讲“君子不器”“一物不识,儒者之耻”,所以传统儒家教育是讲究通识的。
美国的方法,是在一个小问题上研究深入下去,这种方法有长处。因为在中国,大而空的东西太多,什么还不知道就讲。美国的那种对小问题的深入研究引进来,对于学术界来讲是一种冲击。但是美国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从大的方面看问题和从小的方法看,就是树林和树木的关系。
我在美国待过,美国的学者反感通史式的著作。他们的主张是一部著作在世界上超过十个人看,就不是最好的著作,有几个专家看就行了。这个观点我也赞成,但是并不完全如此,《圣经》那不是好著作吗,全世界有多少人看?《红楼梦》不是好著作吗,何止十个人看呢?《论语》、《十三经》更是历代学者都在看,你不能说它不是好著作?所以美国人的方法也有偏见。
总要有学者来坚持一种从细小入手的方法,美国的这种方法论,我觉得要学习,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不要认为美国的方法更好,而丢掉我们自己的方法。现在,中国人要踏踏实实地做点工作、做点资料、研究一些问题,美国人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中国的方法和美国的方法结合起来去研究,才是最好的方法。
王镛:他是中西美术交流的使者
英国学者苏立文和美国学者高居翰相继辞世,这对于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是个重大的损失。他们两人都是西方专门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权威专家和代表人物。
从他们研究的方向来看,苏立文侧重于中西美术的比较,最近出版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关注的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历史。高居翰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绘画,最初是从中国书画著录入手,深受研究中国书画的瑞典学者喜龙仁的影响。西方的中国美术研究,往往都是从书画著录入手,根据文献记载和中外的书画收藏,特别是流散在西方的书画珍品展开研究。
西方学者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应该说在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上都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形成互补的关系。高居翰、苏立文和他们的前辈,基本上没有我们经常说的西方人所坚持的西方文化中心概念,他们都有世界性的眼光,相对来说比较公允和客观。但是,西方学者的价值观念和评价体系,和中国学者不太一样。他们毕竟受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的影响,在判断具体的美术现象时和中国学者的观点不尽一致。比如高居翰的有些观点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争议。他提出中国绘画史的终结论,认为中国绘画史在宋、元达到高峰后,基本上都是风格的重复,是终结的;还提出写意是中国晚期绘画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和我们现在提倡的弘扬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是相左的。
我认为,引起争议在学术上未必就是坏事,这比毫无争议的平庸结论更富有价值,更有启发意义。另外,他们把中国美术介绍给西方广大公众,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同时又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广到中国,对中国美术的研究起到推进的作用。他们是东西方美术,特别是中国美术史与西方学术交流的使者。他们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在向西方公众介绍中国美术历史方面,是无人取代的。
他们的去世在学术研究者层面,短期内会难以为继。因为文化传播和交流,要有一定条件,像他们具备这么丰厚学养和严谨治学态度的学者,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大量产生的。他们辞世,非常让人惋惜,同时也促使我们对他们的学术著作进行重新阅读和思考,从而推进中国美术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徐佳和:《时代肖像》,为谁画像?[图文] 徐佳和:《时代肖像》,为谁画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aijeyci23y.webp)
![张晓刚:川美现象在走下坡路[图文] 张晓刚:川美现象在走下坡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zfqojnvshb.webp)
![飘泊者的足迹:评杨劲松[图文] 飘泊者的足迹:评杨劲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5qtmccoi2a.webp)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图文]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3glduqduvp.webp)
![徐文生:牡丹文化与绘画[图文] 徐文生:牡丹文化与绘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w5fjulyeh2.webp)
![齐白石有无媚俗[图文] 齐白石有无媚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himtibxm3o.webp)
![湖北写实油画纵观[图文] 湖北写实油画纵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lxncunhtgk.webp)
![陈丹青:怎么看懂毕加索[图文] 陈丹青:怎么看懂毕加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3rsqrvzcua.webp)
![罗斯科:绘画当为奇迹[图文] 罗斯科:绘画当为奇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vt1nveioa3.webp)
![实验艺术被认可还是被招安[图文] 实验艺术被认可还是被招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dpkbtkosyi.webp)

![林散之与启功:近代书法中的一动一静[图文] 林散之与启功:近代书法中的一动一静[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itsjivgzqg.webp)
![绘画的态度[图文] 绘画的态度[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hgstxq1n2h.webp)
![皮道坚:让浩瀚的江流荡涤心灵[图文] 皮道坚:让浩瀚的江流荡涤心灵[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zrrheygkps.webp)
![艺术性和公共性 城雕美丑之辩[图文] 艺术性和公共性 城雕美丑之辩[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12fnpmugto.webp)
![历数全球最大胆的裸模 艺术献身or出位炒作?[图文] 历数全球最大胆的裸模 艺术献身or出位炒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4ekwubmka0.webp)
![熊广琴:画画不仅是技术更是学问[图文] 熊广琴:画画不仅是技术更是学问[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4fneijzivn.webp)
![让优秀的印论遗产不再流失[图文] 让优秀的印论遗产不再流失[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voqamcwhi1.webp)
![许仲敏的艺术场域[图文] 许仲敏的艺术场域[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gn0kjnztpx.webp)
![展览为何日趋乏味平庸[图文] 展览为何日趋乏味平庸[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naa30tdfv3.webp)
!["地下"文物应不应合法化?[图文] "地下"文物应不应合法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wapisuzg5y.webp)
![梁依云:当杜尚成为经典 有谁能来突破[图文] 梁依云:当杜尚成为经典 有谁能来突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mvfrb5fect.webp)
![周明智——墨舞神韵 自出一宗[图文] 周明智——墨舞神韵 自出一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twk2tqzi5r.webp)
![胡智勇:成化斗彩珍品不只有鸡缸杯[图文] 胡智勇:成化斗彩珍品不只有鸡缸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mai4j3zjjn.webp)
![孙良:“绘画艺术是单独存在的”[图文] 孙良:“绘画艺术是单独存在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cnvgkav05k.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