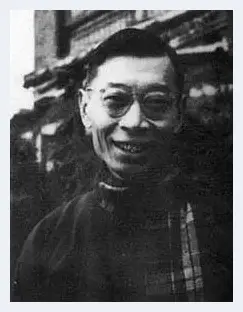
傅雷
在充斥着“墓志铭”式美术批评的当下,或许只有读读傅雷当年的美术批评,才能感觉到那么一点点慷慨激昂。应该说,“墓志铭”式的美术批评看似赞声一片,但细细品来,其传递的信息却是盖棺论定的“送终哀乐”。真正学术性批评的缺乏,正是导致当下美术创作和美术批评鱼龙混杂、鬼话连篇局面的根源所在。
近阶段,傅雷的美术批评被许多媒体大肆引用,因此也被很多人看作是美术批评的标准和经典。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虽然傅雷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翻译家和敢于直言的美术批评家,有些评论也言之有理;但有些时候却太“任性”,不免有那么一点点爱屋及乌了。
高鸿:美术批评岂能爱屋及乌
做美术批评的活儿是一件很费神的事,尤其是批评时下的画家。因为,过誉有违公论,过责有伤私情。不过,傅雷对此问题似乎不是那么在意。他既不怕得罪人,也不怕捧死人。按现在的时髦话说,他是极为任性的,几乎任性到目中无人。
在此,让我们先看看傅雷是如何评价齐白石和黄宾虹的:
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盗名;而白石尚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他只崇拜到金冬心为止)。宾虹则是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之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尤其可贵者,他对以前的大师都只传其神而不袭其貌;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仝、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是子久、云林、山樵的意境。
白石老人则是全靠天赋的色彩感与对事物的新鲜感,线条的变化并不多,但比吴昌硕多一种婀娜妩媚的青春之美。
他(黄宾虹)的写实本领,不用说国画中几百年来无人可比,即赫赫有名的国内几位洋画家也难与比肩。他的概括与综合的智力极强。所以他一生的面目也最多,而成功也最晚。六十左右的作品尚未成熟;直至七十、八十、九十,方始登峰造极。我认为在综合前人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在傅雷的眼里,齐白石不欺世盗名的辉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尚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他只崇拜到金冬心为止)”;二是“全靠天赋的色彩感与对事物的新鲜感,线条的变化并不多,但比吴昌硕多一种婀娜妩媚的青春之美”。
如此,傅雷这两句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齐白石之所以能够“全靠天赋的色彩感与对事物的新鲜感”,原因是“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而齐白石之所以“比吴昌硕多一种婀娜妩媚的青春之美”,恰恰是因为他的“线条的变化并不多”。通常说来,中国绘画的最核心要素是线条的丰富表现。如果“线条的变化并不多”,是难以深层次表现中国绘画的广度、深度和高度的。傅雷推崇吴昌硕,是因为“吴昌硕全靠‘金石学’的功夫,把古篆籀的笔法移到画上来,所以有古拙与素雅之美,但其流弊是干枯”。由此可知,吴昌硕的最成功之处,就是黄宾虹极力主张的“留意金石古文字,拟通之于画理,知前人之谬误,而思救正之”。至于说吴昌硕的画“其流弊是干枯”,我以为,这正是傅雷对吴昌硕绘画艺术解读的失察。因为仅仅是直观比较,吴昌硕的笔墨也完全体现了黄宾虹推崇的“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审美要求。
此外,傅雷对黄宾虹的推崇也是失察的。尽管黄宾虹是一位山水画大家,但也有其缺失之处——过于偏重文人画的成就及其历史作用。虽说我们为黄宾虹所提出的唐、宋是“辉煌之时”,元是“奋发有余之时”,“明画枯硬,清多柔靡”,以及“至道、咸而画学中兴”的“清醒”认识所深深折服,但其认为的“画学中兴”“有本之学”“道咸之间,考核精确,远胜前任。中国画者,亦于此复兴。如包慎伯、姚元之、胡石查、张鞠如、翁松禅、吴荷屋、张叔宪、赵撝叔,得有百人,皆以博洽群书,融贯古今”(黄宾虹《论道咸画学》)的论点,显然有失得当。
王伯敏在《中国画家丛书·黄宾虹》中就这一问题提出了有悖乃师的看法,称:“他(黄宾虹)所列举的这些文人画家,都不过在当时读书赋诗之余,偶尔画几笔的画家。他们在绘画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谈不上‘中兴’。不过,在康、乾以后,山水画家大都崇古复古,缺乏创新,虽重笔墨,风趣索然。尤其是娄东、虞山之后的‘小四王’,更是如此。到了道、咸,这些文人强调笔墨情趣,有别于一般摹古的作品,那倒是事实。”
我比较赞同王伯敏的实事求是之说。黄宾虹列举的上述诸画家理应不是“画学中兴”的中坚画家,只是画史有记载而已。按照黄宾虹所说的“及道、咸间,金石学盛,画艺复兴,泾县包慎伯,著有《艺舟双楫》,古来笔墨口诀,昭然大明于世”(黄宾虹《画学篇释义》),验之如上得“古来笔墨口诀”的“百人”,说他们“博洽群书”,倒也说得过去;而说他们于画学是“有本之学”“融贯古今”“画学中兴”,继而还说他们“已逾前人。民族所关,发扬真性,几于至道”(黄宾虹1952年自题《雨景写意图》),似乎过于牵强。
这抑或是黄宾虹斤斤于“笔墨”所形成的偏见。我如是说,自无点滴诋毁黄宾虹之用意。我们研究黄宾虹,应该将其视为一个艺术家,而不应该将其供奉在“神坛”上。从严谨的学术研究层面上来说,过分拔高是一种故弄玄虚。
作为一个艺术家,黄宾虹自有其思想观念的局限和鉴识上的偏颇。既然黄宾虹是“用很多中国文化的概念来诠释笔墨”,那他就不应该认为“释石涛尚有墨障未净”(黄宾虹《鉴古名画论略》)、“石涛大有才气,功力亦深;晚年署耕心草堂之作,用笔浮滑,殊少遒劲,顿失国画正轨”(黄宾虹1947年《与郑拙庐书》)、“石涛未免浮烟瘴墨之弊,开扬州八怪江湖恶习;因用笔太快,轻率浮躁之气未能涤尽。而学元人又多空廓软弱,不能实中虚、虚中实,兼虚中虚、实中实者,皆是笔不能压纸,何况入纸又透过纸背耶”(黄宾虹1948年《与曹一尘书》)。以理性的史学眼光来审视有清一代山水画,石涛是无可争议的开派型画家。他的绘画实践和其所著《苦瓜和尚画语录》,堪称震古烁今。为何在黄宾虹的眼里就变成了“顿失国画正轨”呢?
诚然,石涛的画有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大幅画作的章法时有窘迫的缺陷。但从整个风神气象来看,是纠偏了因袭成风的摹古恶习。仅此一点,以上黄宾虹为之推崇的“有本之学”“融贯古今”“画学中兴”“已逾前人。民族所关,发扬真性,几于至道”的“如包慎伯、姚元之、胡石查、张鞠如、翁松禅、吴荷屋、张叔宪、赵撝叔,得有百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综上所述,我们对傅雷的画评应该予以重新认识,不能因为他的地位和名气就一味盲目信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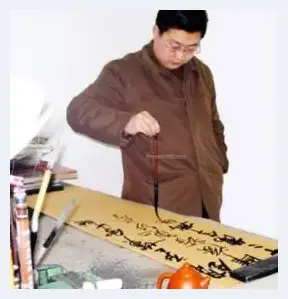
薛元明
薛元明:雷语不“雷人”,化作“雷雨”涤精神
稍稍对近现代文化史有一些常识的人,对于傅雷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概括傅雷的一生,有三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一是作为翻译家的角色,成就斐然,奠定了其在近现代文化史中的崇高地位;二是作为父亲的角色,一本《傅雷家书》让人家喻户晓,在家庭子女教育方面堪称典范和楷模,确立了其“中国好父亲”的形象;三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他以极其悲壮而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悲剧英雄。
其实,傅雷还有另一个侧面值得关注,那就是他善于和敢于在美术批评方面发声,对于当时声名显赫的画家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他的很多点评文字即便在今天读起来,依然觉得犀利敏锐、切中肯綮。
傅雷的点评不拖泥带水,三言两语便直中要害;不光说长处,还敢于说短处。其文章字字如刀,让人读起来大呼过瘾。傅雷在艺术方面是一个修养极为全面而又有天赋的人。他精通艺理,且能举一反三。
1931年秋天,傅雷自法国回到上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事美术史教学工作。与此同时,他发表了《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我再说一遍:往何处去?往深处去!》等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傅雷是“懂”艺术的,但他并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不懂得”艺术评论的固化套路,所以他的点评往往生拙、猛烈,散发着无穷魅力。这种集“内行”和“外行”于一身的特点,使傅雷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距离和视角对艺术进行评判,且独具一格,真可谓“雷语不雷”。
对于傅雷的点评,也许有人责其偏激。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偏颇。就艺术创作而言,需要偏师独出,成一家之言。艺术批评也是一样的道理,需要反映个人的见解。个人之见原本就是偏激之见。偏见有时才是主见。有了个人独特的视角,才有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倘若都是人云亦云,魅力何在?价值何在?我认为,只要没有人身攻击,关注的重点又是艺术本体,不管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评论,都依然在艺理范围之内。
美术批评往往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私人交谊的深浅,直接影响着艺术品评的结论。毋庸讳言,傅雷的点评文字也有个人喜好的因素掺杂其中。比如,傅雷对张大千等人的评论夹杂了一些个人意气,对黄宾虹和齐白石的赞美亦复如是。只不过,前者属于差评,后者乃是好评。
傅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不以润格的高低来评判书画作品的优劣。比如傅雷对黄宾虹的品评,我们可结合黄宾虹的自我评价来看。黄宾虹自认其画要50年后才能为世所知;但事实上,傅雷在当时就堪称黄宾虹的知音:“迩来沪上展览会甚盛,白石老人及溥心畬二氏未有成就,出品大多草率。大千画会售款得一亿余,亦上海多金而附庸风雅之辈盲捧。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竟标价至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同一时期,黄宾虹的一幅山水画仅能卖几万元或十几万元。可见,市场并不是判定书画作品好坏的标准,更谈不上是唯一标准。因为市场本质就是有钱人的游戏。傅雷有先见之明,早就看到了黄宾虹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明白,书画的好坏标准关键在于其对艺术史的影响力。
退一步讲,傅雷的美术评论虽受一些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但始终没有逾越艺术的框架而出现阿谀之词和人身攻击。这说明,作为一个批评家,傅雷是完全合格的。他对书画极度敏感,思想和灵感的火花喷薄欲出,激情、理性、睿智都具备了。当然,批评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有一些个人喜好,有三五知己好友或交恶对象都属人之常情。关键在于“度”的把握。如果一味迁就个人喜好,最终就会逾越底线,将批评变成一种客套的捧场或攻击的工具。
从傅雷的美术批评,我们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美术批评家要有担当。首先,批评家要有独立人格。丧失了这一点,一切都是空谈。其次,批评家应该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单纯的书画家角色。二是批评家本身的艺术素养要不断提高。有关善书和善鉴的争议由来已久。批评家不会写字、画画是否就一定不能胜任呢?这当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全面的艺术素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当下很多批评家的知识结构是片面的、割裂的,评论起来怎么会融会贯通呢?傅雷属于新、旧时代转型时的人物,其知识结构完满、圆通,且学贯中西、思路开阔。他的人格是独立的,其对艺术的认识是深刻的。三是对批评方式要有正确的把握。傅雷的品评属于顿悟式的,当头棒喝,醍醐灌顶,没有现今尤其是“学院派”批评的模式化和套路。时下,美术批评界存在的关键问题,是批评家丧失和缺乏独立人格,一切向“钱”看。即使是看起来高、大、上的批评,其实质也是空洞无物、不知所云或人云亦云,完全看不出批评者的底气和主见。这就好比削足适履,使得原本鲜活有力的批评变得枯燥乏味。其实,批评不需要套路,也不应该有套路。
傅雷极其犀利的批评,正是时下最缺乏的,值得推崇和效仿。这些批评文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今,读起来依然不觉得过时。从中,我能感受到“雷语”非但不“雷人”,反而是“雷雨”,涤荡着人的心灵,净化着艺坛污浊的空气。
“画理画论暧昧不明,纲纪法度荡然无存,是无怪艺林落漠至于斯极也。”(傅雷语)傅雷的批评体现了批评者应有的独特声音。如今的书画圈极其需要这样暴风骤雨式的批评,最好能来得更猛烈些。

李敬仕
李敬仕:一个艺术爱好者的情感判断
傅雷知识宏富,学养精深,除了翻译和著述之外,还发表了不少评画言论,其中不乏富有睿智的远见卓识,被许多人叫好和热捧。但仔细推敲他的这些言论,其中存在的情绪性偏颇的荒谬之处也显而易见。作为一个评画者,傅雷首先是位艺术的爱好者和欣赏者。欣赏活动的特点,表现为一种感觉和理解、感情与认识的统一。其中,感觉和感情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艺术欣赏虽和艺术批评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在性质上又有显著区别。王朝闻指出:“艺术欣赏是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艺术批评应当是对艺术作品进行逻辑思维的科学判断……通过一定的理论分析,对艺术作品客观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作出评价。”因此,作为学术研究活动的艺术评论,其价值观是中立的,即必须摒弃和超越个人的情感好恶,而采取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也就是说,艺术欣赏允许偏爱,艺术批评则要力求客观公允。傅雷为人桀骜不驯,秉性耿直而又嫉恶如仇,这使他评画时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因此,他的评论还仅仅停留在艺术欣赏层面而未进入艺术批评的层次,至多只是一个艺术爱好者的情感判断而已。
首先,从傅雷关于中国画的论述来看,他所钟情和褒扬的是文人写意这一风格的画。即使提及唐、宋,也是指王维、董源这类所谓“南宗”画家的祖师爷。否则,就是“甜熟”“恶俗”,是“画匠”“画工”。在这一点上,他和黄宾虹可谓情投意合。据画家陈佩秋回忆,她在上海美校读书时负责保管老师黄宾虹的画稿,同学们要临摹的话就到她那里去借,她发现同学们一临就像,包括她自己。对此,陈佩秋感到不满足。后来,她遵照另外一位老师郑午昌的建议,找了自己喜欢的五代画家赵幹的作品《江行初雪图》来临摹。她画了一个多星期,被黄宾虹看见了,就责问道:“怎么画这个东西?这是匠人画的。”但陈佩秋心里却认为:“文人画没有匠人画细致,匠人画要比文人画难画。”正是傅、黄的艺术观点的相同,即使年龄差距甚大,两人仍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二人频通书札一百余件,惺惺惜惺惺,互为赏识。关于傅雷的评论,黄宾虹称“名论高识,钦佩无已”;傅雷则赞誉黄宾虹“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之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仝、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是子久、云林、山樵的意境”,可谓是推崇备至。傅雷又说:“他(黄宾虹)的写实本领,不用说国画中几百年来无人可比,即赫赫有名的国内几位洋画家也难与比肩。”这种过甚其词的言说,不免令人掩口而笑。黄宾虹的画是经傅雷发现并推介的。他对黄宾虹的作品几乎没有提过一点意见,而且也不准别人发表不同看法。据说,施蛰存认为黄宾虹晚年因视力欠佳,其画越来越像个“墨猪”。此话一出即引起傅雷的大怒,批评施氏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画。另一方面,傅雷对以从画之大法出发,以塑造形象为核心的画进行贬斥。他指责张大千:“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何谓“外形为重”,何谓“唐人精神”,他没有明言细说。而我们所知道的张大千,其画筑基深厚,艺术业绩、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其对于工笔、写意,人物、山水、花鸟、草虫并臻佳妙,是位不可多得的全面型丹青高手。
其次,傅雷评画毫不忌讳地表现出一种浓重的感情色彩,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必要否定其画。批评标准应该是根据一定的社会思想和美学观点提出的。它必须适应一定历史时期广大群众的欣赏需要、审美趣味以及文艺发展的需要,而不是随着评论家的喜恶可以随心所欲改变的。傅雷对刘海粟的评价,却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矛盾现象。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和刘海粟交谊甚笃,有段“蜜月”时期。那时,他写了《刘海粟》一文,里面写道:“……愿你,海粟,愿你火一般的颜色燃起我们将死的心灵,愿你狂飙般的节奏唤醒我们奄奄欲绝的灵魂。”又,“一个真实的天才”,“我只问中国要不要海粟这样一个人”。这样高调的称颂几同肉麻的吹捧。回国后,傅雷因为看不惯刘海粟的所作所为,两人开始交恶乃至绝交。刘海粟的画也就在傅雷的眼中成了“从未下过真功夫而但凭秃笔横扫,以剑拔弩张为雄浑有力者,直是自欺欺人……鄙见只觉其满纸浮夸(如其为人),虚张声势而已……他的用笔没一笔经得起磨勘,用墨也全未懂得墨分五彩”。又如,他因看不惯张大千善于借势结交权贵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对他举办展览卖画,画价定得太高就愤愤不平,责备他“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吴湖帆率门人开画会推销作品,也受到傅雷的猛批:“……作品类多,甜熟趋时,上焉者整齐精工,模仿形似;下焉者五色杂陈,难免恶俗矣。此教授为生徒鬻画,计固良得,但去艺术远矣。”在傅雷看来,中国画走向市场,辱没了文人的尊严,必然江湖气十足,难免恶俗。
再次,是对人物画的忽视和贬低。面对当时卓有成就的徐悲鸿、蒋兆和等画家的人物画,他几乎视若无睹,不置一词。对于造型能力要求较高的人物画(特别是肖像画),文人们是难以涉足并忽悠大众的,所以以保持沉默为佳。即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或以“俗气”加以否定。傅雷在提及张大千的人物画时,批其“创作往往俗不可耐,仕女尤其如此”,又批徐燕孙“在此开会,标价奇昂(三四千者触目皆是),而成绩不恶,但满场皆如月份牌美女,令人作呕”。
本来,评画应该从画之本身优劣出发。譬如《清明上河图》被公认为中国画的经典作品,是因为这幅画的艺术水平令人叹为观止,并没有人去追究作者张择端的人品是优异或有瑕疵。傅雷则是从“画以人传”的思维出发,把道德置于画之上,把他看不惯的画家打入谷底。这样的评论类似戏剧界的票友,执拗地为了自己所心仪的演员,不惜和其他演员的粉丝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所以,他的画评基本上还停留在直觉状态的个人体验和感悟,甚至超出了作品本身的范围,借以宣泄个人的好恶和情思。因此,对于这样的画评,我们可以作为参考,但不必当真,否则自己也会掉入情绪偏激和偏听、偏信的泥潭之中。

![中国古代体育雕塑之美[图文] 中国古代体育雕塑之美[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0qve1sejhe.webp)
![彰显等级的古代“豪车”都长啥样?[图文] 彰显等级的古代“豪车”都长啥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d1lr2ex1sg.webp)
![陈晓烽:青铜器收藏者要有独立精神和见解[图文] 陈晓烽:青铜器收藏者要有独立精神和见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km2qharn5o.webp)
![陈逸飞《浔阳遗韵》应说是雅俗共赏[图文] 陈逸飞《浔阳遗韵》应说是雅俗共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aunam0sxw1.webp)
![清代画家黄慎:画到精神飘没处[图文] 清代画家黄慎:画到精神飘没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ssknjffxks.webp)
![以工匠精神打磨中华创世神话主题画[图文] 以工匠精神打磨中华创世神话主题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jbrif15uyq.webp)
![王献唐藏品毛公鼎全形拓等将首次面世[图文] 王献唐藏品毛公鼎全形拓等将首次面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2ryw01ar22.webp)
![神思之远 —— 许江的山水精神[图文] 神思之远 —— 许江的山水精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5hm3ch1gba.webp)
![从商场到机场 博物馆无处不在[图文] 从商场到机场 博物馆无处不在[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hg34ef5tli.webp)
![《2022年特别推荐当代最具收藏潜力艺术家》——刘继聪[图文] 《2022年特别推荐当代最具收藏潜力艺术家》——刘继聪[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shxkeebntu.webp)
![艺术先锋人物——画家丛建滋[图文] 艺术先锋人物——画家丛建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df5dgeseb1.webp)
![阿根廷与中国:跨文化的对话与沟通[图文] 阿根廷与中国:跨文化的对话与沟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sxuhy4duzs.webp)

![【名家风采】罗宁人物画作品赏析[图文] 【名家风采】罗宁人物画作品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3wdyw2mbbw.webp)
![艺术史的危机与当代艺术走向[图文] 艺术史的危机与当代艺术走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03mi51vfk2.webp)
![仙鹤是一品鸟古时常入画[图文] 仙鹤是一品鸟古时常入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fa0wbz0vcj.webp)
![吴冠南花鸟画:绚烂奔纵的写意[图文] 吴冠南花鸟画:绚烂奔纵的写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odv5xr5jx5.webp)
![走向世界的苍松画家禹化兴[图文] 走向世界的苍松画家禹化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b0jxnkzfzy.webp)
![米巧铭油画个展《无相》在泰国曼谷成功举办 [图文] 米巧铭油画个展《无相》在泰国曼谷成功举办 [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lyvmb5xd5o.webp)
![荣宝斋上海拍品赏析:林风眠《双鹭》[图文] 荣宝斋上海拍品赏析:林风眠《双鹭》[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ywmjiqziov.webp)

![丝绸之路北方行·赵文元研究八[图文] 丝绸之路北方行·赵文元研究八[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r23mjylez2.webp)

![百骥争辉 群像恢弘壮美 ·赵文元研究四[图文] 百骥争辉 群像恢弘壮美 ·赵文元研究四[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5p0eynaqim.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