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可弗兰西斯·培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具象画家,而那些未被其流畅笔触和丰富配色征服的人也许会给他贴上“堕落的怪物”或“20世纪灵魂暗面”之类的标签。岁末年初,这位已故英国艺术家的大型回顾展在澳大利亚举行。从中观众可以看到,随着他的人生进入不同阶段,他的技术如何发展,主题内容如何变换,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一生都记录在作品中。”

1957年,培根在伦敦巴特西画室。英国摄影师道格拉斯·格拉斯摄。

▲《纪念乔治·戴尔的三联画》
英国最富有的艺术家达明·赫斯特,在钻石头骨和鲨鱼尸体卖出高价之后,斥巨资收入弗兰西斯·培根的5幅作品,作为自己的收藏。俄罗斯巨富、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卡塔尔王室和英国足球俱乐部老板同样对培根趋之若鹜,他们甚至愿意支付8600万美元将他具有惊悚美感的作品挂在墙上。
他们都对孤独、扭曲的形象感同身受吗?他们也与培根的孤独、焦虑、尖叫的教皇心灵相通吗?
弗兰西斯·培根(1909-1992)无疑是20世纪杰出的艺术大师。他对油彩的全新运用构建出这个世纪的伟大形象,他不断扭动笔刷,辅以毛纺织物、蜡笔、调色刀、喷漆等工具和材料,甚至以创造/破坏的姿态将颜料投向画布,这类充满暴力色彩的图景,却是艺术家通过丰富耐心和独特品位精心设计的。

《卢西安·弗洛伊德肖像》
尽管很多人认可培根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具象画家,那些未被其流畅笔触和丰富配色征服的人也许会给他贴上“堕落的怪物”或“20世纪灵魂暗面”之类的标签。面对扭曲的人物肖像、尖叫的教皇、歇斯底里的商人和奇形怪状的野兽,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政时,曾经对培根有过一个著名的评价:“描绘恐怖图景的可怕男人”。
对培根的评价常常趋于两极,爱戴他的人相信培根是在为人类经验中的原始、不安和恐惧作像。艺术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常年将培根的作品挂在床脚,一刻都不愿意其离开自己的视线。而赫斯特对这位心中的英雄不吝赞美之辞:“培根与戈雅同等地位。他拥有这样的勇气,进入地狱,与黑暗的物质角力。他最好的作品,会让你战栗不已。”培根最好的图像,会让赫斯特想起“在噩梦中到过的地方”。
培根本人一次在提及自己的作品时表示,他希望自己的画看起来“就像有人刚刚经过”,“像蜗牛留下黏液一样,留下人类存在的痕迹”。
岁末年初,澳大利亚人将有机会亲身感受弗兰西斯·培根诱人的力量,这位已故英国艺术家的大型回顾展将在新南威尔士美术馆举行,展览呈现培根绵延50年的艺术历程,从1940年代他作为艺术家声名鹊起,至1992年他以82岁高龄去世。从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随着他的人生进入不同阶段,他的技术如何发展,主题内容如何变换,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一生都记录在作品中。”

《弗兰西斯·培根自画像》
半是醉鬼,半是僧侣
就像他的第一位艺术导师巴勃罗·毕加索,弗兰西斯·培根的作品也是他生活的视觉日记。毕加索,是充满激情的异性恋者,曾将6位不同时期的恋人肖像一一诉诸笔端。而培根是一位同样激情满怀的同性恋者,他的画笔同样描摹过6位恋人的面容。与此同时,二人同样都是危险的恋爱对象,在1998年的传记电影《情迷画色》中,现任007扮演者丹尼尔·克雷格成功演绎了培根的一位恋人——内心饱受挣扎的乔治·戴尔。
影片开头部分,笨拙的小偷从屋顶上摔落下来,被画家抓了一个现行。“脱下你的衣服,”培根上下打量着小偷,舔舔嘴唇,“来我床上,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戴尔和培根的关系是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1963年,54岁的培根搬进了伦敦南肯辛顿一处马厩改建成的二层楼房。从此也迎来了他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比自己年轻25岁的乔治·戴尔,一个英俊而健美的小偷,此后一段时期,他成了艺术家最钟爱的模特。
“培根会被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吸引,”英国艺术史学家马丁·哈里森说,“就像他自己的阴暗面,喜欢在肮脏的俱乐部游荡,酗酒、赌博和淫乱。培根热爱冒险,在艺术和生活上皆是如此。戴尔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对艺术一无所知,但他崇拜弗兰西斯,就像一个宠物小狗——这也将他置于危险境地。”
培根对于文学情有独钟,而他的画笔所描绘的也常常类似于狄更斯或巴尔扎克作品的现代版。如果你想一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伦敦风貌,或许可以看看培根作品选集。作家和艺术家、餐馆歌手、油滑的骗子、丰腴的女士、艺术赞助人、法国诗人、金融大亨、意大利富豪、摇滚明星……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等在这里汇聚一堂,在艺术家暴风骤雨般的画笔下,他们的脸孔被扭曲、肌肉被搬动,却又呈现出各自的鲜明特质。
那一时期,培根的狂欢宴饮是非常著名的,据说他每天午后时分会准时出现在惠勒饭店,通常他会点牡蛎和香槟,然后转战一些酒馆和俱乐部,直至深夜或凌晨。“我只想漂流……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看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1986年接受英国记者梅尔文·布拉格采访时,他作出如此表述。
在俱乐部,他被一大群马屁精和真正的崇拜者围绕着,同时,几位评论人朋友满足了培根对于知识话语的渴望。“即使与他们在一起,培根也会避免讨论任何与他的作品的意义有关的话题,”哈里森说,“他认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对观众紧张的神经系统创造一幅视觉冲击的场景。人们认为这很难接受,因为培根的作品似乎需要解释。”培根也不会回答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他相信生活在当下,“我由衷感到乐观——尽管对象是虚无。”
作为艺术家的声望渐长,每天花费十多个小时饮酒作乐,培根同时又保持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规律。无论前晚如何酒醉未眠,清晨6点至下午2点,他在沉默中独自作画,他相信创造力会像炼金术一般从自己的无意识中自然流露到画布上。很少有人进入过他的画室。“培根讨厌别人看他工作,”哈里森说,“这种面对面的方式让他感到局促,感觉对模特是一种伤害。”
通常培根会请自己的朋友、摄影师约翰·迪金为人物拍照,然后将这些照片留在身边作为素材。“培根需要在混乱中工作,”哈里森说,地板上堆满了即将倒下的书籍、杂志上撕下的纸张、成百上千幅照片,“许多照片折叠起来,给予培根以扭曲肖像的灵感。”颜料棒、笔刷、破布、香槟酒瓶和箱子互相覆盖、堆积,墙上泼洒着油漆,艺术家以此做颜色混合的实验。
即便是培根的恋人也从未获准入住他家,他为戴尔和其他随后的情人支付附近住房的租金,他们受到召唤时才会拜访他。培根从未想过家庭生活。“他讨厌所谓‘亲昵低语’的关系,”哈里森说,“他只喜欢性爱。本质上讲,他是一个孤独的人。”
肖像画是培根创作的根本。对培根来说,肖像画既不同于抽象艺术,也区别于模仿、类比、描写的艺术。在他看来,抽象艺术脱离不了装饰的蹩脚作用,而模仿、类比、描写艺术则被斥为插图。肖像画是培根“直接与神经系统对话”的方式,是培养直觉和对非理性的理解的路途。纵观培根的肖像画作品,可以看到,这些画前后一脉相承:没有表情,没有心理活动,表现的不是心灵状态,而是实际存在的状态。即便是描绘自己最亲密熟悉的朋友乔治·戴尔、卢西安·弗洛伊德、伊莎贝尔·罗斯索恩等人时也是如此。孤独、苦恼及精神上的无依无靠构成了肖像画的坚固底色,就像共同命运的特征,而这,也正是培根生命的底色。
画出人心中的恶魔
艺术家弗兰西斯·培根是17世纪初英国同名哲学家的哥哥尼可拉斯的后裔,他的曾曾祖母曾是拜伦男爵的亲密伴侣——拜伦曾以诗作向其致敬。培根的父亲原本是一位少校,退役后在爱尔兰成为驯马师。与光辉的家族传承,严厉的家庭教育相比,培根似乎是一个注定出走的异端。
年幼的培根患有严重的哮喘,并且对马和狗都过敏,他的父亲为了训练儿子的坚强性格,对此不以为意,甚至常常因其过于女性化的倾向而用马鞭鞭打他。1926年,培根因为在家中试穿母亲的贴身衣物而被父亲逐出家门。
爱尔兰已经显得十分遥远,而成人世界并没有什么恻隐之心。16岁的培根来到伦敦,依靠母亲信托基金中每周3英镑的支出而勉强度日,这段时期,拥有俊俏脸庞的培根同时混迹于底层社会和高雅厅堂两个世界,他做过女装销售员、仆人,也许还做过“小白脸”,他曾在泰晤士报上发布过“绅士伴侣”的求职广告。
1927年和1929年的巴黎之旅,成为培根走向艺术的转折点。巴黎蓬勃的艺术氛围感染了培根,而罗森博格画廊的毕加索画展让培根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回到伦敦后,完全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培根以“家具设计师”的身份开启了艺术生涯。不久之后,他结识了来自澳大利亚的艺术家罗伊·德·梅斯特,后者在绘画技巧及艺术史方面对他进行了指导。梅斯特是一位虔诚的信徒,热衷于耶稣受难的场景,而无神论者培根也受其影响,画了一幅鬼魅般的《受难》(Crucifixion,1933)。这件作品被视为革新的序曲,在赫伯特·里德的书《今日艺术》中,与毕加索的作品相对印刷。而今,该作已经成为达明·赫斯特个人的收藏,在澳大利亚进行展出。
不久之后,培根和牛津大学研究生埃里克·霍尔坠入爱河,这位富有的商人抛妻弃子,成为培根的恩客。二人在欧洲到处旅行,在蒙特卡洛豪赌,这一期间,培根也会偶尔作画,完成了一些实验性作品。
二次大战期间,培根因哮喘病而未服兵役,只是在尘土飞扬中勉强参与了国内救护。这一期间,培根的父亲去世了。培根和霍尔寻得一处拉斐尔前派画家曾经使用的画室,培根的保姆也前来与他们会合。在战火纷飞的伦敦城,培根与两位组成了临时的“选择家庭”。
1944年,二次大战激战正酣。35岁的培根以其高度原创性作品震惊了艺术世界——《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ThreeStudiesforFiguresattheBaseofaCrucifixion,1944)惊人的橙色三联画描绘了三个卑鄙、咆哮、畸形的人物,灵感来自希腊神话复仇女神三姐妹,同样也表达了介于动物和人、某个时代的噩梦和肖像之间的景象。培根解释该作品没有宗教意义,但象征着人类的残忍和邪恶。培根把这三幅习作看做自己绘画生涯的起点,其后,他开始创作一系列以受难、教皇、独裁者为主题的作品,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体现了对生命本能的敏锐洞察。
本次展览收集到一系列他早期“受难”系列的重要作品。“受难”是培根早期作品的核心,而“尖叫”是其经典意象。培根对于张开的嘴有一种迷恋。创作生涯开启之初,他曾对普桑作品《屠杀无辜》中妇女看着屠刀下的孩子发出的惊叫印象深刻。在巴黎,他也曾买下了一本图示嘴部疾病的书。当他看到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1925)的“敖德萨阶梯”一段时,护士戴着破碎的眼镜、脸上淌血地惊叫的图像深深震撼了他。另一件吸引培根的图像是委拉斯凯茨的作品《教宗英诺森十世像》。这些形象散落于培根的工作室,培根的天才技艺就是将这些各不相同的元素放入同一幅画中,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我就是一台搅拌机,”培根承认说,“目力所及,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被磨碎拌在一起。”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非常推崇培根的作品,他认为扭曲的脑袋画出了加诸于人身的看不见的力量,“这些脑袋的活动并非来自于通常所理解的运动,而是一些压迫的力量、膨胀的力量、痉挛的力量、压平的力量、拉长的力量,这些力量都作用在静止不动的脑袋上。仿佛看不见的力量从各种不同的方向在击打着脑袋。……它们划出了那些力量正在击打的区域。”
培根与贝克特、卡夫卡等人一样,都树立起了不能被制服的对象,德勒兹相信,让它们显形,才会带来胜利的可能性。
尽管培根的作品引起了艺术界的注意,但在当时,他具有挑衅性的画面很少有收藏家愿意买回家中。
1950年代,培根过着游牧生活,他暂借朋友的房子作为工作室,又在世界各地周游。他结识了新的情人彼得·莱西,他是前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二人臭味相投,但他们醉酒之后争斗变得升级,他们几乎掐死彼此。莱西后来搬到摩洛哥的丹吉尔,在酒吧中担任钢琴演奏家。培根定期会去拜访他的沮丧的情人,直到1962年,莱西将自己醉死在酒池肉林。
这段时间培根的生活漂泊无定,但艺术家创造了各种系列作品:教皇、穿西装的男子、动物、互相纠缠的男子。他们经常是为了某个展出而赶着绘就。如果细查培根早期作品的主题,就会发现,培根心中有太多魔鬼(独裁者、教皇以及其他父亲形象),他无法摆脱这些形象将注意焦点对准自己。直到中年临近,培根对于宏大、戏剧性主题的关注逐渐减弱,他开始意识到最丰富的创作主题来源于自己的身边、每日的生活。从1960年代早期开始,肖像画成为培根作品的核心,他将描绘的焦点对准了自己的密友和恋人。
艺术家及其追随者
1971年10月,培根在巴黎大皇宫举办大型回顾展。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巨大成就,他是第二位享此殊荣的在世艺术家,前一位是他的偶像,毕加索。
这一期间,他和戴尔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戴尔陪同培根来到巴黎,但无法接受汹涌而来环绕着艺术家的政要和崇拜者,将自己沉溺于酒精和药品中。哈里森介绍说:“戴尔带了一个委内瑞拉小白脸回到他和培根共同的酒店房间,但培根抱怨这位男士有脚臭,搬到了隔壁房间。”第二天,戴尔被发现死在厕所马桶上。
在开幕式那天早上,人们在酒店房间里发现了死于药物过量的戴尔尸体。培根以专业的姿态完成了当天的准备工作,维持着迷人形象,整晚和大家在一起。“但戴尔的死深深影响了他。他意识到泼洒金钱,制止戴尔偷窃,剥夺了他的身份,也终结了他存在的理由。”哈里森如是说。
不久之后,培根以死亡场景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三联画,其中一幅,是戴尔卧倒在马桶上,往马桶里呕吐。“1972年戴尔三联画的流动形象,似乎是生命从他体内泄漏而出,”哈里森称之为“令人难以忘怀的黑暗哀歌”,“是驱魔,也是驱除心中的愧疚。”
戴尔去世5年后,培根与一位小他40岁的英俊的吧台小弟约翰·爱德华兹展开了恋爱关系。培根再一次在新欢身上浪掷金钱,给他在附近购置了公寓,加上郊区的别墅。爱德华兹对于恩客全心全意,但与戴尔有重大区别。
“爱德华兹是一位好脾气、有爱心的年轻人。他崇拜培根,”哈里森说,“但他不会胡说八道。当培根开始大发脾气或者开始毒舌,爱德华兹会说,‘我现在要走了,弗兰西斯。’然后就会直接离开。”像戴尔一样,他对艺术一无所知,对培根的很多描绘他的肖像也鲜有理解。培根遗产基金会主席布莱恩·克拉克(BrianClarke)说,“约翰只是会问培根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总是把我画得像一只猴子?’”
晚年的培根变得更为平和,他与爱德华兹的关系更像父子之间的关系。培根将爱德华兹设立为自己的惟一继承人。
此时的培根对于后进画家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导者,在伦敦,他与卢西安·弗洛伊德、迈克尔·安德鲁斯、弗兰克·奥尔巴赫、里昂·科索夫、罗恩·基塔依等一干倾向于具象风格的画家被称为“伦敦画派”。其中,培根和小他13岁的画家弗洛伊德维持了30年的友谊常常为人所津津乐道。
英国艺术评论家威廉·费沃正在完成一部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他介绍说二人的友谊始于二战期间的伦敦,当时弗洛伊德21岁,培根34岁。
“比之同时代画家,培根的作品更令人吃惊,疯狂而无所顾忌。卢西安是他的崇拜者,他同样欣赏培根对于上流社会不屑一顾的态度。”费沃说道,“二人同样非常聪明、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欣赏严肃的谈话,也喜欢风趣和挑衅。他们都喜欢结交公爵和公爵夫人,同样热爱狂欢到黎明。”
“作为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孙子,卢西安·弗洛伊德理解培根复杂的性心理。”费沃进一步解释说,“对于年轻的卢西安来说,他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物,不顾一切的浪漫主义者。”
弗洛伊德和英国诸位名媛的爱情故事非常有名,而在他的床脚,他总高高挂着弗兰西斯·培根1953年创作的两个互相纠缠的男性裸体。“卢西安表示这一作品启发他良多,自己不会让其离开视线,”费沃说,“他甚至不愿意将之借出做展览。”
珍·威洛比女士在20多岁时成为弗洛伊德的挚友,有传闻说她将成为弗洛伊德第三任太太,最终并未成真,但二位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慢慢地,她积累下关于这两位艺术家的重要收藏。当弗洛伊德去年去世后,这幅作品而今悬挂在她的卧室中。
1975年,66岁的培根开始频繁前往巴黎。在那里,他继续拥有大量拥趸,澳大利亚艺术史学家艾迪·巴塔赫和莱因哈特·哈瑟特成为他在巴黎的邻居和晚年的挚友。
在他们家中墙上的醒目位置有一幅培根为夫妇二人创作的肖像。“我们认识培根4年后,有一天他突然宣布,‘我现在准备为你们画一幅肖像。’”巴塔赫回忆道,“我那时候蓄着胡子,弗兰西斯说,‘艾迪,你必须剃掉胡子,那是一幅面具,我看不到你真实的面容。’我不太情愿地剃除了胡须。然后培根说,‘哦,不,你留着胡子看起来更好。再留起来吧。’然后我又留起来了。他花了3周时间,在巴黎工作室创作我们的肖像,我们不被允许在那里观看创作进程,直到他完成。有天,弗兰西斯说,‘哦,今天我将你也摧毁了,莱因哈特。’他将作品交给我们之后,有一天,他又想要回去,把我的右眼再扭曲一些,但我说,‘不。’”
在他创作生涯的晚期,培根肖像中的形式变得没有那么扭曲,人脸逐渐浮现,他画面中的色彩变得逐渐黯淡、冷峻。培根不断回到自己的肖像创作中。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所有的朋友都像飞蛾般逝去”,只剩下“自己的老脸”还可以画。
未尽心愿和身后盛名
在所有关于艺术的讨论中,培根经常严厉批评他自己和其他艺术家,但很少提及他作品的意义。“弗兰西斯会说,‘一幅画需要开启我们内心感觉的阀门’——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欣赏者。”巴拉赫说,“他会说,‘绘画的意义不在于说明或装饰,但是为了丰富、加深生活的质量。’他也会面带微笑地引用《麦克白》:‘生活就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儿意义。’”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培根迷恋上一位英俊的西班牙年轻人何塞·卡佩罗。弗兰西斯仍然对生活充满了渴望,但他的胃口有所减弱。哈瑟特回忆道,“有一阵子,他希望自己被土葬而非火葬。他说他喜欢留下一个头骨的意象。”
“穷尽一生,弗兰西斯都在寻找自己的理想伴侣,”巴塔赫说,“他会说,我的梦中情人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身躯,配上尼采的心灵。”他希望对方比自己更强壮,身体上和精神上,完全征服他,掌握他。但培根从未发现过这样一位足球运动界的尼采。“弗兰西斯只想要一个同性的伴侣。”巴塔赫说,“他总是在二人关系中占据上风,然后抱怨他的情人过于弱智。”
1991年,培根在巴黎参观贾科梅蒂的展览。“他臃肿不堪,因哮喘频频感到不适。但我们享受在一起的时光。这是最后一次相遇。”哈瑟特说,“4月,培根在马德里的医院打电话给我。他违背医生的嘱咐,去那里拜访卡佩罗,却感染肺炎住进医院。他很担心不能如期来到巴黎和我们相见,我告诉他没关系,我们一直在巴黎,什么时候来都可以。3天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病逝的消息,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2003年,53岁的爱德华兹因肺癌去世以后,培根遗产基金会在其工作室中遗留的20幅作品基础上建立起来。
“弗兰西斯从不关心钱的问题,”巴塔赫说,“他会说,他作品的价格会在他死的时候轰然倒塌,也许一文不值。他只为自己绘画,如果别人喜欢他的作品,那是运气。”
培根的作品在他生前达到100万美元,死后10年,飙升至1000万美元。2008年,一幅1976年创作的三联画以8600万美元成交,俄罗斯巨富、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是这幅作品的新的拥有者。
他的收藏者还包括谢赫·玛雅莎,卡塔尔公主斥资5300万美元买入《教皇因诺森十世的习作》(StudyFromInnocentX,1962)。英国货币交易经理、托特纳姆热刺队老板约瑟夫·刘易斯和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史蒂夫·科恩都买入了他的“尖叫教皇”系列作品,花费金额未知。
“问题是,而今600幅培根作品中的大部分都已被主要的收藏家和博物馆得到。一旦有作品流入市场,可能会达到1.2亿美元的价格。”培根遗产基金会的主要代理人杰拉德·法乔纳托表示。
培根的鬼魂也许会比他的“尖叫教皇”叫得更为凄厉,当他得知自己身后的事情。奇特的是,他描绘英俊的小偷情人乔治·戴尔死在巴黎马桶圈上的三联画,现在价值超过1亿美元,荣膺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收藏品。
正如已故英国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2008年写道,“这个画家的鸡奸、施虐、恐惧和令人作呕的死亡,已经成为20世纪晚期英格兰最艰难、无情、抒情的艺术家,也许也是属于全世界的。”
链接: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MarioVargasLlosa)

培根作品《HeadI》(局部)
我想我是在跟某人的搏斗中被咬掉左耳的。但凭着剩下的一个小洞,我仍能清楚地听到世间的声音。我也能看得见,虽然得斜着眼,很艰难。尽管第一眼看上去不太像,但挂在我嘴巴左边的青紫色肉瘤确实是只眼睛。它呆在那儿,恪尽职守地捕捉形状和色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医学奇迹,足以证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进步非凡。我本来被那场大火宣判为完全失明——我不大记得火是怎么着起来的了,轰炸还是袭击——由于氧化作用,那场大火的其他幸存者全瞎了,头发也没了。我确实好运气,只丢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经过眼科医生的十六次手术,被救下来了。它没有眼皮还常常流泪,但足以让我看电影自娱自乐,尤为重要的是,可以很快发现敌人。
这个玻璃箱子就是我的家。我能从墙壁看到外面的人,但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我:在这个充满了监视的时代,这真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安全装置。当然,这个玻璃箱子防弹、防菌、防辐射,而且隔音。它还总是洒满了香水。
我的嗅觉极其灵敏,通过鼻子我尽享愉悦,也饱尝痛苦。我应不应该把它称作鼻子呢?这个巨大的膜性器官,能够闻到所有甚至最微妙的气味。我指的是这块浅灰色的东西,长着白色的疥癣,从我嘴巴开始,往下一直到我粗大的脖子。不,这不是肿胀的甲状腺,也不是患有肢端肥大症的喉结。这是我的鼻子。我知道它不好看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的极端敏感会给我造成无法描述的痛苦,比如附近有腐臭的老鼠或者恶臭的东西流过我住所的下水道时。尽管如此,我仍然崇拜它,有时我认为我的鼻子是我灵魂的居所(假设灵魂存在的话)。
我没有胳膊也没有腿,但我的四根残肢愈合得很好而且变得坚硬,所以我可以轻松移动,甚至移动得很快,如果需要的话。追捕者从未在追逐中成功抓住我。我的手脚是怎么残废的?也许是工伤;或者是一次意外,在我未出娘胎前,我妈为了减轻怀孕之苦而错吃了某种药(科学没能挽救一切,很不幸)。
我的生殖器毫发无伤。只要找到一位通情达理的性伴,我能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我喜欢通奸,但不精于此道。我经常体验早泄的失败和耻辱。我深信,人们享受排泄更甚于做爱。
我最大的骄傲是嘴。我嘴巴大张,并不是因绝望而喊叫。我保持张嘴是为了秀一下我可爱的白尖牙。哪个不嫉妒它们呢?两三颗牙齿掉了,其他仍然完好无损,还能吃肉。假如需要,嚼碎石头也不在话下。不过它们更喜欢撕扯小牛的臀肉,喜欢深深咬进鸡胸和小鸟的喉头。吃肉是神的特权。
我没有不幸,也不想别人同情我。我就是我,这就够了。知道别人过得不好是种很大的慰藉。
大概上帝确实存在,但在历史的这一刻,有没有上帝一点都不重要。这个世界会好吗?也许会,但用这个问题自诘何意义之有?我活着,尽管外表很丑,但我仍然是人类竞赛中的一员。
好好看看我,认识你自己。
(本文是略萨根据培根的作品《HeadI》写成的,发表于1985年6月28日法国的《新观察》杂志。秘莫一翻译。)来源:东方早报

![乾隆皇帝是收藏界的破坏狂[图文] 乾隆皇帝是收藏界的破坏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byyih3wfzl.webp)
![画家林墉:曾经的年轻艺术家偶像[图文] 画家林墉:曾经的年轻艺术家偶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xyuxvryvll.webp)
![霍春阳:中国花鸟意染时尚之都[图文] 霍春阳:中国花鸟意染时尚之都[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lfeoltpd0y.webp)
![深入生活 绘画当然不是臆造[图文] 深入生活 绘画当然不是臆造[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0xq455z3as.webp)
![官员落马后墨宝去留引发尴尬[图文] 官员落马后墨宝去留引发尴尬[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nm303gf2rd.webp)
![徐冰:以国际化思维滋养中国艺术[图文] 徐冰:以国际化思维滋养中国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3hxmahxknv.webp)
![影像批评:论摄影法则的遵守与打破[图文] 影像批评:论摄影法则的遵守与打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2ltk3t1koe.webp)
![周明智——墨舞神韵 自出一宗[图文] 周明智——墨舞神韵 自出一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twk2tqzi5r.webp)
![雕塑家的艺术跨界实践[图文] 雕塑家的艺术跨界实践[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nsap5f0aet.webp)
![鲁明军:许多批评家根本不懂艺术[图文] 鲁明军:许多批评家根本不懂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4hy4dc3ek3.webp)

![美国新抽象与中国极多主义[图文] 美国新抽象与中国极多主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smawsta3nb.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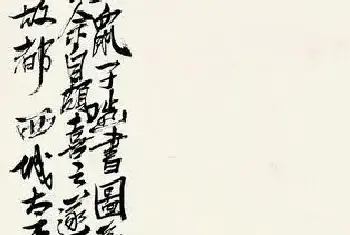
![中国为何稀缺好的当代公共艺术[图文] 中国为何稀缺好的当代公共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uwlqtql5pc.webp)
![徐冰:中国画在未来会变的越来越重要?[图文] 徐冰:中国画在未来会变的越来越重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3sq3jhebjn.webp)
![崔岫闻:大于艺术的是什么[图文] 崔岫闻:大于艺术的是什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s1m5yaf5pa.webp)
![王建勋:徜徉在线条世界里的智者[图文] 王建勋:徜徉在线条世界里的智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rciucl3z0r.webp)
![人之初:西方艺术史中的儿童形象[图文] 人之初:西方艺术史中的儿童形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04vqb2r1ne.webp)
![刘默:吴昌硕不断重复自己[图文] 刘默:吴昌硕不断重复自己[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oplp0sprma.webp)
![国画不当代何谈中国当代艺术[图文] 国画不当代何谈中国当代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jujjnox4ee.webp)
![玉雕的变革:从金蝉奖的设立看蒋喜的创新之思[图文] 玉雕的变革:从金蝉奖的设立看蒋喜的创新之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cmch4fzu1u.webp)
![戴丹:梵高的启示[图文] 戴丹:梵高的启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inoeyslohc.webp)
![比利安娜:艺术可以改变世界[图文] 比利安娜:艺术可以改变世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3i15ex3dpd.webp)
![水墨:当代中国本土艺术的“唯一稻草”[图文] 水墨:当代中国本土艺术的“唯一稻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qdd5r4cueb.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