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自己写得太多了”,这是《杨川庆诗选》后记中的一句玩笑,但事实上,这位龙江诗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走上文坛以来,已经发表诗歌数百篇,出版诗集四部,同时还有大量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作品不断面世。笔耕不辍是杨川庆的真实写照,在这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偏爱的是诗歌,正如他自己所言:“读诗写诗的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在这个诗歌生产与消费并不景气时代,杨川庆的这种执着并不多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在创作历程中自觉与各种流行的诗歌潮流划清界限,坚持回到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思想资源当中,以清醒而睿智的理性意识、富有张力的象征手段以及符合新诗美学规范的审美趣味来锻造其诗作的独特气质。
“以哲理作骨子”(宗白华语),这是五四时期以冰心、宗白华、朱自清等为代表的“小诗派”的诗学主张,杨川庆在部分诗歌的创作中显然接受了这一主张。比如,他在《夏天的失落》中写到:“六月杨花,洁白似雪/这是背叛夏天的品格/灵魂在如诗的季节走失/我听到哭声,来自收获的时刻”。在这四句诗中,意味着热情、喧闹和喜悦的“六月”、“夏天”、“收获”等三个语词,分别与“雪”、“走失”的“灵魂”、“哭声”三个意象对应起来,这既是诗人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也是以辩证的方式对世界、人生做出的理性思考。人群中总有一类个体是与众不同的,他们能够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在当下眺望未来,从总体出发把握事物的正反两面,这就是《夏天的失落》带给我们的启示。
象征主义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所借用的文学理论资源之一,也是当时名噪一时新月派、现代派等诗人所采用的主要创作方法。“努力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赋予抽象观念以具体的可感知的形式”是象征主义的核心创作理念,这一观念也存在于杨川庆的部分诗歌中。《寄北》是诗人身在上海时写的一首小诗,全诗如下:“此时,南方的阳光正在盘旋/我沐浴其中,思绪若起伏的海面/北方此时可在飘雪/我思念那里,那银白的田园”。这首诗的后两句构成了一个悖论,即前一句“可在飘雪”表现的是一种疑问,而后一句“银白的家园”则明确断定北方已经被雪所覆盖。也就是说,无论北方是否正在下雪或是否下过雪,在诗人心目中,它都必须是“银白的家园”。这样的表述在逻辑上显然是不成立或至少是不严密的,但从象征主义所追求的“内心真实”来看,刻在诗人内心深处的北方的形象,无论飘雪与否,都是一片洁白。此外,诗人还赋予北方纯净(银白)、恬淡(田园)的形象特征,并以喧嚣(盘旋、起伏)的南方对其加以衬托。
自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界谋求“进化”的欲望经久不衰,先锋小说、新生代诗歌、女性写作、小剧场话剧等等文学版块不断刷新大众的审美趣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五四文学革命所呈现的思想与美学资源,正不断失去其原有的影响力。在“前卫”与“传统”这个二元结构中,今天的文学界似乎更看重前者而视后者为创作活动中的绊脚石,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所言,“很少见到有人为自己支持一种传统而自豪,自称那是一种骄傲,并视之为好事”。然而,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五四新文学革命是否真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应当淡出文学的舞台,换句话说,五四所提倡的“为人生”的思想主张以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出现的种种写作思潮在今天真的就成为不合时宜的明日黄花了吗?事实上,五四新文学所提出的命题与当时思想界所探索的“现代性”理论密切相关,而这一理论正是我国当今学界所反复讨论并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实践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文学甚至其它领域回到五四传统寻求可借鉴的各种资源,便绝非当事者的思维惰性或因循守旧。
杨川庆对五四诗歌传统的坚守显现出诗人不凡的智慧,原因在于,与其说新文学革命是一种文学传统,不如说是一个文学思潮,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实践中,这个思潮并未功成圆满,它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而这种发展方向极可能是当下新诗脱离困境的出路之一。(李枫张宇宁)

![李彦君:培养文物专家的园丁[图文] 李彦君:培养文物专家的园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bdrau2tm1a.webp)
![米原康正:我的摄影与色情无关[图文] 米原康正:我的摄影与色情无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xr5ay2nbzz.webp)
![雕塑:凝固的快乐与哀愁[图文] 雕塑:凝固的快乐与哀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fydsqp1ryu.webp)
![徐冰阿什莫尔博物馆新展访谈[图文] 徐冰阿什莫尔博物馆新展访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1ffgizh1s3.webp)
![人民日报:“傍名”出版伤了谁?[图文] 人民日报:“傍名”出版伤了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f1g5ybogu0.webp)
![玉石与当代艺术的跨界实验[图文] 玉石与当代艺术的跨界实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uce1sfkfmm.webp)
![刘小东谈利森画廊个展[图文] 刘小东谈利森画廊个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3ssxhzk0pn.webp)
![崔岫闻:大于艺术的是什么[图文] 崔岫闻:大于艺术的是什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s1m5yaf5pa.webp)
![诗书画印的守望[图文] 诗书画印的守望[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x5n3mzhq2f.webp)
![与山传神 与花写照—浅析马健郡的国画[图文] 与山传神 与花写照—浅析马健郡的国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foedcyewdo.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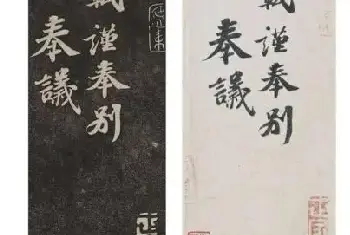
![谢稚柳与陈佩秋的书画艺术[图文] 谢稚柳与陈佩秋的书画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arwbysuuct.webp)
![自杀漫画呈现民国社会病态风潮[图文] 自杀漫画呈现民国社会病态风潮[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twvfjkliwe.webp)
![“平衡”的艺术:厨房天平设计[图文] “平衡”的艺术:厨房天平设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nyucaw1xhk.webp)
![谁是艺术家?[图文] 谁是艺术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5vdu2ccxjs.webp)
![最后的Art HK 最好的时代[图文] 最后的Art HK 最好的时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e0mz0e5aiz.webp)
![文人画的文化价值正在回归[图文] 文人画的文化价值正在回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ara4lj140t.webp)
![人之初:西方艺术史中的儿童形象[图文] 人之初:西方艺术史中的儿童形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04vqb2r1ne.webp)
![熊广琴:画画不仅是技术更是学问[图文] 熊广琴:画画不仅是技术更是学问[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4fneijzivn.webp)
![中国动漫产业现状:量高质低 缺乏创意是软肋[图文] 中国动漫产业现状:量高质低 缺乏创意是软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dlohbv015g.webp)
![艺术评论家的幸与不幸[图文] 艺术评论家的幸与不幸[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ufeyhhdbxx.webp)
![回归自然的心灵--栾可新山水画色彩浅谈[图文] 回归自然的心灵--栾可新山水画色彩浅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svsplj1e5f.webp)
![梁依云:当杜尚成为经典 有谁能来突破[图文] 梁依云:当杜尚成为经典 有谁能来突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mvfrb5fect.webp)
![书画临摹作品有无著作权?[图文] 书画临摹作品有无著作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25ovvj5uff.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