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河,湖北沙洋县西部的一条小河,发端于北部山地,蜿蜒曲折,犹如长龙,向南流入后港镇边上的长湖。河流中段有一个小村庄,叫城河村,而村子所在地就是城河遗址。现在我们知道,遗址本身是5000年前的一座古城。因为年代久远,我们已无法考证这些名称的使用先后,但是,一河、一村、一遗址,都与“城”字有关,无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佳提示。

城河遗址鸟瞰 彭小军供图
屈家岭的力量
在中国古代可以稽考的先秦文献中,长江中游一直是一个荒蛮的地区,以至于被《史记·货殖列传》形容为“无积聚而多贫穷”,直到西周后期楚国崛起才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气势。但新中国近70年的考古研究证明,长江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还有一段时期足以和当时的黄河流域、长江下游媲美,这就是距今5100~45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
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群星闪耀,文明之源满天星斗。屈家岭文化占据江汉丘陵地带,自身社会发展独具特色,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显示,随着庙底沟类型、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存的衰落,史前文明出现大范围的动荡整合。此时,屈家岭文化开始北进河洛、西入关中的扩张,势头强劲。在强势扩张的背后,是屈家岭文化对长江中游的长期经营和不断整合。他们不仅主导完成长江中游文明共同体的构建,将长江中游的大多数区域纳入他们的文化版图,而且在大洪山南麓和洞庭湖西岸修筑了十余座古城。这些古城的面积大小不等,从洋洋百万平方米到区区数万平方米都有。屈家岭文化正是借助不同层级的古城及其周边的附属聚落,共同维系着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共同体的完整。故此,对相关古城开展考古研究,是探索屈家岭文化社会结构的关键钥匙。
由于之前的条件所限,学术界仅仅对最大规模和最小规模的城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大量中等规模的城址一直没有开展过持续的聚落考古工作,从而影响了屈家岭古城网络体系的整体研究。为弥补这一缺憾,2012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开展了系统发掘和持续研究,希望以此了解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的功能布局和社会结构。
长达7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城河遗址的保存面积约70万平方米。作为屈家岭文化在汉水西部的一个区域性权力与信仰中心,它以体量宏大的城垣、规则有序的水系、引人关注的大型院落建筑、葬俗独特的墓地等一系列相关遗存,再次实证了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的物质文化成就,为我们了解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的功能布局打开了一扇窗户。

出土的钺 彭小军供图
筑城的智慧
种种考古迹象为我们描摹出这样一幅画面:5000年前的一个冬天,城河的先民们开始修筑这座古城。地点早已选定,但那里被各种杂草灌木之类的枯枝败叶覆盖着,砍伐清理太费事。于是用火,一烧了之。城墙用料显然是就近取材、因地制宜的结果。先民们把附近挖来的土进行混合加工,再一层层堆砌、夯实,城墙就一点点“长高”了。
水是生命之源,不可或缺;而南方又是多雨的,易成水患。如何处理水,体现着先民的智慧。遗址上处处可见先民对水的利用和改造。在城墙内坡的地面,有规整的排水沟渠,雨水顺着城墙流到沟渠中,再汇聚到固定区域,有效防止了水流对城墙根基的冲刷破坏。城墙的外侧,有完备的“护城河”环绕,最宽处达61米,最深处有6米以上。与“护城河”呼应,城墙东南、西北及北部中段均设立有水门,城外的河水从西北、北部两处水门进入城内,又分别从西、东两处水道汇集于东南水门,进而借助人工沟渠排至城外的自然河流。如此,既保证了城内大量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又避免了旱涝之灾,体现了娴熟的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模式。
在城内的最中心位置,有一座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大型院落建筑。这座建筑规模宏大、位置特殊、形制独特,或是城河城的“中枢”。院落东侧是一片广场,地面是用加工过的红烧土颗粒搅拌泥土铺垫而成。院落南侧有陶窑生产区和祭祀活动区。当年的王者,住在城内最中心的位置,通过信仰垄断,在广场上向万千族人宣示自己的权力。或许,也是在这个广场和祭祀台上,城河的英雄们,带领着他们的族人护城挖沟,改造大地,开启了各自的不凡人生。

出土器物组合(一) 彭小军供图
神秘的葬俗
科学的考古发掘向我们展示了城河先民生产生活的图景。那么,他们死后又去了哪里呢?
在事死如事生的史前社会,先民们对于墓葬的营建极为重视,常常投入很大的成本和精力。墓地的发现和揭露,能够帮助我们真切了解古人的社会结构,为探讨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最为直接的材料。因此,城河墓葬区的寻找一直是考古队割舍不下的学术任务。
在城河首次发掘之时,就有老乡向考古队提供线索,在北壕沟的外侧曾捡到带孔的石斧。考古人员敏锐地意识到,老乡所说的“带孔的石斧”很可能是“钺”。钺是身份等级的象征,是权力的标志,一般出现在重要的墓葬里。几乎可以断定,城河遗址的墓葬区应该在城址的北部。
2017年底,由于一次偶然的、巧合的,却极为关键的勘探,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发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墓葬。随后,确定了整个墓地的墓葬数量不少于235座。尽管这些墓葬的主人只是城河先民的部分群体,但墓地中展示的葬仪足以体现当时的社会观念。
与新石器时代的大多数墓葬一样,墓地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另有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在偏洞中。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而且保存状况相当不错,这在长江中游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见。葬具痕迹包括结构复杂的独木棺和板棺。有的独木棺直径达1.5米,有的在棺内还设有隔板,隔板下面放置随葬器物,板上放置墓主。这是在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史前独木棺,为了解当时葬具结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物质支撑。
我们还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合葬习俗。位于墓地最中心的第112号墓,面积达22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墓葬。这座大墓是“同穴三室墓”,即同一个墓坑,墓底部用土梁隔成3个墓室,每个墓室内各埋葬一座独木棺。中间墓室的主人是一名成年男性,他的随葬品包括体量巨大的棺木、暗红色漆盘、大量的磨光黑陶,以及玉钺、象牙器等,这些都足以显示其高贵的身份。尽管两侧墓室人骨无存,但无论从棺木体量和随葬品数量来看,都无法与中间墓室等同。葬礼的过程也极为隆重,不仅随葬了上述大量器物,还在棺外放置了猪下颌骨,并且在填埋过程中,在中间墓室上方摆放了大量的带盖容器,以视对死者的尊重。3座棺木内都发现了象征军权或王权的玉钺,而且刃口全部指向西方。
在这座大墓的西侧,有一座同穴双室的合葬墓,编号第233号,“打破”了112号。打破,是考古学的科学表述,其实考古人员更倾向于这是一种“对接”现象。233号的墓主在下葬的时候,葬礼的操办者应该知道112号的存在,而且有意识地在112号的西端开挖了同穴双室的墓坑,从而形成了一个“五连间墓室”的特殊形制。有意思的是,233号的两个墓主都是女性,并且都随葬了纺轮,似乎暗示城河先民有着“男持钺、女纺线”的性别分工。
类似于这样的大型墓葬还有5座,面积都在10平方米以上,分布于墓地的不同位置,并且都是同穴双室合葬墓,墓室内常见体量巨大的棺木和丰厚的随葬品。通过对保存下来的人骨鉴定可知,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都是头朝城内,表现出了对生活场所的眷顾。在它们的周边,则分布有数量不等的中小型墓葬,头向不尽相同。不过,也似乎存在部分墓葬围绕大型墓葬分布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准确关系有待于古DNA信息的最终解读。
墓地所在的王家塝是一处自然岗地,是遗址所在范围的海拔最高点。活着的人们选择这处岗地埋葬他们的祖先,既不占用城内宝贵的土地资源、影响生者的日常生活,又能够让先祖们矗立在制高位置,“俯瞰”全城,佑护子孙,体现了“生死有别”的理念。更为难得的是,这个地点恰恰是城外河水进入城内的必经区域,或多或少体现了水在人们心中的特殊地位。

“五连间”墓葬 彭小军供图
古城的密码
城河城址的数次发掘,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全面发掘,弥补了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系统研究的缺环,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
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这些墓葬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其社会发展程度与同时期的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达到了同样水平。

出土器物组合(二) 彭小军供图
对屈家岭社会发展程度的新认识,也为我们理解和观察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势扩张提供了新的基点。城河遗址发现的黄土台、筒形器、四耳器等祭祀遗存,表明屈家岭文化古城有着共同的祭祀、信仰体系。规划有序的大型城垣和人工水系,显示了屈家岭先民在对抗自然、改造大地过程中的决心和能力。墓地中出土的直壁圈足杯,在庙底沟类型末期到仰韶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中均有发现,是屈家岭文化扩张的典型例证。大口缸在大中型墓的出现,独木棺在大墓中的流行,以及钺在大墓中的显著地位,则表明屈家岭文化社会上层广泛参与了周边地区的深入交流。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极大参与了史前中国的形成过程。
现在,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城河遗址还有很多故事等着考古人员去发现、去聆听。考古队员犹如穿越时间隧道般,奔赴那场五千年前的葬礼,与城河的先祖们面对面的交谈……

![书法热潮背后,蕴含怎样的文化信息?[图文] 书法热潮背后,蕴含怎样的文化信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isordblasp.webp)
![谁在哭泣?美国国会大厦里的艺术品[图文] 谁在哭泣?美国国会大厦里的艺术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v03qtjsmjs.webp)
![欣赏儒将刘子贤将军书法作品[图文] 欣赏儒将刘子贤将军书法作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1s2vrsyx5w.webp)
![板胡乱弹[图文] 板胡乱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icxqywqw4a.webp)
![灵性而澹然的水墨世界[图文] 灵性而澹然的水墨世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bndtyrpj0y.webp)
![激扬的水墨诗情 王涛的水墨人物画[图文] 激扬的水墨诗情 王涛的水墨人物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zj0jdzjyco.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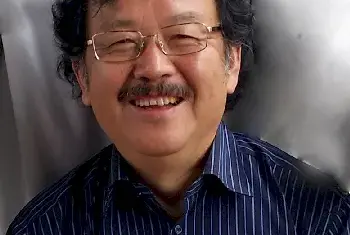
![翰墨丹青:品读孙阳老师的国画艺术[图文] 翰墨丹青:品读孙阳老师的国画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ijnrrl0hmt.webp)
![高士奇行书七律诗轴赏析[图文] 高士奇行书七律诗轴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qo140fnp0r.webp)

![党旗飘飘ーー喜迎建国七十周年”樊萍艺术欣赏[图文] 党旗飘飘ーー喜迎建国七十周年”樊萍艺术欣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ecxicoi5bs.webp)
![我与邓之诚先生的书缘[图文] 我与邓之诚先生的书缘[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retgzuomqx.webp)
![“党旗飘飘喜迎建国70周年”尹天石艺术欣赏[图文] “党旗飘飘喜迎建国70周年”尹天石艺术欣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qspzdz4pbu.webp)
![非遗如何传承保护:江河不断,我们不散[图文] 非遗如何传承保护:江河不断,我们不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vfoe0f3bf0.webp)
![艺术品价格打骨折 该挤挤水分了[图文] 艺术品价格打骨折 该挤挤水分了[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ijhiewa2av.webp)
![2019年艺术市场方向:投机主义与大型画廊的主导[图文] 2019年艺术市场方向:投机主义与大型画廊的主导[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yt302hx30s.webp)
![彩墨丹青 董春莲老师泼墨作品赏析[图文] 彩墨丹青 董春莲老师泼墨作品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zqjsv5celz.webp)
![井上豪:西域壁画中的粉本与使用方法[图文] 井上豪:西域壁画中的粉本与使用方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1rz3acb1hn.webp)
![好的人物画必有技术难度[图文] 好的人物画必有技术难度[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omtcb4cs3h.webp)
![潘天寿“一棵松树”2亿多![图文] 潘天寿“一棵松树”2亿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3jj5gxzogt.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