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不存在随随便便的看,更别说观看。观看拥有其自身的逻辑,历史,结构,要求,条件。特殊的“道”和先验原则使其区别于,优于对各个个体无差异的经验和体验。西方文明中的视觉中心主义,除开视觉相对于其他感官的优先性,更首先确立的是视觉和观看中那无比丰富,繁杂和霸道的等级制。在艺术范畴中这就意味着,人观看的方式决定了他是否可能成为观看者,决定了他的观看中能否真的出现艺术。
但这篇文章试图探索另外一面,观看又或者一切艺术经验的非等级制层面:它在人的主动和特别的观看之外的能动层面;而以这一点又得以建立另一种等级制,更高的“道”。观看者总同样被观看着:这是常识。但如果不将这种被观看关系直接推进到人际,而是首先将它挽留于艺术品和观看者之间,这就变成了神秘:因为这意味着观看者被艺术品观看着,意味着艺术品回望着每一位前来一睹其芳容的观看者,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交流,造成影响。

在这个神秘的维度中,艺术品真正地不可被观看所耗尽和占有。艺术品不是可以被消耗和购买的物资和商品,也不仅仅是艺术理论所研究的元素,风格,符号的集合,而是某种超越实在之外的精神之物,某种指向甚至命令——它等待着在这种神秘的物对人的指派中实现于每一位观看着的被观看者那里。
但它不可能是某种直接指导和规训人们的指示或标语,更不是互动艺术中发放给参与者的行为指南。语言和视觉符号的多义性,歧义性(并因此:虚无性和反讽性)总是不可剔除的,在艺术馆中更是如此,因为正是这一点才让其可能成为艺术。艺术确实来源于生活,但它同样指出非它那般的生活根本不是生活:它高于生活的那个部分表现为这种反过头来的否定性——它指出生活的非生活部分和可能性。
下面,我用一个或许太极端又或许太直接的例子来尝试展示这种被观看之道。太极端是因为这种分析或多或少确实源自我自身所感受到的“被观看体验”,因而仅是私人假设。太直接是因为这件艺术作品确实拥有一个看向画外的眼神。但特殊之处在于,这个眼神并非来自于某个被描绘于古典人像画中的无名贵族,画家也并未因为想让画像栩栩如生而让该眼神与观众直接对望。

Le Cyclope (The Cyclops), ca. 1914
Oil on cardboard mounted on panel
65.8 × 52.7 cm
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在《独眼巨人(Cyclops)》中描绘的巨人形象正从画面前端的山岗之后探出,扭过头来,仿佛正为了寻找什么而望向画外。向上微翻的巨大独眼占据着面孔的正中心,使它发散出明确的非人气息。同时,一位裸女熟睡于前景的草丛中,她的姿势暗示她似乎没有被巨人的出现所惊扰。
考虑到雷东的整个创作史,这张于去世前两年完成的画作拥有非常明确的特别地位。

l y eut peut-etre une visionpremiere essayee dans la fleur
(There was perhaps a first vision attempted inthe flower),
1883
这位法国象征主义画家处于近代和现代艺术交接的时间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过渡阶段。在他之前的诸多艺术巨匠依旧发挥着余热,在他之后的现代艺术大师也即将登上舞台。

The Eye like a Strange Balloon Mounts toward Infinity
(L'Œil, comme un ballon bizarre se dirige vers l’infini),
1882
雷东的艺术创作也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被称为“黑色(Noirs)”时期,大多以黑白版画为主,其中描绘着各种带着人类神情的奇怪生物,比如微笑着的蜘蛛,自主飞行的眼球热气球。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作品当属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所绘制的插画,暗示全知之眼的眼球形象就出现于此。

L'Araignée souriante
(The Smiling Spider), 1881
传闻经过一次不知名的重病,他完全转入了色彩,其中绚丽斑斓的背景是其主要特色。在这个时期中,创作的主体形象大多是沉静于内心的人,他们呆滞,忘神地注视着花朵,不与观众产生任何直接交流。除此之外,雷东也经常创作拥有浓厚象征性的作品,比如驾驶马车飞天向上攀升的阿波罗等。这些绚烂画作中的色彩背景直接启发了后来的色彩主义者,并衔接于诸多现代思潮。

Mystery, circa 1910
这两个阶段不仅在风格上,更在思想表达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作为象征主义画家,雷东反对印象派中将所见色彩看作为真实的感官科学态度,并反对理性主义者的唯理论。他认为只有心理,自由想象,无意识,梦境等非理性状态才是自然的,才是真实的——之后的超现实主义,自动绘画等与之一脉相承。因此,雷东在画中表现出的人物以及人物对于花束的出神注视都更多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这种出神状态暗示人物从外在意识中逃逸,专注于真实的内在。因而,后期色彩画作中的炫丽背景都更应当被理解为对难以直接表达的心理背景和色彩的间接表达尝试——如他本人所言:“让可见之物的逻辑服务于不可见之物”。

这就是被观看之道,观看唤起的行动力,随波逐流的主动性。它要求艺术理念在观看者那里实现,要求观看者自身的实现。它是要求人进行自我实现,进行行动的绝对命令:艺术品将观看者制成作品,使他们一同合流于该理念所实现的新世界,新生活之中。
因而,这就确立了跨越观看之道的等级制,作为艺术理念的普遍人性与作为观看者的单一个体间的不可逾越的差异。并在二者之间给出了那唯一的大“道”,即上“道”:向上与强力合流为一。

Closed Eyes,Odilon Redon
c.1895
简单概括:如果说前期的黑白版画中的非人怪物依靠它们人性的神情而直接表现了作为真实人性的非理性(这赋予这些画作明显的诡异气息),那么后期迷失于冥想和内心的人物则表现的是远离了意识和理性却并不因此变得野性的人性,反而正是以此他们才得以真实地存在。这就是他后期画作中的结构:为了不让背景色彩被约减为装饰色块,而是维持为具体的心理真实,为了展示这不可展示的具体内在,画中的人物必要地出神,不在场,离失于背景之中。
回到我们的例子。《独眼巨人》这张画作的特殊之处首要在于,前期和后期的标志性形象共同出现了:独眼向上微翻的巨人暗示着精神性的启示(神启)和非理性,非人的结合与同一,而熟睡于草丛中的裸女则联系于那些沉静于内心的呆滞人物,因此仿佛可以认为画中的背景也还是她的内心世界。

通过仔细的观察,我们发现没这么简单。如果确实将女人与背景的关系理解为沉睡的外在和真实的内在的关系,那么前景与背景的差异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并根本的,即具象与抽象的绝对差异。并由于左侧的远处背景的边界异常模糊,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巨人并非是从远处的山野中探出身子,而是位于草丛山冈与色彩空间之间,前景与背景的根本差异之间:独眼巨人似乎从空无之中,从女人的熟睡现实和她的心理真实之间的夹缝中出现。

独眼巨人就仿佛于梦中惊扰女人睡眠的噩梦,它确实属于她的心理真实,却不可避免地直接干预她熟睡着的现实状态:它的一只手搭在了画面右侧的山冈上,似乎要从这个空无之中跨入现实。同时,只有当女人的现实之眼熟睡时,她的真实之独眼才会睁开,同时看待这两个世界,真实与现实的同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独眼巨人的眼睛是神启之眼,全知之眼。

![乌菲齐美术馆:“鲜花之城”的艺术殿堂[图文] 乌菲齐美术馆:“鲜花之城”的艺术殿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px5xvmj1eh.webp)
![在亚洲天王专场中看大师向天才致敬[图文] 在亚洲天王专场中看大师向天才致敬[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j5xxamxfuz.webp)
![埃贡·席勒:被艺术史遗忘了50年[图文] 埃贡·席勒:被艺术史遗忘了50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siw2d1qrb4.webp)
![2020年特别推荐艺术先锋人物:著名画家赵英斌[图文] 2020年特别推荐艺术先锋人物:著名画家赵英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xmbuzxbmzf.webp)
![艺术市场合作呈现激增新态势[图文] 艺术市场合作呈现激增新态势[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hiyslto12k.webp)
![阿钵:禅修路上的“摇滚”[图文] 阿钵:禅修路上的“摇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p0mj23c0vu.webp)
![天地玄黄,金墨无界——李志松在古今中西之间构建永恒[图文] 天地玄黄,金墨无界——李志松在古今中西之间构建永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4oa030jztv.webp)
![在丰子恺翻译中轻轻飘过的“未来主义”[图文] 在丰子恺翻译中轻轻飘过的“未来主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k4x0ia3yzb.webp)
![你欣赏的艺术品都是垃圾?[图文] 你欣赏的艺术品都是垃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mmzp32cufd.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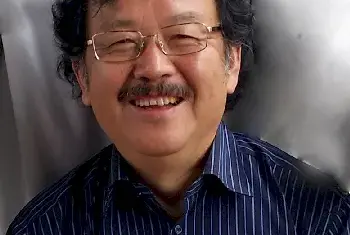
![为啥欣赏书法往往变成各说各话[图文] 为啥欣赏书法往往变成各说各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1qvp3cw5u1.webp)
![疫情影响全球艺术 藏家愿意在线上为艺术买单吗[图文] 疫情影响全球艺术 藏家愿意在线上为艺术买单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lcxd001s1s.webp)
![陈振,以写意笔墨为精神气韵,把热带雨林花鸟描写的生动而传神,自由而生机[图文] 陈振,以写意笔墨为精神气韵,把热带雨林花鸟描写的生动而传神,自由而生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xmokwpvj2l.webp)
![翰墨丹青写风骨│品读著名画家李建军笔墨精神[图文] 翰墨丹青写风骨│品读著名画家李建军笔墨精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4ysj1m0syd.webp)
![扬州画派:名臣盐商与画家[图文] 扬州画派:名臣盐商与画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a3qfoj5i0c.webp)
![如何欣赏白石虾和悲鸿马[图文] 如何欣赏白石虾和悲鸿马[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04yciipfmm.webp)
![透过自画像窥探著名画家内心世界[图文] 透过自画像窥探著名画家内心世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fanq25naga.webp)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日本茶具[图文]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日本茶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obxw0kmh3r.webp)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文房四宝及书画[图文]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文房四宝及书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krfppptclw.webp)
![彩墨丹青 董春莲老师泼墨作品赏析[图文] 彩墨丹青 董春莲老师泼墨作品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zqjsv5celz.webp)

![刘玉来:提高素养更上一层楼[图文] 刘玉来:提高素养更上一层楼[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nutks51auq.webp)
![百骥争辉 群像恢弘壮美 ·赵文元研究四[图文] 百骥争辉 群像恢弘壮美 ·赵文元研究四[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5p0eynaqim.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