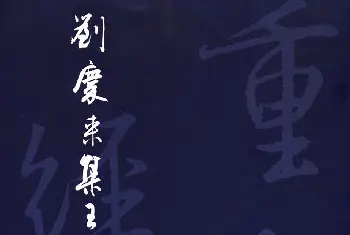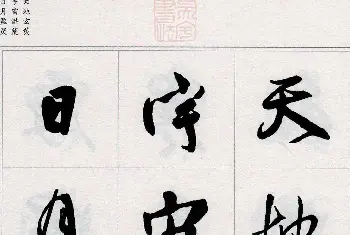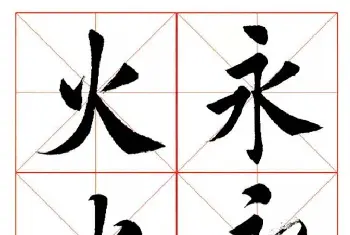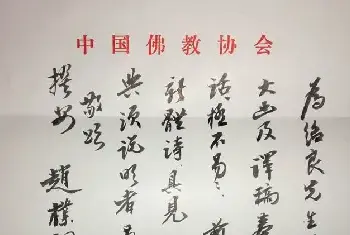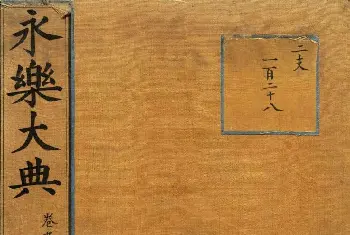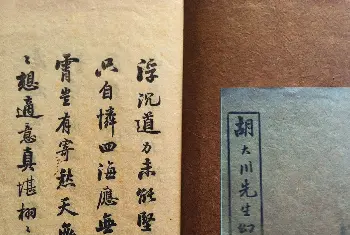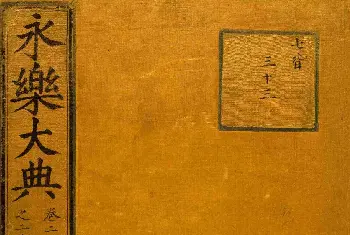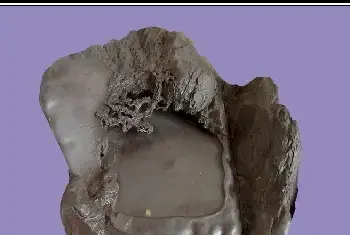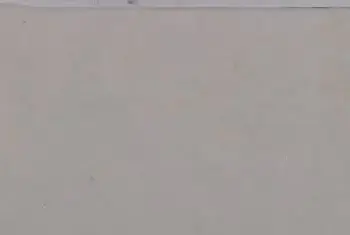米芾与淮阳军考辩
■ 张利
北宋的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土、海岳外史。祖籍山西太原,迁居湖北襄阳,故有“米襄阳”之称,后长期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其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他初师欧阳询、柳公权,字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后转师王羲之、王献之,体势展拓,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自谓“刷字”,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关于米芾出生年月,已在历史上多有考据,然而关于米芾去世的确切年月,却始终众说纷纭,而且对于淮阳军这一关系他最后生命的地方以及在此地留下墨迹、碑刻很少的原因,一直以来无人论述。淮阳军乃笔者家乡,现仅就其去世年月以及生前最后在淮阳军的有关情况考辩如下:
一、 米芾死亡年月考
米芾出生于仁宗皇佑三年(1051年),“以母侍宣仁皇后藩邸,恩补秘书省校书郎”(《全宋词》),二十岁时改临桂尉,之后历任临桂尉、含光尉、长沙椽、杭州从事、知雍丘县、监中岳祠、涟水军使、蔡河拨发、发运司属官、太常博士、书学博士、无为军、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徽宗大观元年丁亥(1107),在他五十七岁,知淮阳军。
《全宋诗》卷1075《米芾》:“大观元年,出知淮阳军,卒,年五十七。”《宋史》本传云:‘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其误明矣。又厉鹗《宋史纪事》云‘大观二年罢知淮阳军’,亦误也。又宋程俱《北山小集•题米元章墓》文谓‘米公卒于大观四年庚寅’,此亦不及张丑《清河书画舫》言之为详。张丑云‘米公卒于大观元年丁亥’,又引蔡肇所撰《米公墓志》谓‘葬于三年六月’,此与方信孺记云‘大观三年葬于丹徒长山下’正合也。且黄长睿《东观余论序》云:‘元章今已物’。此序作于大观二年戊子六月,则米卒于大观元年为定说矣。”(大观元年(1107年)——笔者注)。清吴炎振《宋诗钞》:“大观二年,罢知淮阳军。”徐松《宋会要辑稿》:“特恩加赐者,……知淮阳军米芾(大观二年三月)赙以百缣”。宋蔡肇《米元章墓志》:“以大观三年六月某日葬丹徒长山下”。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据《宋史•奸臣传》,蔡京封楚国公在大观三年。米芾‘被旨预观’亦当在本年。蔡京所跋即《大观帖》,其标题皆蔡京手书。每卷末刻有‘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旨摹勒上石’字样。因此,芾本年当尚在人世。薛绍彭有《秘阁观书》长诗一首,惜未署作年”。《全宋词》云:“芾字元章,……生于皇佑三年(1051),……大观三年(1109)卒,年五十九。或云元年卒,年五十七。”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大观元年丁亥,米公卒,时年五十七。米芾生于北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卒年,史载不一,米芾生前好友蔡肇所撰《米元章墓志铭》称“享年五十有七”,南宋人撰写的《京口耆旧传》也说“卒年五十七”。自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一出,所定大观元年(1107)几为定论。
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米芾年表》考证米芾逝于大观二年三月(1108年),即:大观二年,戊子,“米芾在淮阳军任。开春上章谢事,不允。三月某日卒于军廨。先是,疡生于首,卒前一月,作书别亲友,尽焚所好书画奇物……前七日,不茹荤,更衣沐浴,临死作偈,合掌而逝。” ……朝廷特恩赙赠百缣。曹宝麟先生认为:米芾卒年,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取张丑之说,系于大观元年。自此即为定论,二百年来,无人献疑。然《宋会要辑稿-礼四四-赙赠》有“[特恩加赐者]知淮阳军米芾(下双行小字:大观二年三月。赙以百缣)” 一条,初疑此年月为赙赠之期,但验诸大人先生,乃知不然。如《会要》“太师、魏国公赵普(淳化三年七月。赠其家绢布各五百疋,米面各五百石)”,与《宋史-太宗纪二》“(淳化三年)秋七月己酉,太师、魏国公赵普薨,追封真定王”之载相同。又《会要》“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赙赠有加)”,与《宋史-徽宗纪上》“(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癸酉,范纯仁薨”无爽。遂识《会要》记事之体例焉。略须辩解者唯杨老令公。《会要》:“云州观察使杨业(雍熙三年八月,北征阵殁。赐绢布各百疋,粟一十石)”。而《宋史-太宗纪二》:“(雍熙三年五月)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竭,为所擒,守节而死。”但此恐是“所擒”之时,“(八月辛亥)降潘美为检校太保,赐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盖可见八月乃“守节而死”之期也。
米芾去世后,蔡肇撰写《米元章墓志铭》(载于清《京口山水志》),铭称其“以大观三年六月某日葬丹徒长山下”,蔡肇(?-1119年)为米芾生前的同辈好友,与米芾交谊近三十年之久,晚于米芾十余年去世。此铭文应是在米芾辞世后而未下葬前由蔡肇应其家人托请而撰写的。故其安葬年月为大观三年六月,当为确切,不会有误。
因此,笔者比较认同曹宝麟先生的考证,那就是米芾于徽宗大观二年在“知淮阳军”时,不幸染疾离世,越年六月安葬于丹徒西南长山下。
二、 米芾死亡原因
史载,米芾大观二年戊子在淮阳军任,“开春上章谢事,不允”,于三月某日因疡生于首而卒于军廨。那么,仅“因疡生于首而卒”,似乎其身体抵抗力未免太差了,不能不让人生疑。但是,如果我们从其生前癖好考证,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米芾的癖好,史料记载和传说都很多。《宣和书谱》中也说:“文臣米芾,……博闻尚古,不喜科举,性好洁,世号‘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韵语阳秋》载:“米元章书画奇绝,从人借古本自临莪,临竟,并与临本真本还其家,令自择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书画甚多。”东坡屡有诗讥之,二王书跋尾则云:“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拟圣智。”又云:’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 宋人《张氏可书》中有则记载:“米元章有洁癖,屋宇器具时涤之。以银为斗置长柄,俾奴仆执以灌手,呼为水斗。居常巾帽少有尘,则浣之乃加於项。客去必濯其坐榻。” 米芾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洁癖――洗手不用巾擦,相拍甩干;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弄得破损不可穿,平时要求对房舍擦拭器皿洗涤;头巾帽子不容纤尘,稍微有灰尘必洗;客人坐过的凳子一定要用水冲洗。甚至在选女婿竟然首先考虑的因素也是清洁,因为候选人的名字叫做去尘,他一看就欢喜,爽快答应了婚事。洁癖――大概是应该算作癖且疵的,名士有洁癖,好像历来为人所乐道。也许就是因为从这个洁癖中,往往可以见人物的深情与真气,所以古人也并不忌讳,至今仍被时人所津津乐道。米芾的颠狂固然对他的仕途有所阻碍,但于他的艺术创作却大有好处。从他的性格中,我们不但能看出一个艺术家率真耿直的本性、游戏风尘的态度,更能体会出一种强烈要求摆脱羁束的叛逆精神。作为艺术家,当他志有所凝时,性便有所偏,形便有所乖,这是很自然的事。米芾的颠狂其实是他强烈个性的表露,也是他力求惊世骇俗、出人意表的意愿的结果。正是这种颠狂造就了一个艺术家的米芾,而不是一个平庸的米芾。
张宗子在《陶庵梦忆》里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有时候,这个癖与疵很难区分开来。从某种角度看,“完人”确是是令人无法接近的,甚至往往有些可怕的成分在。因为过度的完美,体现了高度的矫作与虚伪,令人心生恐惧。张岱将癖疵与深情真气联系在一起,应是经惯世情之人的灼见高论。但是,任何癖好都要有个度,超出了度就会出问题,甚至是命丧黄泉。因此,如果结合现代医学研究,米芾“因疡生于首而卒”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现代医学认为:“细菌是人类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它经常保护人体免受疾病的侵扰。因为它能够与有害微生物抗衡,限制其繁殖。在不论青红皂白消灭所有细菌的同时,我们却将整个人类的健康推向了危险深渊。” 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所有细菌中,绝大多数是有益的,可谓是机体的“保护伞”。如果不加选择地消灭有害的和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细菌,就会为有害病菌大开绿灯,破坏了周围的微生物平衡,无法正常发挥其调节作用,并在炎症发生过程中防止人体免疫反应过度而引起大范围发炎,免疫系统也就无法发挥作用。笔者认为,按照今天的医学分析,米芾的死因与其嗜洁成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讲究卫生固然是好事,但过分的卫生却导致其自身免疫能力的下降,以致在淮阳军“因疡生于首”后不治而亡,令人叹惋。
其次,米芾知淮阳军后,一方面可能是水土不服,导致其“疡生于首”;另一方面,由于其洁癖的心理,“疡生于首”使其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恶疡之脏,又久而不愈,其心理负担极重,最终酿至死亡。
三、 米芾与淮阳军
关于淮阳军,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邳州。此地为宋代所置,治下邳,。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邳州――南直隶邳州府(邳州直隶州),“古徐州地。夏为邳国,春秋时为薛国地,战国为齐地,秦属薛郡,汉属东海郡。东汉永平中,改临淮郡为下邳国,治于此。晋因之,宋、齐俱为下邳郡,后魏因之。孝昌初,置东徐州梁中大通五年得之,改为武州。后周曰邳州;隋初,废下邳郡。大业初,废州,复为下邳郡移治宿豫县。唐初,仍曰邳州仍治下邳。贞观初,州废,改属泗州。元和中,改属徐州。宋太平兴国七年,置淮阳军。金复曰邳州。元因之,属归德府。明初,改今属,以州治下邳县省入编户四十七里,领县二。”
米芾在大观元年六月后,“迁礼部员外郎,未入拜而弹章其言,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有旨罢。遂出知淮阳军。” 其间,米芾流于后世的仅有《崇国公墓志铭》、《广帅帖》、《腊月帖》、《公衮帖》等少许墨迹和碑刻。然而,在淮阳军这块土地上,却未见其任何墨迹和碑刻。原因何在?据笔者考证,原因有二:
其一,《语林》云:“元章晚年学禅有得,卒于淮阳军。先一月区处家事,作亲友别书,尽焚其所好书画奇物,预置一棺,坐卧饮食其间。前七日不入荤,更衣沐浴,焚香清坐。及期,遍请郡僚,举拂示众曰:‘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掷拂合掌而逝。”又,魏平柱《米芾年谱简编》云:“卒前作《临化偈》云:‘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人欲识去来,去来事如许。天下老和尚,错入轮回法(路)’”。由此可知,死前一月,米芾将其所好书画奇物全部付之一炬,这其中当然要包括他在淮阳军近期的墨迹了――从他独立癫狂的个性、从他的参禅悟道、从他豪迈不羁的作风,我们都可以想象和猜测的到他那不近于常人的所作所为了。
其二,由于淮阳军水患不断导致米芾书迹的泯灭。米芾在淮阳军任职后,虽然时间跨度在6-9个月左右,但作为“宋四家”之一的他不可能止笔不书,也不可能不去应对地方之所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淮阳军这个地方历史上一直是水患不断,以至于淹没了他的历史痕迹,这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据史料记载,处沂沭泗流域下游,素有“邳苍洼地,洪水走廊”之称,上游有南四湖,下游有骆马湖,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沂河、中运河、邳苍分洪道三条流域性河道纵贯南北。传说黄帝之孙禺号乃奚仲的先祖,而奚仲是辅夏禹治水的重要人物,后受封于邳地,率部族东迁海渚一带定居,建立邳国。据可靠的史料记载,仅自1368年到1948年的580年间,邳州历史上共发生水灾340次,其中以1730年8月(清雍正八年六月)为最,经推算沂河临沂洪峰流量达30000~33000立方米/秒,重现期为248—500年一遇。1912年和1914年沂河也曾两次发生洪水,临沂洪峰分别为18900立方米/秒和17800立方米/秒,仅次于1730年,居第二、三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出现了1957年、1963年和1974年大洪水。大水来临,逃命惟恐不及,哪里还顾及到书画;洪水滔滔,无情的席卷和湮没了一切,即使是碑刻恐怕也难逃劫难了。
“云间铁瓮近青天,缥缈飞楼百尺连。三峡江声流笔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几番画角催红日,无事沧洲起白烟。忽忆赏心何处是? 春风秋月两茫然。”米芾的这首《望海楼》让我们不时的在仰望其高,依稀看见他一边喝酒、一边画画、一边吟诗,长江夹着三峡的涛声从笔底流过,杯中六朝的帆影连同酒一起喝下。细细品位,我们不禁追想他那不平凡的一生,感叹他在淮阳军最后的时光。
历史也许就是这样,她不时地留下许多遗憾和缺失。但正是这历史的伟大和美艳,才让后人不断的去揣度、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