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的艺术市场,无论对艺术家来说还是对其他人来说,都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状况中。当代艺术或老式艺术品的天价看起来是病态的。任何异常都会造成不安和质疑。如果价格代表了内在价值,那么很难解释人们会花10万美元买一幅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或者花8万元买一幅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的作品,同样的价格曾经能够买一幅伦勃朗的画;最近,这个价格还能买到一幅最伟大的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这使人联想到不真诚、投机,以及在艺术品购买中存在的“自我—兴趣、经济—利益与社会地位”之间的三方游戏。
此外,市场中充斥的贪得无厌的利益也影响到了博物馆、一般公众与艺术家。市场在对艺术的判断中从来不是清白的,但是,现在这种将艺术作为宝贵投机性商品的新意识败坏了人们对艺术的所有认识。有关价格的知识很可能再一次通过艺术渗入到人们的一般艺术观念中。这也使艺术家敏锐地意识到销售价格可以作为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除了越来越依赖投机性市场外,艺术还变成了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对象。艺术文献采用一种新的陈词滥调来博取公众的注意力。出现了一种新的、令人厌恶的艺术宣传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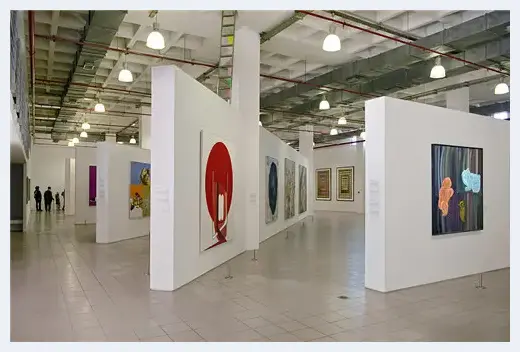
画商和博物馆的展览目录也发生了变化,其中充斥着艺术家的生平传记,以及狡猾的选择和充满暗示性的名目——展览清单、藏家、评论、文章以及专著,艺术家的档案就像一则广告,而且比那些老式的通常由一位友好的诗人或评论家所写的展览前言要重要得多。还有内附彩页的昂贵手册可供出售。
这在艺术家群体中引发了敌意,这是激烈竞争的结果,这些竞争又引发出声势更加浩大的宣传,艺术家之间那种老式的亲密无间以及波希米亚式的愉快的丧失,以及对那些成功者的猛烈反对——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和罗斯科(Rothko)都曾被攻击过。
据说少数几位艺术家的成功造成了对下一代艺术家的忽视,其中也包括那些跟这一成功群体同时代的画家。这是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吗?立体主义者以及马蒂斯的成功对二流立体主义者和野兽派的市场产生影响了吗?
在19世纪的时候,沙龙(The Salon)作为艺术家与公众签订合约的主要平台变得越来越大:获奖人将得到政府的资助、委托、购买、肖像定制、订单,以及在官方学校的教职。评委会掌握着那些只能在沙龙展出作品的许多艺术家的生杀大权。只有极少数画商买卖当代的绘画。然而,与评委会体系所做的斗争并未解决问题。艺术家们在展览地之外另立新的沙龙,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依然如故。不断增长的财富(尤其是在美国),导致了画商数量的巨大增长。沙龙随着艺术展览这一自由事业的增加而逐渐被边缘化,某些艺术家由于市场对他们的巨大需求而逐渐从对画商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就像17世纪一样。
今天艺术购买中涉及的大部分兴趣具有某种赌博的性质;它对那些熟悉股票市场投机以及观望新的投资领域的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是这样一种活动,其中,商业行为变成了作为文化—提升以及文化—象征符号的社会声望的主要来源,而且与此同时,这为其藏家带来更多的财富;它们还构成了某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在这里,艺术以一种自由事业的形式加入了作为一种自由事业的市场。相比于作为商人而言,作为一名收藏家要更自由。商业中对价值的判断来自可销售性以及需求;在艺术中,他还要观察人们想要什么;作为一位有想象力的商人,他要敏锐地预测商机。如果哪位商人能够足够聪明地在1947—1952年间购入波洛克(Pollock)、德·库宁(de Kooning)和罗斯科(Rothko)的作品,那么,他要么是位有些艺术天赋的非凡人物,要么就是通过身边的艺术家和评论家而格外消息灵通。
令人不安的不是这些人会通过艺术(品)价格的上涨而获利,而是这一看法对人们的艺术态度所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影响。艺术品史无前例地变得更像商品;人们与艺术的关系染上了所有商业企业中都会产生的疾病。
在艺术中,我们察觉到一种商品心理学所带来的严峻后果,以及今天整个社会的获利趋向。这在艺术中造成的影响,不能与经济整体的本质以及其对文化造成的影响区分开来。
人们对绘画和雕塑(相对于诗歌)的巨大兴趣,恰恰是因为它们那作为艺术的独特品质能够产生昂贵的、罕见的以及投机性的商品。

![寅虎纳财 鸿虎齐天——著名画家谢荣仁[图文] 寅虎纳财 鸿虎齐天——著名画家谢荣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lqsdyfrei0.webp)
![刘海粟书画真伪浅谈[图文] 刘海粟书画真伪浅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xhp1xqetpy.webp)
![2017投资理财机遇多艺术收藏坚持抓精品[图文] 2017投资理财机遇多艺术收藏坚持抓精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ifyhujntgo.webp)
![俏色玉雕拍卖场上不落的神话[图文] 俏色玉雕拍卖场上不落的神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3pswxcwjve.webp)
![“珠山八友”瓷板画收藏家、画家叶向礼的收藏之路[图文] “珠山八友”瓷板画收藏家、画家叶向礼的收藏之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bayzxhrn1n.webp)

![他的油画真切地反应了现实生活中的美好及特点[图文] 他的油画真切地反应了现实生活中的美好及特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pczidupcnj.webp)
![墨之语画家詹亦然笔下的水墨葡萄[图文] 墨之语画家詹亦然笔下的水墨葡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kstbwltych.webp)
![艺术先锋人物:著名画家朱建红[图文] 艺术先锋人物:著名画家朱建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phnmlhs1md.webp)
![听水陆攻战纹铜壶“壶说” 讲述巴蜀图语的神奇[图文] 听水陆攻战纹铜壶“壶说” 讲述巴蜀图语的神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q3w4e2b42h.webp)
![傅抱石:中国画精神和民族国家同荣枯共生死[图文] 傅抱石:中国画精神和民族国家同荣枯共生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41iuachrgi.webp)
![从巴黎到纽约 如何看艺术市场中心的变化[图文] 从巴黎到纽约 如何看艺术市场中心的变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km5xvcyg3k.webp)
![肖像画:像还是不像 这是一个问题[图文] 肖像画:像还是不像 这是一个问题[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s0cdq1wldi.webp)
![刘艺先生谈草书系列文章之六:《草书的线条》[图文] 刘艺先生谈草书系列文章之六:《草书的线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yoxjuuxsn3.webp)
![康熙宋荦铭青花鱼纹尊赏[图文] 康熙宋荦铭青花鱼纹尊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pskm4mtcdc.webp)
![荣宝斋上海拍品赏析:林风眠《双鹭》[图文] 荣宝斋上海拍品赏析:林风眠《双鹭》[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ywmjiqziov.webp)
![著名版画家阿太作品欣赏[图文] 著名版画家阿太作品欣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umbb3hb4qi.webp)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汪亚尘画作[图文]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汪亚尘画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paafkvdmfg.webp)
![仙鹤是一品鸟古时常入画[图文] 仙鹤是一品鸟古时常入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fa0wbz0vcj.webp)
![不断崛起的东南亚艺术[图文] 不断崛起的东南亚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vxoc0x51sn.webp)


![用泥土和火焰绽放敦煌艺术---艺术家罗红[图文] 用泥土和火焰绽放敦煌艺术---艺术家罗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3ybozkgybz.webp)
![观物取象--翁道胜绘画艺术创作方式研究[图文] 观物取象--翁道胜绘画艺术创作方式研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wxvd1s1cyb.webp)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李秀峰[图文]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李秀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rbjqpjha5x.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