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翟万益
古陶文是指魏晋之前镌刻、打印或书写于陶器、砖瓦质材上的文字,它在书写载体和书写内容方面均有别于甲骨文、金文、碑石文、简书、帛书和玺印文字,不仅是研究中国古文字学和史学、考古学的重要资料,现在把它纳入当代书法创作,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参照。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框定其历史时限时,下限划分到魏晋,一方面是针对现有资料,像陆心源的《千甓亭古砖图释》时代下限为晋宋,陈直的《关中秦汉陶录》,下限确定为汉,更重要的是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文字在魏晋之后或者在魏晋,反映在古陶器上的文字和日常使用文字同步并行,很少有古陶文的那种书写形式,多为隶、楷、行、草书体,和纸帛文书同向发展,因此不列为古陶文书法的研究范畴。
陶器上出现刻符和刻文的历史比较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发现一些刻画符号。例如关中仰韶文化类型的西安半坡遗址,临潼的姜寨、零口、垣头遗址,长安的五楼,铜川的李家沟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发现各种刻画符号二百七十个。晚于关中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浙江的良渚、台湾的凤鼻头、山东的章丘城子崖下层等处出土陶器上的刻符,青海乐都的柳湾、甘肃半山马厂遗址所出土陶器上的彩画符号。关于这些刻画和彩绘的符号,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的认为是记号,有的认为是“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有的认为是简单的文字。但1960年山东莒县出土的龙山文化灰陶尊上的刻文,已被许多专家认可为文字,这是中国最早的书契文字。上古削木为觚以为书写载体是十分理想的材料,遍地是材,但都无稽可考。随着陶器制作的规模化,古文字在陶器上出现,只是当时生活的局部反映,其性质仅仅是一个商标的作用,用以区别陶器的制造者、所为者和使用者。私人作坊的世袭性质使一些陶文有了青铜器上族徽文字的标识性质,一旦稳定下来,父子相传,代不改易,使原初的字形固定地保留了下来,不和日常使用的文字同步,作为书法的借鉴,我们删削藩篱,站在唯美的角度,都可以为我们恰当地加以利用。
商周时代的陶文,主要见于山东莒县、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日照,上海青浦崧泽、马桥,浙江良渚,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新郑、登封、阳城,广东佛山,河北磁县下七垣,江西清江吴城、万载榕树窝、鹰潭角山,山东沂源,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陕西武功、岐山、扶风、凤翔,湖北宣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陶文并不发达,与之相对应的是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可以进行对比研究,而同址出土者多为器物编序号码、族徽记号,文字最多者为山东沂源出土的商代陶文共有十一个单个刻画,但不能释读。与之同期的商代通行文字尚不止于此,我认为只能在文字大背景中是一个另类,并不能代表商代文字使用的通行状况。从刻画方式看,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陶戳按抑文字的状况,大多为手工随意信手而做,表现出更多的率意性;从文字的内容考察,不同的陶器上有着相同的文字,如陕西岐山出土的陶器上的“周”字,书写都有着极大的稳定性,并且表现出了一致性,到了这个时候生产量的不断增加,陶工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刻制陶戳的愿望就产生了。
这时期的陶文多为一器一字,陶器的表面积和文字的占有面积之间有着很大的比例悬殊,依据现有资料进行比较研究,陶工都是固定地占有一定的书写面积,没有铺天盖地的那种书写思想,把更多可以书写的面积让给空白,表现出中国文字在空间中的约束性。同时表现出了陶工对空间的把握意识,虽然有些文字书写气度上十分奔放、恣肆,但都很难跨越他们心中长期形成的制约。
春秋时期的砖瓦、陶器上的刻符和陶文,各地都有零星发现,比较集中的是陕西省凤翔县高庄的秦宗庙遗址出土的瓦上发现刻画符号三十多种。战国时代的陶文发现的数量最多,主要见于山东的齐国临淄古城遗址、河北省的燕下都遗址以及秦都咸阳遗址等,战国时代的陶文早已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早在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马星翼所撰《邹县金石志》中已有关于邹县出土陶文的记载,还有王懿荣的一则题跋中谈到吴式芬曾收藏过一件传为长安出土的有铭的陶鼎,由此可断定,陶文的研究滥觞不应晚于道光时期。此后收藏、研究、著录之风渐开,到上世纪末,大约有著录近七十种之多,其中未刊著录四十五种,已刊的接近二十种。近年,高明的《古陶文汇编》、袁仲一的《秦代陶文》、陈直的《关中秦汉陶录》体例都较为完备,所收图录更是超前,山东王恩田新出的《陶文图录》收有一万二千余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古陶文和其他种类的文字相比较,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陶文产生的时期远早于其他文字,且发展时间长,整个伴随了中国文字书法的全程,可以说一部陶文史就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书法篆刻史,而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等类文字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流行;第二,陶文除了秦惠文王四年瓦书及秦始皇廿六年诏版铭文外,一般不超过十字,而多数为一二字或三四字,少有长篇幅的记事类铭文;第三,甲骨文、金文、竹木简、帛书多出自社会地位较高层次的人的手笔,而陶文多为社会地位低下的陶工所作;第四,从文字学及书法的角度观照,陶文的书体较其他文字更为丰富多彩,从中国文字的最原初形态到篆书、隶书、楷书、行草等各类书体都囊括在内,包含了汉字起源、发展的很长过程。仅以战国时期的陶文与其同时期的其他文字相比,其结体自由、表现奔放、变化丰富、笔道遒简,足资书家之借鉴;第五,甲骨文、金石文字和简书、帛书等材料,多涉及重大政治事件及上层统治者的活动,而陶文绝大部分内容反映了“物勒工铭”的情况,尤其是陶模的印制,本身就是典型的印章资料,这些材料可以直接被当代篆刻艺术吸收和借鉴。
陶文有了上述这些特征,就有着其他类型文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现在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吸收其艺术营养、扩展陶文书法艺术的创作,当是一个重要课题。
古陶文产生发展的历史
人们一般说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如果与七千八百年前大地湾陶片上的刻符相比,甲骨晚了四千多年,所以陶文应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文字生发的一个侧面。当人们发明了火,把大地上烧成陶盆形状的结块转化成了陶器,并在其上绘上抽象的图案,提升到了哲学思维的高度,那么,在彩陶图案产生的同时,提纯文字符号的能力就具备了,与此相伴的陶器上的符号就成了中国古老文字的孑遗。
中国文字的生发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每一个文字,都有它自身变化的历史,如“炅”遗留下的陶文本身就是一个字族,那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消失了的这个字族的材料何止千万倍。在《陶文图录》里,收有“炅”字四个。通过文字可以看出书写的熟练性和完美性,“日”和“火”本身是字符,就这两个字符的提纯,好多民族到现在都没有提纯出来,“山”和“火”的区别,在字里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尝试。在山东的诸城和莒县同时有这样的符号,证明了文字通行区域的广大,这种文字不是一个部族在用,而是通行于多个部落之间,在这个字族产生的同时,肯定在先祖的实际生活中不仅仅是这一个字,它还有一个更大的文字群生成一个体系,应该窥豹一斑,从一个字推论到一个体系,就像我们现在化验一滴血就能分析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一样。这个字的排列组合本身反映了一种哲学思想,太阳在上面,其下为火,火下是土地(“山”是土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反映了相生相克,互相依存的关系。当然这几个字肯定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从笔画变动的区间上来看,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性,这种变动的区间性都非常的优美。从文字看,它到我们看见的这个遗存的表现已经经过了很长的时日,最简单的判断是,我们看见的这个陶文绝不是第一次诞生的。
再看看河南安阳出土的陶文“皿”,这个字《陶文图录》里收了四个,这在同期的甲骨文里有较多的存在。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这就是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共同生活在一个通用的文字体系之中,由于器皿的“皿”自身的繁复性,造成了“皿”字各自不同的形态,但它的基本构成部件都是相当统一的,表现出了它大的方面的确定性与细节的曲尽变化。
战国时代的陶文,现在的学者像高明、王恩田都进行了地域分类。经过分类的陶文,尤其像齐国民营制陶业同乡同里的陶文印的形状、铭文格式、书体大都相同这一现象,王恩田认为当时很可能出现了以刻字为谋生手段的刻字业。这种印模是活字印刷的先声,但一直滞留在原地没有发展,一直到了宋代才用于印刷。印模的出现,比手工刻画更为快捷方便,也更为标准明确,作为商标的作用可以随着商品永久地存在而有了准确的区别。
刻制了一个陶模,要用多长时间,印多少个器皿,当然没有规定,只要不坏,可以一直用下去。日常的文字在使用中不断变化规范,陶模却没变,用到最后就和现行的文字发生了差异,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作为一个世代相传的作坊,既然有了自己的标记,那就世代相袭,以致出现了像青铜器族徽那样的状态,铭文和族徽文字发生了时代的错位,这种情况在陶文中仍然是存在的,作为相同的大文化背景,这也不足为怪。
陶模具有滞后性,手工刻画又有着超前性,所以在陶文体系中同时存在着这么两种文化现象,陶文成型了,不再改变,是过去式,陶工随手刻画到陶器上的文字又是现在时的,陶工随时接受着当下的文化发展信息,反映着最新的文字成果,两种文字形式共同构成了一部古陶文发展史。
陶文与其他古文字的比较研究
陶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早采用手工刻画的方法。由于时间的漫长,地域的广泛,陶工的众多,表现手法各不相同,呈现出的风格间距比较大。造成这种风格间距的原因,一个是文字形变造成的,每个工匠各具独立的审美思想,书写中表现出了差异性。另一个原因是工具的不确定性,他们处于不同的作坊,手中所持的刻画工具极不统一,所以书写工具的变化不居带来了表现风格的千差万别。再则是面积意识的不同,在一个陶器的固定面积上,到底刻画多大的文字,全由陶工自己来确定,他们有着自己的行业习惯,也有个人的灵动自主的发挥,在二者之间就有了自己的空间,这两个因素之外,还不能排除那种临时的发挥,既有着守成的一面,又存在着失范的一面。几千年里这种看似简单的操作过程中,由于中国文字体系的复杂、陶工组成结构的更迭繁杂、表现工具的变动不居、表现陶器面积的不确定性,使风格多样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这是手工书写的状况。
再来看看印模印制的状况。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印模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成千成百的制陶作坊,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各自生产陶模,不统一性是非常肯定的,这个模到底要多大,文字的安排有何规定,只是一个大约的习惯在起作用。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情况,相同的陶模钤盖在泥坯上,都有不同的变异,一是印模的用力程度不同,在泥坯上的深浅程度发生了变化,二是印模的干净程度不同,先一天盖了印模,用水清洗干净了,每次这样作,操作过程力度都保持一致,钤出来的效果会大致一样,如果印模上沾上了泥水,就会使模上的文字发生变异,这一点也会影响钤盖的效果,进而带来风格的变化。还有种情况,那就是印模揿在平面和弧面上的效果也不一致,在陶器的平面上,印模和这个平面平行,那么就能大约反映出印模的真面目,如果印模钤盖在一个弧面上,它自然存在着形变。手工作坊的时代和机器操作的时代,产品的区别性是很明了的。
几千年极为丰富的变化,为我们的创作积累了伟大的材料,齐白石依据吴让之的一方“丁文蔚”印就创造了一种风格,我们在陶文里引发出千万种风格不是神话。
古陶文创作的条件变化
现在利用古陶文材料进行印章创作,从文字的搬用到印式的借鉴已经不存在多大的困难,古陶文在当代印章的转化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这就是陶文的泥味。印模揿按在陶坯上,这个未干燥透的泥坯,一按到底,力度使印文彻底地保留在泥坯上,没有余地,即便是十分刚烈的笔画,到了这种柔和的泥上,刚味也要消去几分。这种状况和遗留下来的封泥是类同的,共同的反映是少了刀味,突现了泥味,也就是增加了柔和之美。
古陶文的结构,有许多常人意想不到的奇特之处,不管它原初是妙手偶得,还是匠心独运,有了这样的奇字,我们自然是眼前一亮,会心一笑。照抄,没有限制,如此却丧失了自己的能动,也不免为古人所讥诮,暴露出了我们的无能。对于需要利用的字,应该是更上一层楼,在古人的基础之上,更竭尽自己的才思,使文字构形多了一层个人的主体审美思想,千年之后与古人的风神相埒。
艺术需要规律,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艺术更害怕规律,循规蹈矩就背离了艺术的本真。走规律与非规律之间的路,向哪边靠得多一些,度的问题是艺术家把握的标尺。在陶文创作中,我在字法上尽力向非规律性这边靠,但避免一边倒。因为书法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门十分成熟的艺术,诸体皆备已千年有余,风格流变更是层楼重上,完全背离规律就成了胡作非为,秉持了规律,但使规律隐没了起来,实际上还是受规律的支使。王羲之在结体上往往是简单字写大,繁复的字写小,这也不是一个铁律,有时会反其道而行之。我在陶文结体中很多时候把繁体字写大,使其更见其大,简单字写小,让其自身感到其小。一些偏旁部首根据事理物理再行加以调整,如“林”字的书写,陶文里往往是二木同致,我把它变成了二木异曲,一个木根部变小,一个木根部变大,变大变小皆合物理,并且两个木在重新组合中不平铺直叙,而是选择了险势,增加审美内涵。像“華”字。主要采用流线型的笔画,下垂的花添加了好多个,一个树上到底开多少花,不仅仅是三五个,增加几个装饰成分也不妨辨识,由于下垂之花的增加,使这个花字分外地修长。真有繁花一树之感。徐谷甫的《古陶字汇》收“匋”字一百零六个、收“万”字六十六个,数量已经够多了,这仅仅是陶文的一个数量,只是中国古文字“匋”和“万”字的部分,在其他古文字中这两个字又有了丰富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字变化的无穷尽,当我们使用这两个古陶文时,又必须赋予变化,随着创作的积累又可形成一个变化的系列。所以对古陶文文字结构的再创作是书家的天职。
陶文的章法,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这个创作的处女地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依赖陶文已有的章法形式。因为这种依赖是有局限性的,长篇巨制就那么两种,陶诏虽然有不少的数量,章法的变化也是那么几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以中国书法的积淀为基础,更需要跨越式的发展,使陶文书法章法后来居上,更胜一筹。我们可以利用甲骨的章法形式,可以利用金文的章法,也可以用简牍的章法形式。陶文的精神内涵是自由开放,率真天然,那么我们用汉碑、唐碑的章法形式,就像给一个地道的农民戴上乌纱一样,官化了,和他的内在又产生了矛盾。时代应该呼唤陶文在章法上有超迈古今的形式出现,大大丰富和扩展陶文的章法形式,由此来冲击中国书法的章法程式,增加无限的生气。
把陶文搬到纸上,进行书法创作,困难首先是文字的缺失问题,比如写一首诗,在陶文字典里寻找,有些字可以找到,有些字陶文里没有反映出来,这种情况是极为平常的事,那怎么解决呢?我认为还是依靠陶文。对陶文里存在的字,也有两种情况,一是独字,就这么一个;一种情况是有两个以上的字,这就要看你确定的创作作品的文字往哪个时代上靠了。大体有一个时段,文字跟着这个时段走也是无妨,如果一个时段里有很多的字可供挑选,那你就更为自由了。对于陶文里没有的字,解决的办法是找部分偏旁去组合,这样我们仍然坚守在陶文的本土上,使它的书写框定在自身的文化基因之内,不会有很大的走失。有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要找寻的文字连偏旁部首都找不出来,无法组合,这种情况下就到你确定的相近的文字里面去找,甲骨文字典、金文字典、玺印字典、战国简帛字典,都无不可。
解决古陶文字缺失问题,通过陶文自身的组合和借用,只是拉起了一个杂牌军,真正要写出陶文的风格来,更需要在陶文的内部去找寻风格裂变的因素。
我对陶文创作的体会
古陶文的研究是早于甲骨文和敦煌卷子的一门学问,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只是近时对篆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书法材料,极少有人问津,主要原因是文字解决的困难与风格提升的艰巨。
陶文每个陶符大部分只是一至三五字,而且每字之间都不尽相同,要把这些散乱的珠子串缀成艺术作品,驾驭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我开始接触陶文材料是1991年秋到北大学习时开始的,当时高明给我们上古文字学,葛英会上甲骨文课,有次葛先生给我们每人发了些陶文拓片复印件,我看后十分兴奋,就利用有限的拓片资料,往自己的篆刻里渗透,收到了意外的效果。有时间就临临那些拓片,作为古文字的一个分支,以增加自己的修养。不久即找到了高明编的《古陶文汇编》,学习的兴趣就更加浓厚了,主要是给自己的篆刻增加意趣,至于书法仍然没有涉猎。到了新世纪之始,我对古文字的学习有了廿多年的积淀,小篆、甲骨、金文、战国文字都不同程度地有了铺垫,开始尝试以陶文进行书法创作。对陶文的创作,由于对其整体状况有一个明了的把握,故而没有像甲骨那样对文字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约束,而是放到中国古文字的大文化背景下去操练,全方位地开放成为我最初的创作思想。在整个陶文里,我最喜欢的是工匠信手挥洒的那种作品,奔放、自由、抒情、无拘无束、一任自然,把所有的法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赤裸裸地剩下了自我。这种无法无天的表现,不仅仅强化的是工匠自身的价值,而且外露了工匠在循规蹈矩生活之中突然闪现的自我,人性在书写的那一瞬间的自由。在当下的境况中,中国书法走过法的重重包裹,可以说法上有法,法再无以复加了。脱去了重重袈裟,走出了森严的殿堂,回归到山野之中,一任天然,这是中国书法迭迭复复发展之后,又一种返璞归真的选择,陶文应该担当起这一放任的角色。
在用墨的选择上,我仍然保持了以往的习惯,水墨分置两处,汲水汲墨随心所欲,不等的量必然给纸面上形成浓浓淡淡的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强烈的,有时变化则是隐秘的,不管强烈还是隐秘,总是沿着一种变化的思维在推进,等到纸上的墨干了,回观写过的笔迹,隐伏的变化都会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只欣赏这一路墨色的变化,也是行于山阴道上,自有重重复复、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韵味,带给审美主体无尽的回味与遐想。
笔法消除约束,这又是一个突破性的课题,我们不要给陶文这匹无缰之马戴上世俗的笼头,让其在我们的笔下过早地丧失了野性。在笔法的提炼中,我反复地审读陶文拓片,从一张张拓片上每个文字的细微之中找寻笔法上的异质,对其形成的过程不断加深理解,在自己的笔下放量性地生发出来。关于笔法的选择,在大的区间上,我站在了陶戳文字和刻画文字的中间,倾倒于一方,自然就是一种偏颇,同时吸收这两种表现手法的笔法特点,在行笔中大胆运用露锋起笔,露锋收笔,适时加入藏锋手法,陶文的藏锋既不是颜楷的藏锋,也不是小篆的藏锋,我适当挪用了自己在甲骨文创作中积累的一套笔法,当使用到陶文领域时,更把它夸张化了。在藏锋的地方,用力的度有了很大的区别,可以把笔毛用到最大限度,也可以微风细雨、轻松地表现,剧烈的手法,同时出现在一个字中,强化笔道的对比性、增加审美主体的视觉感受。藏锋起笔的路线不因袭隶书、不重蹈楷书,多路线、多手法,不同力度、不同角度、不同墨量,使变化曲尽其美,丰富多彩。为了加大抒情效应,汲墨的程式和自己草书创作一样,起笔饱汲墨,笔道渗染到一起,连续写好多字也不汲墨,到笔出现了飞白仍不罢休。当笔头上形成干枯状态时,还是在绞转拧擦,挥洒不已,一笔墨写了一个长长的音乐节拍,起止分明,过渡舒张,韵律修长,给人一种酣畅淋漓之气概。毛笔在纸面上舞蹈,在草书情况下可以达到,陶文能不能如此,回答是肯定的。起伏的大小,起伏波段的长度,决定了书法的旋律,在这一点上我自觉秉承古陶文书写的内在精神,达到气韵的舒张,心灵的自由,使情绪如海水一样无滞无碍,尽力向深度的云端流去。

![创造意象 兴象抒情:浅谈杜世禄的积墨写彩山水[图文] 创造意象 兴象抒情:浅谈杜世禄的积墨写彩山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4voyrxbklp.webp)
![壶韵茶味——温红远壶艺印象[图文] 壶韵茶味——温红远壶艺印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x1gqvrcri1.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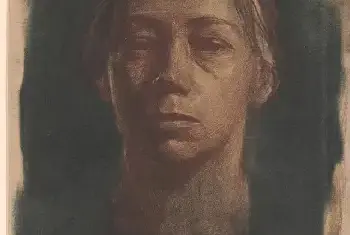
![刘震云谈《一九四二》:灾难,我们拒绝遗忘[图文] 刘震云谈《一九四二》:灾难,我们拒绝遗忘[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5yx12dzoxf.webp)
![经济低迷 富豪为何还在投资艺术品[图文] 经济低迷 富豪为何还在投资艺术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t030nt1kzz.webp)
![按下暂停键的艺术市场迎来线上转型契机[图文] 按下暂停键的艺术市场迎来线上转型契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wzvnxoprvb.webp)
![从王羲之到颜真卿 书法史都经历了什么[图文] 从王羲之到颜真卿 书法史都经历了什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mmomodp03z.webp)
![如何与空间交流 对蔡磊个展“景别”的回顾[图文] 如何与空间交流 对蔡磊个展“景别”的回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venhwgziwk.webp)
![浅析工业遗产旅游复兴的八大模式[图文] 浅析工业遗产旅游复兴的八大模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olga0bplxi.webp)
![国泰民安·同贺祖国71华诞——著名画家穆春华[图文] 国泰民安·同贺祖国71华诞——著名画家穆春华[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2waqznpbux.webp)
![李磊:推理莫奈[图文] 李磊:推理莫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13dwtn0gwk.webp)
![罗汉成:笔墨承道山水寄情[图文] 罗汉成:笔墨承道山水寄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nbrtrro4oe.webp)
![揭秘世界画廊业之王高古轩的商业模式[图文] 揭秘世界画廊业之王高古轩的商业模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vxss4i2t2r.webp)
![2020年特别推荐艺术先锋人物:骆松涛[图文] 2020年特别推荐艺术先锋人物:骆松涛[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otk2gmv1dp.webp)
![数字化与文物归还[图文] 数字化与文物归还[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fpga324pgd.webp)
![彩墨丹青 董春莲老师泼墨作品赏析[图文] 彩墨丹青 董春莲老师泼墨作品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zqjsv5celz.webp)
![盛放几代人温暖记忆的连环画该怎样连通当下[图文] 盛放几代人温暖记忆的连环画该怎样连通当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2rnfnodthg.webp)
![张大千艺术市场解析[图文] 张大千艺术市场解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y3abdhnp51.webp)
![论博物馆创新维护的重要性[图文] 论博物馆创新维护的重要性[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zw4qnhzr14.webp)
![上海一年300多场艺术特展背后的秘密[图文] 上海一年300多场艺术特展背后的秘密[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g5114x0x5w.webp)

![丝绸之路北方行·赵文元研究八[图文] 丝绸之路北方行·赵文元研究八[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r23mjylez2.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