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应该是一门吸引人的学问,美术史论系应该成为美术学院的中枢部门,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被人轻视,首先在于中国文献和中国思想大面积的空缺。美术史家应该通过中国原典同原作的比照,进行对称研究,而20世纪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称的。
20世纪的战争和政治运动致使历史研究停顿,销毁和封禁古籍使得美术史研究流于直观和肤浅,很多作者绕开古代文献,想当然地、直观地写史。这样一类美术史研究离不开千篇一律的套话,比如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章法严谨、用笔洗练等等。每个朝代的开头都要讲一通政治背景,比如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政权更迭等等。农民起义对中国美术的发展没有直接意义,实际上,中国古代美术是社会财富过剩的产物。每一次大型农民起义都是对中国美术的摧残,与此相关的研究也是牵强附会。比如韩滉的《五牛图》,本来是标准的帝王文化的产物,依据的是五行学,仅仅由于牛是农耕工具,美术史家就想当然地同农民挂钩,有一部书是这样评论的:“韩滉对人民的苦难有所了解。他的《五牛图》,笔墨简练,形象生动,呈现出一种浑厚朴实的艺术风格。”“对人民的苦难有所了解”,言下之意是对农民有所同情。作者显然没有查阅韩滉事迹,没有查看有关韩滉的笔记。《新唐书》中的韩滉传,只有他结党营私、不顾民众疾苦的事迹。比如有一年暴雨成灾,山西运城盐池一带出现内涝,八成庄稼受灾,盐池出产的食盐味道发苦。分管盐池的韩滉担心皇帝为当地农民减税,揩掉他的油水,便向朝廷谎报灾情,声称盐池仍在生产瑞盐。皇帝鉴于秋天多雨,盐业必定受损,派遣中央官员检查。检查官害怕韩滉报复,伙同韩滉继续欺骗皇帝。韩滉的这类行径,使得史家对他品格的讽刺毫不留情,说他没有飞黄腾达之前,通过自我矫饰以求晋升;一旦得志就暴露本来面目。这是历代弄臣的共同嘴脸。
如果“为尊者讳”的陋习在美术史研究中不加以清算,连古代史家都不如,研究的价值何在?缺少了自己的文献,中国美术史不得不借用别人的本钱。把中国古代美术同西方现当代学术思想生硬地拼贴,仍然是当今学院论文的通行作风。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现当代美术,却很难分析中国古代美术,因为两者的性质全然不同。用分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美术,永远见不到它的真相。因为制约中国美术的思想主体,也就是农业文明与帝国政治这个基础,千古不变。阴阳二元论、三统论、五行学、易学以及儒、道、佛思想,统统是分科方法和零碎工程的敌人。中国古代美术看重功能而不是看重艺术,不强调个性而是关注类型。类型是常例而个性是特例。研究者不关注中国美术的常例,而用强调个性和独特的现代艺术观去挑选古代美术作品。
中国美术史研究是国学的一支,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研究中国美术史,就无法绕开三千年沿革的历史文献。中国古代文献将近几万种,核心文献上千种。研究国学必须经过充分的阅读。国学界的共识是50岁之前不要谈国学。从总体上看,35岁以上、65岁以下年龄段的中国学者,知识结构已经固定,国学被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学者荒废了。
20世纪以来,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出土的众多文物与文献,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可是由于中国博物馆条件和制度的落后,大量美术文物至今深藏密室,造成资料封锁。
美术史家认清现状不难,难的是改变学术氛围和社会氛围。中国美术史是文科中最难的学问,是学术中的马拉松项目,它不同于美术创作,只要有感觉和个性,就有可能创造杰作。美术史研究需要长期阅读和思考,它不是这个时代的选项。少数有国学积累的学者,到了出成果的年龄就面临退休,退休后的工资锐减,写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学术著作常常要自费出版,学术研究变成了义务劳动。总之,用毕生精力研究美术史,不是这个时代的选项。美术史撰写、评价、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由既得利益者操控的学术,只能是维持现状的老生常谈。这使得很多学美术史的研究生,毕业了还没有入门。他们的作风至少还会影响两代人,因而我对美术史研究的前景并不乐观。

![人民日报:“傍名”出版伤了谁?[图文] 人民日报:“傍名”出版伤了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f1g5ybogu0.webp)

![吴门画派之宗师沈周[图文] 吴门画派之宗师沈周[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vdpbahozmz.webp)
![一个非美术馆的展评[图文] 一个非美术馆的展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i4w0hq25j4.webp)
![与山传神 与花写照—浅析马健郡的国画[图文] 与山传神 与花写照—浅析马健郡的国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foedcyewdo.webp)
![罗斯科:好艺术是纯粹的[图文] 罗斯科:好艺术是纯粹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0xo4wazjca.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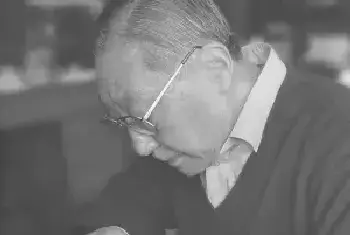
![中国画题款钤印有讲究[图文] 中国画题款钤印有讲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ndaphu1bb4.webp)
![艺术为民:访著名画家喻继高先生[图文] 艺术为民:访著名画家喻继高先生[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to04fpdnid.webp)
![书画临摹作品有无著作权?[图文] 书画临摹作品有无著作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25ovvj5uff.webp)
![培根:用画布绘出的恐怖图景[图文] 培根:用画布绘出的恐怖图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v3ar4o03el.webp)
![“这些书信可弥补张爱玲整个传记”[图文] “这些书信可弥补张爱玲整个传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p1qhwghedf.webp)
![趋势:新水墨黑马逐渐成形[图文] 趋势:新水墨黑马逐渐成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xp3tr2drh4.webp)

![灵犀独慧 技近乎道—陈铸的书法艺术[图文] 灵犀独慧 技近乎道—陈铸的书法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sy1hhgqxhw.webp)
![溯源法古 独树一帜开新篇——记感应书法和梦幻画风创始人宋草人[图文] 溯源法古 独树一帜开新篇——记感应书法和梦幻画风创始人宋草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a3z0jomhfm.webp)
![崔岫闻:大于艺术的是什么[图文] 崔岫闻:大于艺术的是什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s1m5yaf5pa.webp)
![欣赏裸体艺术是靠情欲还是依赖品味[图文] 欣赏裸体艺术是靠情欲还是依赖品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ztdrfzqaev.webp)
![原研哉:无印良品美学炼金师[图文] 原研哉:无印良品美学炼金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ma0hjh2fmw.webp)
![石湾公仔黄:用中国画技法捏陶瓷[图文] 石湾公仔黄:用中国画技法捏陶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ayd5sjt54r.webp)
![胡智勇:成化斗彩珍品不只有鸡缸杯[图文] 胡智勇:成化斗彩珍品不只有鸡缸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mai4j3zjjn.webp)
![毕加索与中国艺术的两次相遇[图文] 毕加索与中国艺术的两次相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z5eqnpzhbk.webp)
![中国实力派山水画家--闫祖智[图文] 中国实力派山水画家--闫祖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jjiuoiprje.webp)
![张晓刚:川美现象在走下坡路[图文] 张晓刚:川美现象在走下坡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zfqojnvshb.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