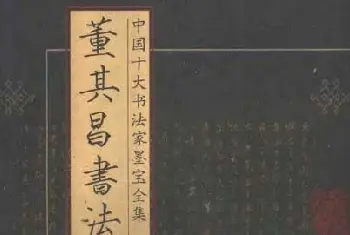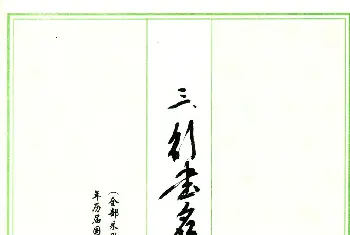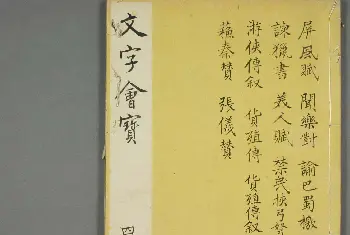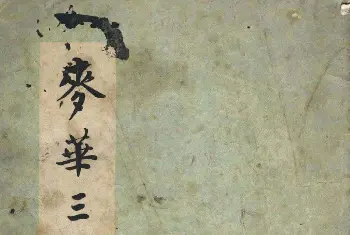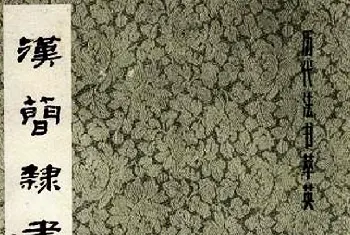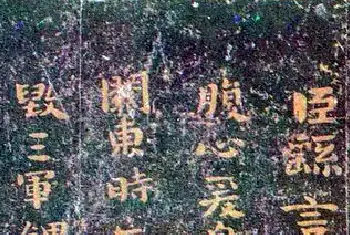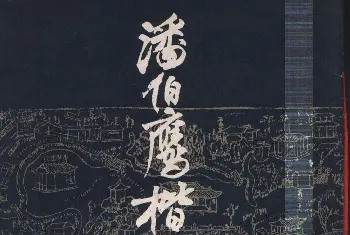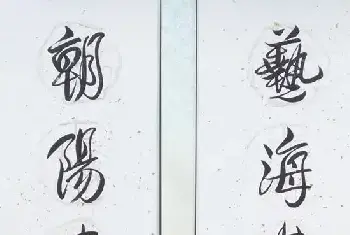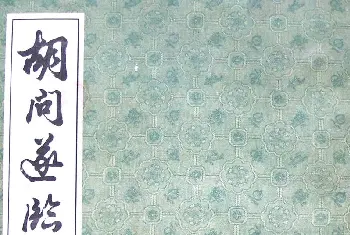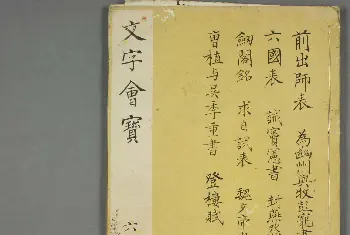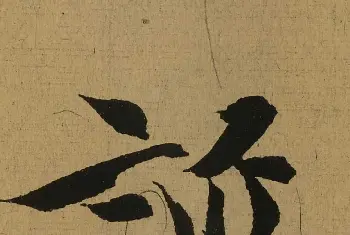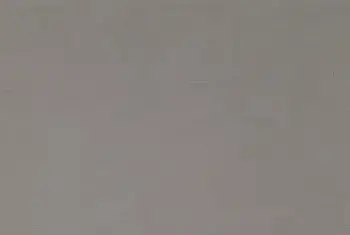二 虚无益充实
中国书法艺术的渊源必须从中华民族对“虚无”的追求中去寻得。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
可知之之谓神。”这是孟子模糊地区分的从实到虚的几个发展阶段。
“充实”是美的前提,此为第一步,这是容易理解的。譬如我们讲“语言美”,就必须丰富自己的词汇,先使语言充实,然后才能有美的
语言,要不然老是几句脏话盘来盘去,何来语言之美。同样,“心灵美”也必须先使心灵充实。孔子称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
者,其由也与。”子路穿着破旧衣衫与穿戴华丽的贵族站在一起,一点不感到难堪,为什么?因为他的心灵充实。唐司空图《诗品·绮丽》谓“
神存富贵,始轻黄金”。多可爱的黄金啊!惟有精神富贵,即灵魂充实,方能将象征富贵的黄金贱视。子路之充实,方有子路之神采。我们可以
想象子路穿着破旧衣衫站在穿着华丽的人中间。不但不显寒酸,反如鹤立鸡群,神采非凡。按照孟子的划分,似乎可算第二级,即“充实而有
光辉”了,也就是说,已由实到虚发展了一步。但离最高等级的虚——“不可知之”的“神”,尚有好几个层次。我们对孟子所分等级,不必
精确计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其最高等级——“神”,乃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虚无境界,这种境界比“圣”还高,连圣人也在不断的追求之
中。
其实古哲并不是追求真正的一无所有的虚无,而是在追求最高等级的充实,是对于“无限”、“本原”的追求,最终是为了寻求解脱,从
实发展到虚的过程,最终是一个解脱过程。
西洋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有一句名言:“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即有限事物由其物理上、或逻辑上的境界限定,由它非某某东西限
定。
这是一句很富有辩证思想哲学的名言,黑格尔称之为“伟大的命题”。(《哲学史讲演录>)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这句话,他说:“在辩证法
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
即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马恩选集》第3卷)斯宾诺莎又认为完全肯定性的“存在者”只能有一个,就是“神”,它必定是绝对
的无限。
其实中国早此二千多年就有类似说法,这就是《老子》中的“执者失之”。(六十四章)和斯宾诺莎不同的是,斯宾诺莎承认宗教的“神”
是完全肯定的存在,中国哲人则以不规定来达到不否定,即《老子》的“无执故无失”。
“执”就是规定。规定就是具体化现实化。因而是一种存在的肯定,但是正因为对该东西加以一种具体的规定,因而也就是对它的一种限
止,这样规定又是否定了,所以说“执者失之”。
日常生活中,说东就排斥了西。说张三,就将张二以外的李四王五全丢了,画一条狗,就再也不是猫、虎、人等等。
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人称佳句,而毛奇龄曰:“定该鸭知,鹅不知耶!”(见《随园诗话》)《列朝诗集》丁十二谭元春传后引吴
门朱魄曰:“伯敬诗、‘桃花少人事’;低之者日:‘李花独当终日忙乎。’友夏诗‘秋声半夜真’;则甲夜乙夜秋声尚假乎”。看似强词夺理,
而言词有挂一漏万之弊,恰是实在。“有执故有失”也。
故《庄子》有云:“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齐物论》。昭氏,姓昭名文,古音乐家,善弹琴。)
郭象注:“夫声不可胜举也。故吹管操弦,虽有繁手,遗声多矣。而执籥鸣弦者,欲以彰声也,彰声而声遗,不彰声而声全。故欲成而亏之
者,昭文之鼓琴;不成而无亏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冯友兰教授解释道:“这就是说,无论多么大的管弦乐队,总不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声音全奏出来,总有些声音被遗漏了。就奏出来的声音
说,这是有所成,就被遗漏的声音说,这是有所亏。所以一鼓琴就有成有亏,不鼓琴就无成无亏。像郭象的说法,作乐是要实现声音(“彰声”
),可是因为实现声音,所以有些声音是被遗忘了,不实现声音,声音倒是能全。”
据说陶渊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无弦琴,而渊明的确有诗句云:
“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他的意思大约就是庄子所说的罢。
《老子》曰:“大音希声。”(希,寂也)
《庄子·天地》:“无声之中,独闻和焉。”
陆机亦曰:“繁会之音,生于弦绝。”
白居易诗句:“此时无声胜有声。”
都是体会到了“虚无”的无限丰富的境界。
中国先哲中最知“虚无”之妙用者,首推老子。
“致虚极,宁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无异是老子追求虚无的宣言。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正因为风箱中空,空气可以不断进去,不断出来,方无有穷竭之时,正是无限。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辛辛苦苦造起屋子,而正是其空虚之处,才是我们所用的。且意义尚不止此,盖屋子之实处,无有变化;而房屋之内(即虚处)却变化万端:
主人之活动,主人之变迁,主人之更替,客人之来往,屋内之陈设等等,变化无方,不可胜计,其丰富与充实又岂实处之可比拟,而此种丰富
与充实,又实赖房屋之中空。虚空之中殊难肯定,亦即无否定矣。庄子亦曰:“惟道集虚。”“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夫虚静恬淡
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此种追求是否惟老、庄为然?非也,儒家亦复如此。
《论语》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王弼曰:“‘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
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皇侃《论语义疏》引《论语释疑》)
孔子深感言不尽意,深知言之徒劳,故亦以无为心。“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亦王弼语,见《周易》复卦象辞注。异类未
获具存,则所得无几,何来包罗一切的无限气象!
艺术家与哲学家一样,亦在苦苦追索。
曹雪芹写林黛玉就很巧妙:“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似蹙”,好像肯定了;“非蹙”立即否定。“似喜”是肯定,“
非喜”又否定。其实都是避免限定。读者又听凤姐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宝玉说:“这们一个神仙似的妹妹”等等
,都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是读者自己勾出了黛玉而浮现于脑海,是模糊不定的形象,却是理想的形象。理想中的美人一由京剧大名旦梅兰芳清
楚地扮出来,变成了绝对肯定的形象,因此而受到鲁迅的调侃:林黛玉的眼睛没有这样凸,嘴唇也没有这样厚。梅兰芳扮相算得美,但是实的,
实则必有所限。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记吴天绪说书云:“效张翼德据水断桥,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惟张口努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
而满堂中如雷霆喧于耳矣,谓人曰:‘桓侯之声,讵吾辈所能效状?’其意使声不出于吾口,而出于各人之心,斯可肖也。”
以虚出之,而得“出于各人之心”。出于各人之心,则丰富生动之状,莫可胜言,此非虚之效耶?
中国绘画最早不重形似,早有“以形写神”、“遗貌取神”之说,从描形到求神,无异由实即虚。再求写意,离实愈远。郑板桥诗句乃云:
“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真魂”云者,非虚极而何?
如此种种,显示出中国的哲人和艺术家无不在苦苦挣扎,企图脱离现实世界、现实形式之束缚,而自由显示其主观的本质。他们要创造一
个无得无失包罗万有之“象”。“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始而不为他们所特别注意而却在不知不觉中创
造完备的书法。书法的价值终于被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