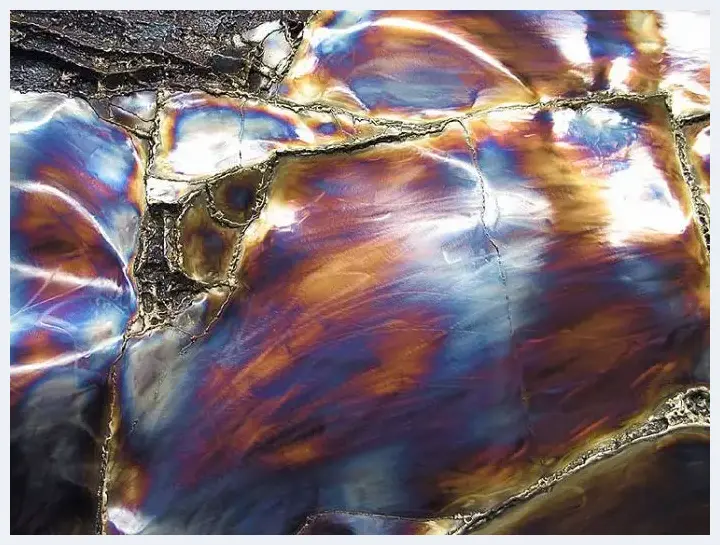
黑格尔关于艺术可能衰亡的观点,与艺术作为生成物(product of becoming)的历史本质是一致的。在黑格尔把艺术视为某种终结之物的同时,又将其当作绝对精神的一个契机,这一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实与黑格尔体系的双重特征是完全一致的。然而,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蕴含着一个他本人从未得出的结论,即:艺术的内容——按黑格尔所说也就是艺术的绝对层面——不同于存亡层面。可以想象,艺术的内容兴许正是艺术的致命因素。音乐便是一个例证。美妙的音乐这一艺术领域中的新秀,很可能仅在有限的人类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根据一种对待客观历史世界的新态度来纲要性地界定自身的艺术造反活动,已经成为反艺术的造反活动。人人都在猜测艺术是否能够在这些发展中得以幸存。但是,人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由于一度反动的文化悲观主义与一种文化批判理论在下述命题上看法一致,艺术,正如黑格尔所估计的那样,可能很快进入其终结或没落时代。一个世纪之前,里莫鲍德(Rimbaud)的名言直觉地预料到现代艺术的历史;尔后,他便保持沉默,并且充当了一名雇员,这都预示着艺术的衰落。
今时今日的美学不可避免地成为艺术的挽词。它可以避免而且必须避免的是致墓边悼词,即预言一切将要终结、品评过去的成就或赶追野蛮状态的浪头。野蛮状态并不比与美学完全相辅相成的文化更好或更糟。假设艺术已经终结、自灭、消亡或者朝不保夕,但这一切并非意味着过去艺术的内容也必然会消失殆尽。艺术很可能凭藉其过去的内容在一个崭新的、不同的、摆脱了野蛮文化的社会中得以幸存。

己经消亡的不只是审美形式,而且还有许多实在的母题。仅举一例,描写通奸的文学曾在维多利亚时期以及20世纪初期盛极一时,但随着资产阶级中心家庭的解体和一夫一妻制的放松,今天则难以为人们所欣赏。于是,这种文学有的流行版本中便找到了一个崭新但可悲的归宿——即带有插图的杂志。《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中的真实要素,曾是该小说题材中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经久不衰,已经超出了原小说的内容与寿命——这一陈述丝毫无意诱使任何人对精神的无敌性产生乐观的信念。当然,有许多例证可以表明,艺术作品的内容之死事实上已导致了更高真理契机的毁灭。事实上,致使艺术及其产品(包括他律与自律艺术,后者具有维护社会分工与才智之特殊地位的作用)消亡的不只是艺术本身,而且还有某些不同于和相对于艺术的东西。与艺术概念搀合在一起的胚芽将会以辩证的方式取代艺术。

![对鲁本斯的重新定位:启发灵感的肉体[图文] 对鲁本斯的重新定位:启发灵感的肉体[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0gdjjns0tq.webp)
![如何收藏艺术大师的纸上小作品[图文] 如何收藏艺术大师的纸上小作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52hcvcml0k.webp)
![朱浩云:从中华书局走出的海派大家沈子丞[图文] 朱浩云:从中华书局走出的海派大家沈子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imdmigwbgk.webp)
![七夕之夜 这些艺术作品中的一吻传情有没有打动你[图文] 七夕之夜 这些艺术作品中的一吻传情有没有打动你[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gkkvz3puqt.webp)
![胸襟开阔·自然天成——著名画家赵金鹏的绘画艺术[图文] 胸襟开阔·自然天成——著名画家赵金鹏的绘画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a1fw2pbxdv.webp)
![不可小觑的“潮流艺术”市场[图文] 不可小觑的“潮流艺术”市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dfmk0x1lz2.webp)
![寅虎纳财 鸿虎齐天——著名画家朱法鹏[图文] 寅虎纳财 鸿虎齐天——著名画家朱法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kewst2ohat.webp)
![传艺术之大美——当代著名画家姜山[图文] 传艺术之大美——当代著名画家姜山[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kqjrspyaon.webp)
![逛美术馆会像吃饭看电影一样成为我们的日常吗[图文] 逛美术馆会像吃饭看电影一样成为我们的日常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hxvfrsg4qb.webp)
![双说顾恺之与王献之的《洛神赋图》[图文] 双说顾恺之与王献之的《洛神赋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kmffbqswp5.webp)
![性灵之美——林娜作品赏析[图文] 性灵之美——林娜作品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xiizfdk0qw.webp)
![董其昌山水画的两种面貌[图文] 董其昌山水画的两种面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3q4rwhoeeu.webp)
![玉兔迎春 丹青贺岁——著名画家翁雪飞[图文] 玉兔迎春 丹青贺岁——著名画家翁雪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o0wvm3goqm.webp)
![典雅明丽写吾心——张劲松国画艺术探索[图文] 典雅明丽写吾心——张劲松国画艺术探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fiesnspsna.webp)
![艺术品市场连续三年下跌[图文] 艺术品市场连续三年下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omiq3inu5a.webp)

![彩墨丹青 董春莲老师泼墨作品赏析[图文] 彩墨丹青 董春莲老师泼墨作品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zqjsv5celz.webp)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4mhciphhag.webp)
![布尔乔亚:爱恨交织的生命痕迹[图文] 布尔乔亚:爱恨交织的生命痕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t1t3utrez3.webp)
![透过自画像窥探著名画家内心世界[图文] 透过自画像窥探著名画家内心世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fanq25naga.webp)

![百骥争辉 群像恢弘壮美 ·赵文元研究四[图文] 百骥争辉 群像恢弘壮美 ·赵文元研究四[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5p0eynaqim.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