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上河图》无疑是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是描绘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清明时节的风光,图中所绘可与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相关内容相对照。①开卷处画汴京近郊,疏林薄雾,农舍田畴,往来行人中夹杂着踏青扫墓归来的轿乘和长途跋涉的行旅;中段写汴河沿岸景物,河中漕船上下,其“虹桥”一段为全画高潮,车马行人,南来北往;后段写市区街道,房屋鳞次栉比,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在表现手法上,此图采用了传统的手卷形式,全图以不断移动视点的方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所绘景物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和谐地组织成统一整体。画面细节刻画真实细微,画中人物多达500余人,不唯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
这幅作品可说是巨细无遗、无所不包地完整记录了宋代都市生活的全貌。的确,在反映宋代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清明上河图》有着文字难以替代的文献史料价值,是了解12世纪中国城市生活的极其重要的形象资料。《清明上河图》无疑是一幅风俗画,作者为画院画师,画法属于严谨精细一路,也就是说它是一幅题材俗、作者俗、体裁俗的“大俗”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明上河图》的确算得是大俗而成为经典的独特例子。
一、《清明上河图》的“俗”与宋朝所具有的同一特质有密切的关系。
张光直先生指出:“文明没有财富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要认识中国文明的特点,关键就是要看“它的财富是怎样积累起来,同时,又是用什么手段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那么,中国历代王朝是怎样累积并集中财富的呢?主要是“借政治的程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而不借技术或商业的程序(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造成的”。②从张光直先生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文明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侧重于政治程序的,一种是侧重于技术和商业程序的,就二者谁更具有“俗”的特点而言,无疑是后者。这是因为“俗”这个词原本就意味着贴近现实,民众的、习尚的、非规范的、非幻想的、非宗教的。
如果把社会生活中技术和商业因素的增强,个人利益和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和保护,强制性的人身胁迫因素和礼教或宗教因素相对淡化等视为一种“世俗化”趋向的话,这种世俗化趋向说起来在唐代就已相当明显,尤其是在其中后期,它不仅体现在绘画和雕塑的审美趣味上,更体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甚至于也体现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宋朝不仅延续了这一趋向,并逐渐把它推向高峰。宋朝的开国之君赵匡胤职业军人出身,他当皇帝的特殊之处亦可归之于一个“俗”字,具体而言就是务实不务虚。宋朝的臣民们在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上迸发出了巨大的热情,北宋的人口即使极粗率的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也正是由于对技术和商业的重视与鼓励,宋朝的农业,手工业等各种实用技术达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而使得宋代的物质文明和都市物质文化成为了传统中国的极高峰。文化的繁荣还表现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相当普遍的较高的文化需求,宋代的市井文化、通俗文学以及风俗画、节令画和画市的兴起等,正是为了满足民众这方面的需要。当然最能体现宋朝繁华景象的城市还是张择端所描绘的那个东京。“东京倚汴水建城,便于漕运。汴水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场上销售。”“东京是皇室贵族官僚的住处,也是‘天下富商大贾所聚’之处。他们以侈靡相尚,大肆挥霍。东京到处有酒楼、食店、茶坊、妓馆。著名的杨楼、樊楼、八仙楼,饮客常至千余人。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贵族、官僚、豪商整天在此享乐”。③
不消说,这里所述的一切都被张择端一一描绘在《清明上河图》中了。
然而,宋朝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朝代,对此黄仁宇这样总结道:“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重实际,不受抽象观念所蒙蔽,而这319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才,又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④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也体现于宋代的绘画,我们知道,恰恰是在宋代,与《清明上河图》之类大俗之作迥异其趣的文人画续上南北朝的血脉而成了气候。与传统中国的历代王朝相比,宋朝的确出现了诸如追求经济利益、注重技术和商业等被我称之为“世俗化”的新气象,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社会生活的更深也更重要的层面上,它依然是守旧的凝固的传统的。因为有新气象,中国的传统绘画在宋朝也就产生了新的变局,绽放了《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奇葩,也因为它终究未能走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它的气运也就难以为继,自然就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了。

二、如上所述,绘画在宋代特殊的社会、文化情景中形成了新的变局,这变局的特点大致可概括为“雅俗分流”四字。
雅与俗恐怕算得是中国文艺美学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不同的一个地方。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因素一直很浓重,宗教是神圣的;中国文化中的“雅”则意味着一种文化涵养和道德情操,所以,一个“俗”字放在西方就容易让人想起与神圣事物相对的东西,而放在中国,则首先让人想到它缺少文化陶冶和精神修养。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绘画雅与俗的区别并非始自宋代,但二者的确是在宋代才形成了二水分流、两峰对峙的局面。其俗的方面以所谓画工或画师画为代表,画工或画师既有属于宫廷画院的,也有院外的;其雅的方面则主要以文人画为代表。大体说来,宋代的画工或画师的创作延续古往今来历代宫廷和民间画工或画师的传统,而士夫画则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传统资源可资利用;画工(画师)画由于直接为宫廷和社会服务,容易与时尚流俗相结合,故总体上呈现出“俗”的美学特质,而士夫画基本不存在服务性,加以作者大都是文人雅士,可以在极大的程度上超脱于时尚流俗,故每每表现出超逸脱俗的美学风采
绘画在宋代的“还俗”倾向主要表现为淡化其传统的礼教和宗教色彩。这一点已为当时一些敏感的士人所察觉,如米芾就说过:“古人图画,无非劝戒。今人撰明皇幸兴庆图,无非奢丽,吴王避暑图,重楼平阁,徒重人侈心”。米芾这番话虽然是针对某些具体的绘画题材而说的,但他说出了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耐人寻味。郑午昌先生撰《中国画学全史》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古代美术划分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并指宋代为“文学化时期”的开端。⑤这个划分大体上是合理的,只是他所说的“实用时期”在今天看来,其中恐怕也有相当浓重的“宗教”或“神教”因素。
为什么绘画到了宋代会出现米芾所说的由“无非劝戒”,到“无非奢丽”的转变?人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通常会首先想到这是艺术的自律性在起作用。张光直在论及中国古代艺术时明确指出: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艺术性特征也正是要从巫术与政治的关系来理解。”粗略地说,在巫术还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的早期国家阶段,“中国古代的艺术品就是巫师的法器”,而“据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人就握有了沟通天地的手段,也就是掌握了古代政权的工具”。⑥如果说远古时代的艺术性特征要从巫术与政治的关系来理解,那么,这之后的艺术性特征就应该着重从礼教与政治的关系来理解。这样去观察问题则不难看出,造成宋画由“劝戒”向“奢丽”转向的根本原因还是在政治方面。但并不意味它不从其他方面去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和配合当时的现实政治。由于注重技术和商业,宋朝统治者对于人们追求财富和享受的“侈心”并不过分压制,而且自身就痴迷于声色之乐,这就很容易酿成社会上下追逐“奢丽”的浮华风气,再加以宋代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艺术的繁荣也就有了物质上、技术上和财富上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宋画是从“奢丽”的方面顺应、配合着当时的政治。
“劝戒”色彩淡化之后的宋画是否就是一味的“奢丽”?米芾看到了“劝戒”功能在当时绘画中的废退,是其眼光独到之处,但其“无非奢丽”一语却不免带有偏激的成分。以文人士夫挑剔的眼光来看,宋画鲜有不“俗”者,完全合乎士夫画标准的作品恐怕少之又少,也许只有苏轼、文同几个人的画才算得上严格意义上的士夫画。既然有那么多的宋画属于或接近“俗”的范围,把它们统统斥之为“奢丽”肯定不合情理。由此看来,对于宋画的“俗”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宋画中大体可纳入“俗”的范围的,院画居多,也还包括满足社会各阶层审美需要的绘画作品。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若以当时人的眼光看,雅与俗的界限是相对甚至交错的。比如,著名画院画家李唐曾这样感叹:“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世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在李唐看来自己的画“不入世人眼”的原因就是太“雅”,但在苏轼之类士夫眼中李唐的“云里烟村雨里滩”也未见得就雅。现在我们不去深究这个问题,以一种大而化之的眼光来看,属于“俗”范围内的宋画则可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流行于宫廷或上流社会的,即“烟村雨滩”之类;一是流行于所谓“世人”中的,即“胭脂牡丹”之类。“烟村雨滩”与“胭脂牡丹”虽有李唐所为之无奈的差异,但两者其实有很多共同或相通之处。从整体上看,宋画的“俗”有以下几个特征:

由于“劝戒”作用的废退,宋代画师们的兴趣就从关注作品的思想性转向关注作品的形象性。具体而言之,画家们现在感兴趣的是所绘对象本身的形式形态,譬如,画月季,不仅要画出月季本身娇艳的姿态,还要画出它在清晨或午间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情态;画孔雀,不仅要画出孔雀升磴时的矫健轻盈,还要进一步画出其总是先出哪只脚的生活习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清明上河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宋画重形象的优点。张择端作为宋徽宗的御用画师,很难说其创作没有奉承上意的可能,不少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有什么倾向性的话,也是借助具体生动的形象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作品首先是以巨大的形象感染力感动观众,其倾向性则如润物春雨一般含蓄而自然,与那些唯恐说教意图不够显豁的“劝戒”之作迥异其趣。
由于对所绘对象本身形式形态的关注,宋画强调写生,注重细心地观察和捕捉对象的形态,生气、表情以及生活习性等等。这样一种注重写生与观察的态度和方法,恰好与宋代高度发达的技术文化相得益彰,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艺术一旦受到科学的影响,结果往往是不仅其客观性加强,而且会进一步追求合理性,于是,就有了宋画的第三个特征:讲理。郑午昌说:“宋人善画,要以一‘理’字为主,是殆受理学之暗示。惟其讲理,故尚真;惟其尚真,故重活;而气韵生动,机趣活泼之说,遂视为图画之玉律。卒以形成宋代讲神趣而不失物理之画风”。⑦郑午昌看出了宋画“讲理”“尚真”的特点,但将其归之为“理学之暗示”这一点却有待商榷。
最后一点,是宋画具有今人所说的开放和多样的艺术生态,这是它很不同于“古人图画”的地方。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是专制主义性质的,这种政治不需要什么透明公开,绘画、雕塑虽为其所用,却往往囿于皇宫禁苑之类特殊场所,而不是像古希腊艺术那样张扬于神庙、广场等公众空间,故中国古代美术具有相当的程式化和符号化性质,并始终有着一种难言的距离感或隐秘感。在中国传统社会绘画越是受到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重视,其艺术生态就越是千篇一律,呆头呆脑缺乏生气。绘画的这一命运在宋朝有了改变,宫廷虽然重视绘画并建立画院,但主要不是从“劝戒”的角度着想,另外,除了限制画院画家到社会上卖画以外,宫廷并不抑制社会各阶层对艺术的需求,因此,宋代绘画在院内院外都获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宋画的这一优点在《清明上河图》一画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古代第一幅全景式的反映世俗生活情景的鸿篇巨制。
宋画以上种种“俗”的特征,会心的“读者”都不难在《清明上河图》中“读”到。如图中的街景市容皆有所本,大都可以跟当时留下的文献资料比照互证,可见作者绝不是凭空杜撰,也不是凭一个仿佛依稀的大致印象,而是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细致的观察甚至写生的。又如,宋画讲神趣而不失物理之画风这一优点在《清明上河图》中也很突出。作为一幅记录当时都市生活全景的风俗画,要画得具体详实热闹不难,要画得曲折而富于机趣、生趣、神趣就很难,实际上自张择端画出《清明上河图》以后,过去和现在都不乏“续貂”者,但大多只能做到具体详实热闹这一步,鲜有把这种题材画得既具体详实热闹又气韵生动、机趣活泼的,故此类“续貂”之作真如苏轼所言,“看一眼便厌”。《清明上河图》的美有着宋画一流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平实、均衡、合理、大方、优美、适度的品格,既不乏浪漫主义的风采又具有现实主义的气质。凡亲眼目睹过这幅作品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图中的一切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平易近人,熟悉得令人心痛、平易得让人感觉自己就在画中……但同时,图中的一切又是令人惊异令人心向神往的。《清明上河图》的这种美感之所以如此动人,如前所言,在于它来自于人、来自中国人本身的生存情态和生活理想。《清明上河图》也可以说是宋代开放和多样的艺术生态所造就的杰作,张择端本身是宫廷画院中人,但他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一个非宫廷所能范围的大千世界,对宋画有研究的人不难看出院内院外多种画风在这幅作品中的汇集、升华。
正是这种魅力使它一问世就令世人为之倾倒,据说在南宋时,临安即出现仿品,它的这种魅力不仅征服了一代又一代有幸收藏、鉴赏它的人,甚至征服了那些仅仅闻其名而未识其面的“观众”,它还被写进小说、编成故事……被赋予浓烈的传奇色彩。《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能凭其“俗”成为经典,在于它的“俗”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被压抑被遮蔽被抹杀的状态,难得有机会露一头角,只是在唐宋两代,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它才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欣赏。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宋代才能产生《清明上河图》,也只有《清明上河图》才能把这个朝代的希望和梦想留存在薄薄的丝绢上。张择端的可贵,在于他以艺术家的灵性感受到了、领悟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的某种最能感动所有中国人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在宋代一度出现的世俗生活情态和理想。
注释:
①孟元老(南宋)撰:《〈东京梦华录〉笔记》,第十卷。该书在“清明节”一章中称:“……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士庶填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各携枣锢、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刍,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之日,皆出城上坟……”。
②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③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④黄仁宇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⑤郑午昌编著:《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
⑥同②。
⑦同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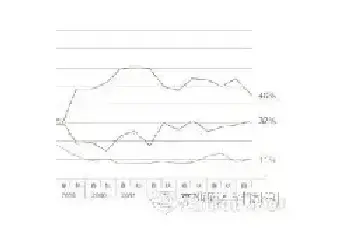
![具象油画与中央美院面临的挑战[图文] 具象油画与中央美院面临的挑战[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wqdgd1sqhh.webp)
![当代著名画家陈军工笔画作品欣赏[图文] 当代著名画家陈军工笔画作品欣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252uuo0dao.webp)
![故宫口红“宫斗”所引发的思考[图文] 故宫口红“宫斗”所引发的思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ealaeaddtp.webp)
![在颠沛流离中 他提炼出了“艺术中的精神”[图文] 在颠沛流离中 他提炼出了“艺术中的精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mbyw4h4ury.webp)
![城市在暗示什么?走近北美的机场艺术品[图文] 城市在暗示什么?走近北美的机场艺术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nnyucis221.webp)
![孔繁峙:14座被占用王府应纳入疏解范畴[图文] 孔繁峙:14座被占用王府应纳入疏解范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14fzjpyzn1.webp)
![彭望明:教书育人立榜样 书印结合扬国粹[图文] 彭望明:教书育人立榜样 书印结合扬国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a250umfzis.webp)
![关于收藏街头艺术 你需要知道的5件事[图文] 关于收藏街头艺术 你需要知道的5件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fpcvcrykca.webp)
![802绿钻暴涨400倍!四版荧光币真的要飞冲天了吗?[图文] 802绿钻暴涨400倍!四版荧光币真的要飞冲天了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lfrmp2u1wk.webp)
![2021特别推荐艺术先锋人物:画家闫旭[图文] 2021特别推荐艺术先锋人物:画家闫旭[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4gb4jlawxo.webp)
![狂放而不失静秀的有耳书法——郁民华书法印象[图文] 狂放而不失静秀的有耳书法——郁民华书法印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mxmqrrwcbz.webp)
![我的父亲-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周玉玮[图文] 我的父亲-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周玉玮[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mmss2jms1c.webp)
![红色经典悄悄成为收藏蓝海[图文] 红色经典悄悄成为收藏蓝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oqk1g1rae1.webp)
![新西兰华人画家创作钓鱼岛油画:表达民族情志[图文] 新西兰华人画家创作钓鱼岛油画:表达民族情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5vd4xb00cl.webp)
![髡残《层岩叠壑图轴》解析[图文] 髡残《层岩叠壑图轴》解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pr2y2ly5eu.webp)
![率意放纵的米芾《蜀素帖》[图文] 率意放纵的米芾《蜀素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iyqejlm0ad.webp)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4mhciphhag.webp)
![我国艺术品市场三大融合趋势[图文] 我国艺术品市场三大融合趋势[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2giimmqtaw.webp)
![米巧铭油画个展《无相》在泰国曼谷成功举办 [图文] 米巧铭油画个展《无相》在泰国曼谷成功举办 [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lyvmb5xd5o.webp)
![聚焦两会|推动李兆顺波画进校园,提升想象创造力,激发大脑潜能[图文] 聚焦两会|推动李兆顺波画进校园,提升想象创造力,激发大脑潜能[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bxv4mz1cft.webp)
![刘玉来:提高素养更上一层楼[图文] 刘玉来:提高素养更上一层楼[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nutks51auq.webp)

![【文脉华彩·罗建泉】时代颂歌|罗建泉国画艺术[图文] 【文脉华彩·罗建泉】时代颂歌|罗建泉国画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dzx5sdzolt.webp)
![我武惟扬 神骏赞歌·赵文元研究二[图文] 我武惟扬 神骏赞歌·赵文元研究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xfa1kb5amb.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