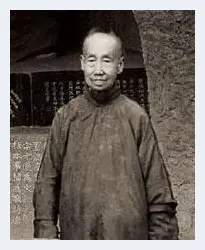
高居翰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写意——中国晚期绘画衰落的原因之一》,他说:“人们的观念中起码普遍地认为,写意是应该受到尊崇并追求的一种绘画特性,无人对此提出挑战。我想提出一种相反的看法:基于采用相对粗疏、率意的笔法制作简单化绘画这一最广泛的意义,写意手法的普遍使用,是清初之后中国画衰落的重要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他理解的写意是“近乎‘描绘(或速写)思想’这样的含义,以较为粗略和迅疾的方式完成绘画。”这显然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题目。文中他其实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指出寥寥几笔、快速制作一些重复性的画面,比如扬州八怪的商品画,这种写意绘画是造成清以来绘画衰落的原因之一。认为写意是粗疏、率意的笔法,这种看法在清代确实存在。如郑板桥论画竹中就提到,有人画雪竹,不好好研究细节,反而托名写意,所以他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他还说,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遂能写意也。对写意的这种误解在今天仍然不绝于世,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吴昌硕展览进行清理和反思的。

大家公认到吴昌硕,他把文人写意推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在于他的金石入画,一改粗疏率意为雄浑超迈,开创了笔墨的新的审美境界。而且他把文人写意的本质通过他的作品揭示得最为彻底。正如夏中义先生分析他画梅。“苦铁道人梅知己,对花写照是长技。”(《巨幅红梅》)吴昌硕画梅是为某种诗性隐喻,用梅花来隐喻其人格理想的“性命”。“著笔不易吾天真,梅花性命诗精神”。吴昌硕笔下的梅是苍崖雪梅,不是槁淡的村梅。因为他从苍崖雪梅中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所以梅花就是他的灵魂。这里,吴昌硕的文人写意画写出的是文人的风骨、格调与思想。
把作品看成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看成是个体的自我实现、走向理想之境的过程,是自我安身立命的方式,这正是以儒学为根基之一的文人画的核心。所以文人画家都讲究修养,不断提升思想境界,成就理想人格,强调画品是人品的投射,通过作品成就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的传统绘画中都能看到“人”的存在。
这个“人”首先是审美主体。古人强调审美主体的心和意在艺术创作活动中起到主体作用,故有“言,心声也;书,心画也”的说法。刘长林先生认为,这导源于中华民族在最初的与自然相处和斗争中所形成的对自然及对人在自然中角色的认知和把握。《易经》勾勒了宇宙的秩序和运行规律。而在五行图式中,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处于对宇宙的领导地位,人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所以在中国造物史和艺术美学发展史中,人的主观意志和主体情感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而物之所以能成为传达主观情思的载体,就在于中国古人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根据易传的解释,人事和宇宙有着相同的秩序和规律,可以由同一卦象序列来表示,正因为这样,才有可能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来窥视人生的凶吉。人事是宇宙的映射,宇宙是人事的外化。所以,人们可以从自然世界中找到合适的载体,成为人心表达的寄托。
正因为如此,文人写意作品中的表现对象,是“不似之似”。它不会是写实,传统中如实摹仿的艺术一直没有占据主流,因为写实拘于物象,无法逼近内在性灵;也不会走向纯抽象,因为梅花即人,人与物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中国艺术的特点正在于托物言志、托物言情。

自克莱夫·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这一理论以来,使艺术形式相对独立出来,艺术家生命意绪和审美情趣的表达能够脱离客观对象的描写而存在。但这个与文人写意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文人写意不脱离对象,物即人。另一个区别在于“写意”有个“格”的问题,不是通过作品表现自己就好了。“格”就有高下之分。所以“人”其次还是“人格”之谓。中国画到最高层次讲求风骨、格调和意境。
我刚才说到文人画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个理想人格是有标准的,比如古代君子的人格境界有重义轻利、安贫乐道、自强不息等等。文人画讲意境格调,都是往高处去追求。像吴昌硕、潘天寿从个体的艺术才情出发,最后达到的是超越个体审美生命、足以标示民族乃至人类精神高度的艺术境界,一种新的美学高度。吴昌硕通过金石入画,达到苍浑古逸的意境,而潘天寿通过指墨创新获致沉雄高阔的境界。我想这才是文人写意的高度所在,也是区别于“表现艺术”的核心所在。
可以说,中国画的“写意”有很多“规定性”,对它的继承发扬,除了中国画领域本身要做出思考外,它已经对其他画种和表现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正如本次“写意绘画”展览的作品所呈示的那样。“写意”核心怎么坚守?其边界能否拓延,譬如是否强调了审美主体的心性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强调托物言志、人品画格的高格调,就可以归为“写意绘画”?这些问题,也许正可以藉由此次吴昌硕展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当阳峪窑残片:古陶瓷上首现曹操、张良[图文] 当阳峪窑残片:古陶瓷上首现曹操、张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dt1wjphd1i.webp)
![让更多人看到博物馆藏品才是最大的爱国主义[图文] 让更多人看到博物馆藏品才是最大的爱国主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wyjgkyul0l.webp)
![不忘初心 中国梦——著名画家杨进禄作品欣赏[图文] 不忘初心 中国梦——著名画家杨进禄作品欣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oxwj4wzhp0.webp)
![【作品赏析】彼得·彼德洛维奇·斯穆克罗维奇作品巡回展[图文] 【作品赏析】彼得·彼德洛维奇·斯穆克罗维奇作品巡回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iep1g53hxp.webp)
![艺术赞助名目繁多 你都知道有哪些[图文] 艺术赞助名目繁多 你都知道有哪些[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0sc4fqwulj.webp)
![吴冠中:说王怀庆的油画艺术[图文] 吴冠中:说王怀庆的油画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kdeubknyzg.webp)
![王本杰作品欣赏:与内心情致互为表里的苍茫山水[图文] 王本杰作品欣赏:与内心情致互为表里的苍茫山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hls0mpwizt.webp)

![著名画家关麟英国画艺术鉴赏[图文] 著名画家关麟英国画艺术鉴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1aplznrujz.webp)
![清末海派画家潘振镛:仕女画的绝唱[图文] 清末海派画家潘振镛:仕女画的绝唱[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zq4v3v1fcy.webp)
![于受万的彩墨工笔[图文] 于受万的彩墨工笔[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r1jb1oylpu.webp)

![数十年磨一剑——谈武锋笔下“行隶” 之新美[图文] 数十年磨一剑——谈武锋笔下“行隶” 之新美[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5ntobtrsfr.webp)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窄门中 谁还能更进一步[图文]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窄门中 谁还能更进一步[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pozo1buknp.webp)
![波罗的海蜜蜡原石为什么能占领蜜蜡市场?[图文] 波罗的海蜜蜡原石为什么能占领蜜蜡市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c4wqncj5ok.webp)
![率意放纵的米芾《蜀素帖》[图文] 率意放纵的米芾《蜀素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iyqejlm0ad.webp)
![内地秋拍挖掘“生货”进行时[图文] 内地秋拍挖掘“生货”进行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i2tccbse3x.webp)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日本茶具[图文]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日本茶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obxw0kmh3r.webp)
![论博物馆创新维护的重要性[图文] 论博物馆创新维护的重要性[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zw4qnhzr14.webp)
![上海一年300多场艺术特展背后的秘密[图文] 上海一年300多场艺术特展背后的秘密[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g5114x0x5w.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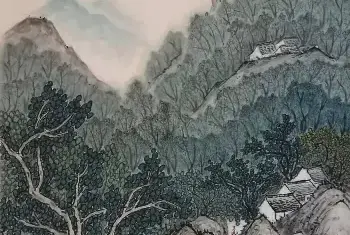
![六十名驹 华夏图腾 ·赵文元研究三[图文] 六十名驹 华夏图腾 ·赵文元研究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wrm55x4hsq.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