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勃罗·毕加索 晨歌 布面油画 195×265cm 1942年
巴勃罗·毕加索 晨歌 布面油画 195×265cm 1942年
1940年6月14日,德军第四军的步兵师在进行曲《普鲁士的荣耀》的伴奏下列队穿过凯旋门,正式占领“不设防城市”巴黎,并在城中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这似乎未对隐退在家的艺术家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年)造成太大影响。即使是法西斯气焰甚嚣尘上之际,艺术家也依旧是我行我素,似乎战争从未对他的生活乃至艺术创作产生任何影响。然而战争的灾难对于这样一位终生都保有对世界的热情和真诚的艺术家来说,真能如此冷眼看穿、无动于衷吗?显然不是,正如艺术家自己曾向人剖白的那样,“在这样的时候,我并不到外面画画,而只是到外面看一看,然后回到我的工作室,画我画上的东西。但是我所画的每一样东西,难道都与眼下发生的一切无关吗?”
确实,在整个二战期间,毕加索几乎从未离开过巴黎的工作室,即使面对纳粹德国的军官几次三番的上门找茬以及盖世太保一而再再而三的骚扰,他也从未想要离开,一直潜心创作。期间有如《格尔尼卡》这样直接控诉战争罪行的作品,也有一系列反映战争对人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的作品。而现藏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晨歌》正是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重要作品。
《晨歌》创作于1942年,其时德军已经全面控制巴黎,毕加索因在创作上一直与法西斯分子持对峙的姿态而开始被打压,并不被允许举办展览,这样的状况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而从毕加索艺术创作的分期上来看,这一阶段是介于“古典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时期”(1917-1932年)和“田园时期”(或称“毕加索创作晚期”,1946-1973年)之间的“蜕变时期”(1932-1945年),这一阶段作品的特点虽不如前面几个阶段那么鲜明,但作品的面貌较前期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更加成熟,从作品的内在逻辑上看,与古典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时期仍保持着紧密的延续性。这些特点我们在《晨歌》中能窥见一二。
“晨歌”原是古罗马时期的一种诗歌形式,在中世纪的“普罗旺斯抒情诗”中达到顶峰,常常表现情人在共度良宵之后,于黎明破晓时分的离情别绪。吟游诗人常常使用曼陀铃或吉他作为伴奏乐器,含情脉脉为情人吟唱这样的诗歌。我们在毕加索的画中看到的正是这样的画面:吟唱者怀抱曼陀铃,坐在情人的床边。床上的女子袒露着她的胴体,静静地聆听着。房间幽暗密闭得令人窒息,裸女如麻绳般拧结着的身躯躺卧在坚硬的床上,吟唱者正襟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右手似乎悬在半空,或者正欲开始演奏,或者刚刚结束他的吟唱。画家有意用大面积的冷色和暗色铺陈并渲染整个画面,吟唱者的皮肤呈现着鬼魅一般的蓝色,而衣着也呈冷灰色调,唯一的亮色便是僵卧在床上的裸女,于是画面笼罩着一种紧张和不安的氛围,墙上、地板的直线条无情地切割着整个空间,更加强化了画面在视觉上的压迫感。仅仅通过感受画面所传达给观者的视觉信息,我们就能清晰地体会到艺术家创作时的内心——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恐惧的关怀。虽然画面所描绘的内容并没有像《格尔尼卡》那样直接表现战争或灾难场面,激烈地抨击和谴责法西斯分子的暴行,但在表现受到战争碾轧的心灵和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与创伤上却能更为广泛地引起反战者和受到战争荼毒的百姓们的普遍共鸣。
当然,《晨歌》作为毕加索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除了鲜明的反战观点之外,从艺术史自身的评判标准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图式上看,毕加索的《晨歌》所表现的斜卧女人体姿态是艺术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觉母题,其传统大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如最著名的乔尔乔内《沉睡的维纳斯》以及提香《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正是这一母题最好的代表。而作为一个向来被认为对传统具有颠覆和破坏精神的先锋艺术家毕加索,他所创作的这件作品中斜卧的裸女是否真的与这一图式传统有些许关联?是后人刻意比附,抑或艺术家有意为之?
从现存毕加索的作品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初,也即我们说的“古典主义与超现实主义阶段”的后期,毕加索似乎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探究这一图式,从留存的数张习作中都可以看见类似的裸女形象。可以说艺术家有意在研习这一图式的创作,但与一般的临摹不同,毕加索可以说只是借着这一经典的视觉母题,实际仍在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和实验。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二者的关联的话,我们只需将毕加索曾认真取法过的画家安格尔所创作的《宫女与奴仆》与《晨歌》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两作间的许多相似之处以及密切的关联。
正如一句流传甚广的毕加索的名言所说:“艺术家的眼睛,可以看到高于现实的东西。”毕加索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闭门创作的时候从未有一刻放弃过关心外面所发生的灾难、人类所经历的创伤,他的确看到了更高的东西,并将它永远地留给了我们。

![企业收藏迎新使命:品牌建设与艺术要“双赢”[图文] 企业收藏迎新使命:品牌建设与艺术要“双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cg3bulzskh.webp)
![花鸟情淋漓 丹青意天成[图文] 花鸟情淋漓 丹青意天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ychfvvo4qr.webp)
![疯狂的石头真的疯了 翡翠今年狂涨不停[图文] 疯狂的石头真的疯了 翡翠今年狂涨不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uc23kgvaea.webp)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什么要重提毕卡比亚[图文]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什么要重提毕卡比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5dra3mfxf1.webp)
![艺术品拍卖背后的财务担保模式[图文] 艺术品拍卖背后的财务担保模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eto4ig20su.webp)
![关于收藏摄影作品 你需要知道的事[图文] 关于收藏摄影作品 你需要知道的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w2y2ttbbpq.webp)
![对话抽象表现主义 贾斯培·琼斯《数字5》浅析[图文] 对话抽象表现主义 贾斯培·琼斯《数字5》浅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04meyd4vyl.webp)
![鲁迅手稿缘何最为规整[图文] 鲁迅手稿缘何最为规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j0klswgkl0.webp)
![说牡丹:“一生爱好是天然”的痴男怨女[图文] 说牡丹:“一生爱好是天然”的痴男怨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dp5fwobh5m.webp)
![艺术的张力:愿众生平等[图文] 艺术的张力:愿众生平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tdceug2o4e.webp)
![博物馆与时尚的“羁绊”[图文] 博物馆与时尚的“羁绊”[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hs052l1vbd.webp)
![揭开江湖画家的面纱:如何界定[图文] 揭开江湖画家的面纱:如何界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szplbiqxoo.webp)
![双面蓬皮杜:因政治而伟大 因艺术而永恒[图文] 双面蓬皮杜:因政治而伟大 因艺术而永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3u40v0ukb3.webp)
![当数字技术遇见文化产业[图文] 当数字技术遇见文化产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o0xvkqmll0.webp)
![区块链引入艺术市场 带来金融产品级别透明性[图文] 区块链引入艺术市场 带来金融产品级别透明性[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isooh0gt5e.webp)
![艺术要为人类的最高文明奠基 ——《艺术市场》与人文艺术家周天黎对话[图文] 艺术要为人类的最高文明奠基 ——《艺术市场》与人文艺术家周天黎对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dsc4oh10or.webp)
![井上豪:西域壁画中的粉本与使用方法[图文] 井上豪:西域壁画中的粉本与使用方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1rz3acb1hn.webp)
![陈履生:博物馆是面镜子 创造和维护特色很重要[图文] 陈履生:博物馆是面镜子 创造和维护特色很重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mnliuebg3w.webp)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齐白石花卉册页[图文]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齐白石花卉册页[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pzow4tmkwk.webp)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4mhciphhag.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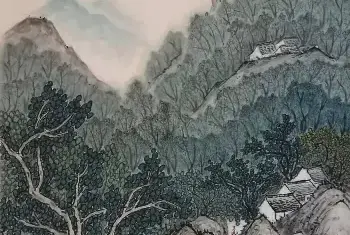


![我武惟扬 神骏赞歌·赵文元研究二[图文] 我武惟扬 神骏赞歌·赵文元研究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xfa1kb5amb.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