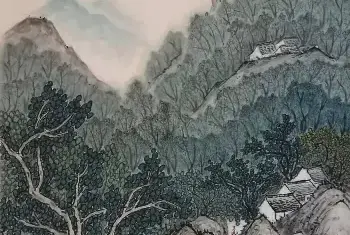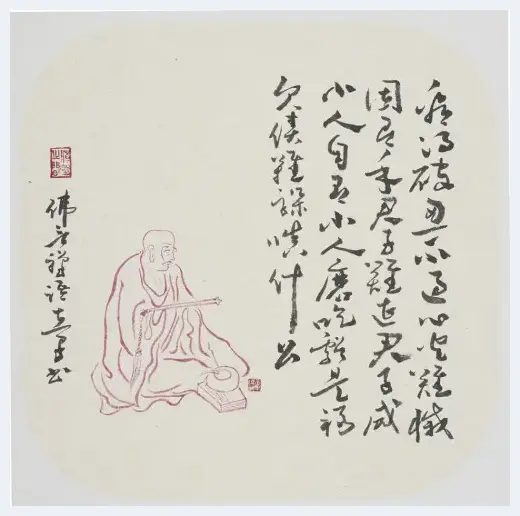
章剑华书画禅意小品
余秋雨
文化需要宏观,却生怕空泛;文化讲究精致,却生怕琐碎。遗憾的是,当代文化思维,大多陷于空泛和琐碎两极。不少人还在两极之间频频转换,一会儿大言宇宙洪荒,一会儿痴迷雕虫小技,独独缺少正常的目光、理解的阐释。空泛之害,使文化脱离大地;琐碎之害,使文化失去魂魄。这两种毛病发生在历史转型期,很能理解,却需要引起注意。
文化上的弊端,仅仅靠批判并不能阻止,只有等待正面范例的引导,才能逐步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等待中,我读到了章剑华先生论书的一系列文章,颇为兴奋。

章剑华书画禅意小品
章剑华先生与历来多数书法理论家不同,他不是就书法论书法,而是去把书法放在一个现代宏观的文化架构来思考它的命运。他心中的文化架构不是一种静态的背景性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生命过程。文化变成了一种气势浩大的生活逻辑,书法只是其中一脉支流,这就使全部论述具有了雄辩的高位,而很多在实践中探寻和固守的书法实践家,往往正是缺少这种高位。

章剑华书画禅意小品
正是在这个高位上,章剑华先生在列数古今有关书法的各种定义后自己立了一个定义。他的定义只有二十五个字:书法是用笔墨对汉字进行造型处理的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这个定义看似平常,但只要对比了其他定义就可发现,它大胆舍弃了最常见的“书写”的概念,代之以“笔墨造型”的提法,又强调了“艺术形式”,使书法在疏离实用性书写功能后的生存趋势,获得了自由度很高的审美定位。同时,这个定义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情感”、“性灵”、“反映”等等非必需性成分,使文化逻辑显得更为干净质朴。能做到这样,只能是宏观思维的成果。

章剑华书画禅意小品
另一方面,宏观思维并没有让他凌虚蹈空。他始终保持着对书法艺术的深挚领悟、精细感觉,并以这种领悟和感觉来控制全部理论走向。照理,他既然在宏观上支持创新,那就很容易让理论变成一种单向鼓励,至少也会对已经发生的“创新书法”和“现代书法”进行包容式的“纯客观”介绍。然而,他并不是这样。他虽然也鼓励了,也介绍了,却绝不掩饰自己的感觉。例如,他在介绍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书法”时,明确批评这种书法“对汉字进行粗暴的夸张和变形”,“创作者受某些功利目的驱使不能心态平静,导致书法作品人文精神含量降低,出现‘不到位’的创作浮躁现象”。这种现象,有目共睹;但这种阐释,却难能可贵。

章剑华书画禅意小品
总之,对于书法,他站得很高,又潜得很深。这样一来,他对中国文化整体走向的思考,也就有了一口实验性的“矿井”。对一个文化思考者来说,有没有这样的“矿井”至关重要。有了这样的“矿井”,就能探知我们脚下的地质构造、资源蕴藏、水源走向、危险所在,也就是说,从一个口道探知到大地的诸多秘密。如果没有,那就只能流于猜想和空论了。众所周知,在中国当代,这种没有“矿井”的文化学者还是不少。

章剑华书画禅意小品
歌德说,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一个宏观理论家如果能够从大地深处汲取水源、获得矿藏,他的理论也就有了避免灰色的可能。我后来有机会读到章剑华先生论述其他文化课题的文章,又看到了他自己的书法作品,更清楚了他的这种两相滋润的健康结构。他论述其他文化课题时视野开阔,方位独特,语气果断而诚恳,几乎不会绕在复杂的概念圈里让人纳闷,这就让人想到他自己毕竟是一个“艺术中人”,不必用理论迷雾来掩盖自己对艺术的隔阂。他的书法作品,由二王、孙过庭到于右任,取的是既有历史等级又有笔墨生命一途。既然他长年累月地一笔笔去写了,因此宏观也就有了支撑。

章剑华书画禅意小品
我本人对中国书法的走向也关注多年,不少看法与章剑华先生近似。我的整体文化观念和书法实践又与他不尽相同,这更增加了我与他心灵对话的乐趣。与章剑华先生相比,我对艺术文化发展前途的看法可能更加随意,更没加谱,更不学术。我觉得艺术文化的高层次推进完全取决于天才个人的出现,而这种天才个人的出现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中国文化的重大使命是尽早发现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伤害,或免于在追捧中沦于一般。至于他们会开辟出一个什么时代,则很难预计。

章剑华书画禅意小品
最后要顺便说一句,《墨语》,真是一个好书名。既简洁又典雅。是在谈墨,还是墨自己在谈?都可以。笔墨有自己的生命力,通过一个个书写者发出声音。书写者首先是谛听者,听听在墨池笔端某些轻柔却又无可置疑的指令。然后,才是表述者。

章剑华书画禅意小品
我这样说,并不是看轻艺术理论。虽然我个人早已告别艺术理论,却知道它存在的意义。艺术理论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要进行清理、考问、评判,使之优劣有界、良莠可分。这对于一代代的艺术新手而言,至关重要,对于其他读者艺术素养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艺术理论对于刚刚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创作活动,也会作出某种裁断和预计,如果裁断和预计有争议,那就展开讨论,这对艺术家和读者,都有好处。理论家不是法官,不是家长,他们的任务也不是吹捧谁、否定谁,而是在滔滔语流中逐步形成一种社会关注的气氛,适合文化艺术的滋生、普及和发展。在这方面,章剑华先生以自己的努力提供了范例。更何况,章剑华先生与我不同,是一个职位很高的文化管理者,因此更需要用理论方式进行思和阐释,建立起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公众文本”,让大家明白他的意图,取得某种社会共识。

![国画大家刘旦宅作品《渊明爱菊图》赏析[图文] 国画大家刘旦宅作品《渊明爱菊图》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p2fc05myos.webp)
![大国巨匠:刘仲文献礼双节[图文] 大国巨匠:刘仲文献礼双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dfdgn3gia0.webp)
![《2022年特别推荐当代最具收藏潜力艺术家》——林哨雷[图文] 《2022年特别推荐当代最具收藏潜力艺术家》——林哨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s2b4xhaxo4.webp)
![浅析主题性创作的构思思路[图文] 浅析主题性创作的构思思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pg5qyncsz2.webp)
![对于亵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我们只能说不[图文] 对于亵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我们只能说不[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t1bw0j3ybi.webp)


![清代画家余省的《种秋花图》 秋时种菊之奇[图文] 清代画家余省的《种秋花图》 秋时种菊之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1ke2ugs0nr.webp)
![近30年 当代艺术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图文] 近30年 当代艺术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gpi1uapadr.webp)
![“我笔写我书”——彭云峰书法赏识[图文] “我笔写我书”——彭云峰书法赏识[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gdun5ceaxs.webp)
![孔繁峙:14座被占用王府应纳入疏解范畴[图文] 孔繁峙:14座被占用王府应纳入疏解范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14fzjpyzn1.webp)
![刘杰当选第十届中国美协副主席[图文] 刘杰当选第十届中国美协副主席[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tgtzzzaaks.webp)
![村民上交西周石斧获奖100元遭吐槽[图文] 村民上交西周石斧获奖100元遭吐槽[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cw1oq24ehr.webp)
![振衫高岗濯清流——葛润翰及其国画艺术[图文] 振衫高岗濯清流——葛润翰及其国画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b3vuddv00z.webp)
![从禁售象牙制品看工美技艺的传承之道[图文] 从禁售象牙制品看工美技艺的传承之道[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xjriujxdpm.webp)
![艺术品市场出现回暖迹象[图文] 艺术品市场出现回暖迹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upxypgr5k1.webp)
![仙鹤是一品鸟古时常入画[图文] 仙鹤是一品鸟古时常入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fa0wbz0vcj.webp)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4mhciphhag.webp)
![展览结束后 艺术品都去了哪里[图文] 展览结束后 艺术品都去了哪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zrmepgyii4.webp)
![吴冠中《双燕》与孤独的文艺青年[图文] 吴冠中《双燕》与孤独的文艺青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alrhbdkqzl.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