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1956年摄于美国。(资料图片)
晚年梁启超在胡适面前常常喜欢有一点争强好胜的表现,他几次与胡适过招,往往是他挑战叫板在先,胡适应战在后,有时甚至就不应战,低调处理。发生在1923年的“国学书目”之争就是这样。最初大约是清华学校的胡敦元等几个同学将赴美留学,请胡适拟一个“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的书目。(《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见《读书与治学》)其后,这个书目发表在2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并被3月4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7期所转载。《清华周刊》的记者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了这个书目,并于3月11日给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针对这个书目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和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胡适有一封答书,回复《清华周刊》的记者,他在书中对书目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并在原书目上以加圈的方式,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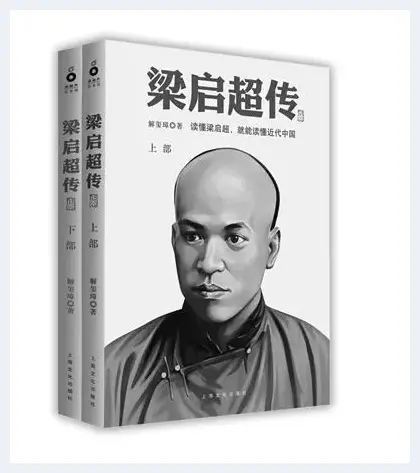
作者/解玺璋
大约这个时候,《清华周刊》的记者也将这个题目给了梁启超。当时他正在翠微山中休养,手中并无一书,而记者催得又很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于4月26日完成后寄出。或许《清华周刊》的记者曾将胡适所拟书目推荐给了梁启超,他在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之后,又做了《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两篇文章,先刊载于《清华周刊》,后来还出了单行本。梁启超将国学入门书分为五类,即: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时涉览书类。这五个类别大致涵盖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比胡适的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分法要高明得多。而且,梁启超的“书目”在注释、提要方面较为翔实,对所荐图书的特点、内容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切实的评价,尤其是用自己读书的切身体会启发青年学子,使人感到很亲切,也很实用。
胡适是“整理国故”的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领袖人物。梁启超更不肯落后,他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却意犹未尽,还要做《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其中不是没有要和胡适一争高低的想法,却也是在帮助胡适回答清华记者的问题。所以他批评胡适的书目是“文不对题”,他列举出三条理由:第一,不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只从个人的兴趣出发;第二,“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第三,忘记了学生在“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饮冰室合集·专集》)有这样一些缺点的书目,自然是不能满足学生要求的,“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的,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我们希望读过那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读书与治学》)对于清华学生的这种要求,胡适有些敷衍,于是,梁启超出来替胡适做他没有做完的事。这当然也和梁启超一贯的看法有关。他从来不认为读书只是为了求知识,如果只是为了求知识才读书,“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饮冰室合集·专集》)他曾经说过: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文,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个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
他在《治国学杂话》中依然发挥这种思想,即从做人的角度指导年轻人读书,他说: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饮冰室合集·专集》)
他希望读书能成为一个人修身养性,为人生确立安身立命之道的途径,他说: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饮冰室合集·专集》)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显,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寄希望于青年,但青年人要想担当起再造中国文明,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就不能只读西洋书,鄙弃中国书,特别是中国的古书。针对当时社会上激烈反传统,反对读古书的风气,他说:“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话说到这个份上,是很有些辛酸的,很难想象,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本民族的心里,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最大、最深刻,也是最沉痛的悲剧。梁启超也曾主张学习西方,也曾做过多年的“搬运工”,把西方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但自从游历欧洲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自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拯救人心,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他告诫那些将要出国留学的学生:
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饮冰室合集·专集》)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胡适并没有作出回应。实际上,在中国留学生必须读中国书这一点上,他和梁启超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在给《清华周刊》记者的复信中就曾指出:“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读书与治学》)很显然,除了在读什么书、为什么读书和怎样读书等具体问题上二人有一些分歧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分歧,所坚持的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遭到了来自鲁迅、陈独秀、钱玄同、吴稚晖等激进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吴稚晖就把梁启超与胡适视为同党,他以轻蔑嘲讽的口气说:
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恶当,公然把他长兴学舍以前夹在书包里的一篇书目答问摘出,从西山送到清华园,又灾梨祸枣,费了许多报纸杂志的纸张传录了,真可发一笑……他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都还要得。后来许多学术演讲,大半是妖言惑众,什么《先秦政治思想》等,正与《西学古微》等一鼻孔出气。所以他要造文化学院,隐隐说他若死了,国故便没有人整理。我一见便愿他早点死了。照他那样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科学与人生观》)

![劳笃文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图文] 劳笃文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550wmkopsa.webp)
![圣索菲亚博物馆之后 又一博物馆将改为宗教建筑[图文] 圣索菲亚博物馆之后 又一博物馆将改为宗教建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czsw1qhtuo.webp)
![74岁老人收藏万余个酒瓶[图文] 74岁老人收藏万余个酒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etba12tzry.webp)
![陆维钊和丰子恺的深情厚谊[图文] 陆维钊和丰子恺的深情厚谊[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y5husybdw3.webp)
![千年绝技只传女人 把绸缎变成雕塑[图文] 千年绝技只传女人 把绸缎变成雕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vigkokqljz.webp)
![55岁大叔扮“乾隆皇帝” 骗走深圳富婆4000万[图文] 55岁大叔扮“乾隆皇帝” 骗走深圳富婆4000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2c2blbuxao.webp)
![247万!国外艺术爱好者烧毁原画4倍价格卖出电子版[图文] 247万!国外艺术爱好者烧毁原画4倍价格卖出电子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poakwszxbn.webp)
![满满回忆!新中国同龄人高公博画的这些童年游戏,你玩过几样?[图文] 满满回忆!新中国同龄人高公博画的这些童年游戏,你玩过几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iwz0y2tjbh.webp)

![戒烟邮票里诉说远离烟的故事[图文] 戒烟邮票里诉说远离烟的故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oawt45111u.webp)
![河北省级非遗高梁秸秆制作技艺:匠心传承 巧夺天工[图文] 河北省级非遗高梁秸秆制作技艺:匠心传承 巧夺天工[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04fyokswh4.webp)
![这些“逆天”的文物 你见过几个?[图文] 这些“逆天”的文物 你见过几个?[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u5o3mmo1ry.webp)
![跟随插画师寻找理想爱情的模样[图文] 跟随插画师寻找理想爱情的模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umsardles2.webp)
![德国柏林城市宫发生火灾 开馆时间尚不确定[图文] 德国柏林城市宫发生火灾 开馆时间尚不确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ufzvy1jaev.webp)
![名为美国金马桶在丘吉尔故居被盗 价值百万美元[图文] 名为美国金马桶在丘吉尔故居被盗 价值百万美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vcb0vao5qd.webp)
![湖北行为艺术家巴黎悬空 所拍照片爆红网络[图文] 湖北行为艺术家巴黎悬空 所拍照片爆红网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yd0z3mahuq.webp)
![民间艺术家6年贴出62米布贴画 将申吉尼斯纪录[图文] 民间艺术家6年贴出62米布贴画 将申吉尼斯纪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snhfjlvaw0.webp)
![台湾1969年纪念币主角被找到[图文] 台湾1969年纪念币主角被找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cyy3vxrwsm.webp)
![毕加索的绘画与情人[图文] 毕加索的绘画与情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lknibigls3.webp)
![被法老诅咒过的五大稀世珍宝[图文] 被法老诅咒过的五大稀世珍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kq0hrsqy1s.webp)
![美院装裱师开博物馆 书画剩余材料历经几百年[图文] 美院装裱师开博物馆 书画剩余材料历经几百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oyzrhadlmq.webp)
![收藏小物件的快乐[图文] 收藏小物件的快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2oypxayrqu.webp)
![农家巧手女修复上万件文物[图文] 农家巧手女修复上万件文物[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de1juea4lh.webp)
![明四大才子文徵明与其《山房忆旧图》[图文] 明四大才子文徵明与其《山房忆旧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bckltgqawl.webp)
![英国网上发布4000页牛顿手稿[图文] 英国网上发布4000页牛顿手稿[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oq14urlzcb.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