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清代官绅的退休生活
官员和绅士到了晚年,早已功成名就,自宜于优游林下,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享受美好的人生。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举的赵翼(1727——1814年),在六十年后的嘉庆十五年(1810年)因重赴鹿鸣宴而自诩:“中岁归田,但专营于著述,猥以林居晚景,适逢乡举初程,蒙皇上宠加旧秩以赏衔,准随新班而赴宴。”晚岁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笔者阅览了清朝人物的百余种年谱,再回忆以往读过的清人传记,感到赵翼式的优游林下者有之,而不安于此者亦复不少,不可得此境遇者则更多。如若把他们的晚景归纳分类,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醉心撰述
笔者发现许多以文字为生的学者,或以撰著为主要职责的官员,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到了老年,仍孜孜不倦,继续著书立说,以之为人生的追求,写出大量的著作。另外以行政事务为主的官员,科举出身,本来有能力写作,晚年利用时间舞文弄墨而乐此不疲的也大有人在。
人们一提到明清之际的学术大师,必定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年)著述等身,年过花甲之后,新著和总结以前的著作又出了一批。他是余姚人,平时阅读诸家文集,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来。到六十三岁(1672年)时,将《姚江逸诗》十五卷梓刻行世,同时还辑有《姚江文略》、《姚江琐事》。次年到宁波天一阁阅览,把流通不广的书抄出书目,其他学人辗转抄写,从而使之流传于世。
康熙十四年(1675年)黄氏编辑成《明文案》,多达217卷,后被辑入《四库全书》。六十七岁将代表作《明儒学案》写成,这部巨著总括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史。自订《南雷文案》于七十一岁,并由门人校刊。到七十九岁,将《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修订,删汰三分之一,编成《南雷文定》。八十三岁得重病,应酬文字一概摒绝,力疾整理文稿,将平日读《水经注》的心得汇辑成《今水经》;适值《明儒学案》刻印校对,口述序文,由儿子代书。从这一年起,所作的文章,命名为《病榻集》。次年(1693年),将《明文海》482卷选成,又从中择出尤须阅读的文章编成《明文授读》。八十六岁寿终正寝,殁前,犹作《葬制或问》、《梨洲末命》等文。
顺康时期的诗坛祭酒王士祯(1634——1711年)成名甚早,然而终身在写作诗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六十二岁,任户部侍郎,“部务稍暇,与同人、诸及门为结夏文字之会”,将以前的诗词和杂文汇编为《蚕尾集》,古文词另编成《渔阳文略》。次年奉命去川陕祭祀山川,写诗百余篇,集成《雍益集》,并作《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会闻》,还认为自己写的诗少了,不如前次去四川作的多。六十六岁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上,撰成《古欢录》。康熙四十三年七十一岁结集《蚕尾续集》,同年因办案得咎,罢职回籍。七十三岁将当年写的诗集成《古夫于亭稿》,次年又将新作编成《蚕尾后集》。七十六岁新作《分甘余话》。辞世前一年的七十七岁已病得很厉害,仍有《己丑庚寅近诗》问世,同时《渔阳诗话》也编成。他的全集《带经堂集》92卷在他逝世后数月刻成。他自回籍即开始写作年谱,后来因病不能握管,口授由儿子代书,完成《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可知他在晚年,年年有新作、新书,与黄宗羲一样始终没有停笔。
南海人吴荣光(1773——1843年),任至湖南巡抚,六十八岁休致,次年作出《辛丑消夏记》,自订年谱亦写至这一年。七十岁出版《筠清馆金文》、《筠清馆金石文字》,并开始撰著《历代名人年谱》。及至病笃,研究工作仍未停顿,不能执笔,请人代书。儿子们怕他劳神伤身,劝他歇息,也是不听。原来吴氏“无他消遣,依然手不释卷,是以精神消耗,虽日服参剂,竟未奏效”。不过,17卷书总是完成了,未留遗憾。
以上几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究其缘由,约有三种。其一,多年形成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学术追求的延续。像王士祯、黄丕烈等人,可能他们就是把研究、著述当作性命之所在,乐趣之所在,人生意义之所在,所以才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后人看来,没有学术研究,他们的一生将大为失色。其二,为了丰富晚年的生活,将精力用到著书立说上,如吴荣光,没有别的嗜好,只有靠读书写作来消磨时光。在清代,人们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老人诗会,也很难经常进行。可以出外观光,如吴荣光致仕后到广西就医,游览桂林山水,然而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允许他外出旅行。而阅览写作,令精力有处使,可减少精神上的苦恼。其三,为了生活,不得不行文卖钱,以养家糊口,许瀚即是如此。
优游林下
官员告老还乡,不必案牍劳形,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袱;或虽罢官家居,有处分在身,但通常的情形是不会再出事的。这两种人都可以说无官一身轻,应当可以养尊处优,颐养天年。确实有这么一批人。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年),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十八岁休致,并未居于故里,而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出版《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藤花吟馆诗钞》。当其所造的北东园“草木日长,半亩塘中游鱼亦渐大,甚可闭户自娱”的时候,认为“浦中风俗日媮,省中时局亦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颇感不适。儿子们劝他远游避乱,友人约他游览杭州,遂举家出游江浙。因有家而不能归之意,自云为“浪游”。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至二十九年,遍历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旧友新朋。
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止,而是考订掌故,满足求知的愿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刻印《三谈》和《巧对录》。梁氏到苏州,朋友约他观光毕沅的灵岩山馆,他曾经去过,但是以前来去匆匆,这次为“考悉其颠末”,欣然前往。细细欣赏,一面感叹毕沅花重金而未能有赏盛的机会,一面将过往没有留意的楹联抄录下来,以备补入《楹联三话》一书中,因此感到“此游亦不虚矣”。到扬州,笔记写了一卷多,拜访其师、致仕乡居的大学士阮元,呈上《师友集》,阮元为之作序,誉为“他日必传之作”。游小玲珑山馆,请主人告知其来历,令后世读者亦能明了此园的建筑特色、名称由来和主家的更易。
满洲旗人麟庆(1791——1846年),官南河河道总督,道光二十二年因河决而罢官,其长子崇实认为乃父“以十余年两河劳瘁,一旦卸肩,反觉优游”,因而赶紧在北京“整理家园,并求田问舍,为娱亲之计”,建成半亩园。麟庆到京,于新宅举行满人的安杆祭天大礼,命长子夫妇主祭,表示不理家政,以颐养为事。同时,“访多年老友,相约游山”。携带二子东之蓟县盘山,历经上中下三盘,趁行宫除草之机,得领略其风光一二;北游居庸关,观览明十三陵,到汤山洗温泉浴;西游西山诸名刹和名胜,碧云寺、大觉寺、黑龙潭和玉泉山皆为足迹所到之处;西南去丰台,观赏芍药,再前行至房山,拜谒金朝皇陵,而这里被视为其远祖陵寝。居家的日子,与旧日的僚属校阅图书,鉴别旧藏字画。有时领着幼女、童孙玩耍,以输棋为乐——“所谓败亦可喜尔”。夏天在退思斋,“读名山志,以当卧游;读《水经注》,以资博览”。秋日夜读诸葛亮《诫子书》,产生与三十年前不同的感受。同时请人作画像,经营生圹。他是真正的优游林下了。
但是他也用心,每到一地,探其历史和特点,并且记录下来。在先他就请人作画,自写说明,每一幅画就是他的生活的一个片段。他说将这些画连缀起来,即为他的年谱。他在江苏任上已将其中的文字刻印出两册,图画未能刊行。回京后继续写、画,上面说到的那些行踪也都一一绘制成幅,其子说花多少钱也要全部刻印出来。他很高兴,及至弥留之际,将全稿置于榻旁,可见念念不舍。其子在他死后不久,于道光二十九年把全书刊刻完成,了其遗愿。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著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地方,即都有追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欲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其原委,即懂得事理,求得新知识。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致力族务家政
前述麟庆不关心家务,是老年官绅的一种类型。另有一批人热衷于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办义塾,训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又较多出现。
浙江海宁人查慎行(1650——1727年),五十四岁才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得康熙帝赏识。六十四岁引疾乞休。旋里后,应族兄之召入五老会,又举行真率会,“与宗兄弟劝酬齿序,杖履肩随,较农桑,量晴雨,间与田父野老咏歌盛世。且举家课,集子弟之能文者试之,有志者期以上进,自弃者勉其改行”。他以教训子弟为己责,“待子弟严而有恩,有过虽成人不少贷”。教育之外,修祠堂,兴祭田。陈敬璋在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谱》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谱主七十二岁条写道:“(查氏)一切世故不与闻,至关祖宗祠墓事,则存贮公产,嫌怨不避,经理出入,劳苦不辞,赎祭田,修祠宇,家虽贫,必竭力捐助,恒比丰厚者倍之。有时独立举行,虽困甚,弗顾也”。为什么这么认真?原因在于他认为子孙的功名财富,都是祖宗功德福泽所给予的,只有追远报本,才能保持家族的兴旺。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年),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四十二岁东归,四十八岁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五十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六十部。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他辞世前一年,自撰楹联云:“时至即行,再休恋身外浮云、天边朗月;知足不辱,问谁似殿前作赋、塞上从军”。他是把一切都看开了。
家庭家族成员的出处进退、身体状况,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人的健康,乃至导致死亡。湘军将领刘长佑(1818——1887年),官至云贵总督,光绪七年(1881年)休致。他的家法,“朔望必谒墓下”。他因在外从军,拜扫时日少,回籍后虔诚履行。当他六十七岁时,本在病中,而每拜墓必恸,因而病情加重。辞世那一年,他三弟的在四川候补知府的儿子病逝,家人不敢告诉他,他总问侄儿为什么不来信。及至其灵柩返里,家人无法再瞒,他因三弟已丧二子,再走一个,极度悲痛,头目眩晕,诸症复发,经诊治虽有好转,但数月后亡故。
坚持修身养性
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必定有一种理念,并以较强的自律能力去促成其实现,否则其成功是难以想象的。事实是有的人不能坚持,或不能全面地持之以恒,半途而废,放任自流;而有的人却能一以贯之,任何时候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坚定人生目标,愈有成就,愈加反省,老而弥笃。遗民、隐士可以说是后一种人的典型,在清代,这一类的人相当多,下面举两个人物的言行,以见其一斑。
明清之际的山西阳曲人傅山(1607——1684年),诗文、书法、医学样样精通,成就卓著。青年时代向往清明政治,明朝灭亡,甘愿隐逸,不做清朝的官,也不合作。顺治前期不幸吃了官司,事毕仍不改初衷。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要求官员推荐人才与试,给事中李宗孔等人荐举傅山。七十三岁的傅氏深知应试就是合作,就要做官,与己愿相违,故而称病拒绝。但是官府不放过他,催逼他起程进京赴考。县令戴梦熊派夫役强行抬着他上路,待到离北京城三十里的地方,他拼死不让再走。
这次特科,本为笼络人才,收买人心,故而官员重视其事。见傅山不上圈套,不给皇帝面子,怎么得了。一个个为在皇帝面前卖好,纷纷出动劝驾。首先是大学士冯溥屈尊拜访,百官跟进,傅山半躺在床上,声称有病,不能起床答礼,更不能应试。人们见他如此自尊自爱,反而更敬重他。所以史书云:“是时海内名士云集,高征君名,进谒者骈填户外,征君卧床蓐不起”。
他的山西同乡、刑部尚书魏象枢,见这样僵持令朝廷下不了台,出面打圆场,奏称他实在老病,请求免予考试。康熙帝允准。冯溥又密奏,傅山虽然未试,给予一官,以收人望,遂命为中书舍人。冯溥强要傅山到庙堂谢恩,傅氏坚决不答应,官方就报告他已病危,难于正式行礼,把他抬来,到了望见午门的地方,他伤心地泪流满面。冯溥怕出事,就地强行扶他下拜,他则趁势倒在地上,魏象枢赶紧说好了好了,已经谢恩了。冯溥、魏象枢等人演了一出戏,圆了皇帝的面子,而傅山始终没有妥协。事后他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再不会有逼我做官的麻烦事了;又说元朝的刘因,以贤孝闻名,被征召就出来做官,后来以母病辞职,希望别人不要把他看作和刘因一样的人,否则死也不瞑目,表示他并未接受清朝的官职。听到这话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总之,傅山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竭力自持,坚守初衷,不与清廷合作,保持了晚节。
颜李学派的首要人物以卓越的修养传名后世。他们生活在农村,亲自耕作,讲求实学,注重践履。李塨(1659——1733年)是学派的集大成者兼发展者。看冯辰等人给他作的年谱——《李恕谷先生年谱》,反复记载他的“一岁常仪功”,强调他的严于自律,悔过迁善。从年谱的写作讲,不免招来内容重复的批评,但在保存史料上则令人知晓李氏的自持精神。《年谱》云,康熙四十六年间(1707年)谱主四十九岁,“仪功如常。去琐碎,戒暴怒,勿听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习恭一次。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杂,年已将衰而德不立,惭哉!”同年,皇三子诚亲王允祉派陈梦雷征聘他。他以草野之人,不足供奉贵人辞谢。而前三年,朋友阎若璩应皇四子、贝勒胤禛之召进京。得病,李氏前往探视,劝他“老当自重”,即作为平民学者,或者说是隐逸,不应当与贵胄交游。李氏五十三岁时,惧怕倚老卖老,与友人书云:
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骄,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邃涵养,改过取善,雷行天复。不然,学且堕落,不唯愧负天下圣贤,亦吾师习斋之罪人矣。
七十岁的冬天他得了类似中风的病,夜不能寐,然而还做能作的事。至次年,每月《日记》的后面,仍然写着“小心翼翼,惧以终始”,自勉不懈。
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引退,因而隐瞒年岁。史书有所谓“官龄”之说,即反映虚报年龄现象的严重。隐瞒,有的也无济于事,被强行休致。但也有一类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或者感到圣眷已衰,也有厌倦政事的情绪,遂生归田颐养的卸肩之望,因此乞请休致,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
乾隆初年,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有各立门户的嫌疑。几十年后乾隆帝说:“鄂尔泰因好虚誉而进于骄者,张廷玉则擅自谨而进于懦者”。鄂尔泰对汉人大臣骄慢,也并非一点不知自禁。乾隆四年(1739年)他六十大寿时不许做寿,作谢客咏怀诗云:
无然百岁便如何,二十峥嵘六十过。官贵倍增惭愧事,恩深徒诵太平歌。
宾朋介寿思棠棣,儿女称觞感蓼莪。老至情怀难向说,不堪重许贺人多。
有难言之隐,不敢张扬。七年(1742年)即受到“交部议处,以示薄罚”的处分。九年腊月得病,次年(1745年)正月疏请解任调理,不准,四月亡故。十年后以胡中藻文字狱案而大被谴责。
蒋攸铦(1766——1830年),历任直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年(1827年)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两江,蒋氏具疏辞谢未成。次年奏称:“臣服官中外,有公是非而无私好恶;在己从不回护,于人何肯瞻徇”?可知圣眷已大有问题。十年(1830年)春因盐枭案被责问,九月奉命内召,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我年来精力日衰,难胜重寄,以受恩深,不敢请(退)”,到京可以“调摄宿疾”,或许身体能好起来。哪知行到半路,被革职,病死在山东平原县。
林则徐(1785——1850年)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逾花甲时从新疆戍地内调,先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身体也不好,一方面想为国出力,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督署任,返回内地。当道光三十年家居时,“设亲社,课戚中子弟”,有享受天伦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起程,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本人的思想状态,世事的状况。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不是其主观愿望所能决定,这就是为官的身不由己。想去位而不可得;继续仕途,可能会出新错,也可能新账老账一块算,没有好下场,如同蒋攸铦;即使皇帝一时顾全大臣颜面,不加重罪,也让人提心吊胆,如同鄂尔泰。如此在职的老臣,晚年的生活怎么会是美满的呢?

![外观俏皮的当代艺术雕塑[图文] 外观俏皮的当代艺术雕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ythrujivuu.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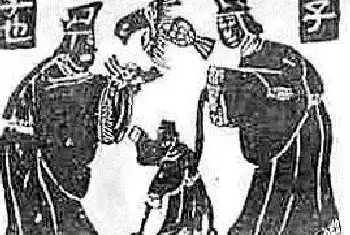
![裸女人形椅被指不尊重女性[图文] 裸女人形椅被指不尊重女性[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30m5k3g1ex.webp)
![美博物馆筹203万竟只修复一双高跟鞋[图文] 美博物馆筹203万竟只修复一双高跟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lw5ucrnhcv.webp)
![伦敦 那些让人心动的博物馆[图文] 伦敦 那些让人心动的博物馆[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irehb52hhm.webp)
![德国70年老厂展出世界最大玻璃地球仪 高达两米[图文] 德国70年老厂展出世界最大玻璃地球仪 高达两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315n4kuowi.webp)
![比利时奇想世界的小怪物想与你见面[图文] 比利时奇想世界的小怪物想与你见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gjpff1xttr.webp)
![一块平凡无奇的石碑 解开了古埃及之谜[图文] 一块平凡无奇的石碑 解开了古埃及之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epzefgrmuv.webp)
![就连充电都能很艺术 让手机仿佛悬在半空[图文] 就连充电都能很艺术 让手机仿佛悬在半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rrbx2bynnp.webp)
![古人的创意吊打我们千年[图文] 古人的创意吊打我们千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mmjwokgnam.webp)
![著名书法家闫锐敏先生收徒仪式在淄博中道国学院举行[图文] 著名书法家闫锐敏先生收徒仪式在淄博中道国学院举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21b2y4omrv.webp)
![逛潘家园夜市买下国画摆件,智利高人气总统钟情中国文化[图文] 逛潘家园夜市买下国画摆件,智利高人气总统钟情中国文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m3yh5okosx.webp)
![马悦然趣谈莫言托马斯共同处:都对自然界感兴趣[图文] 马悦然趣谈莫言托马斯共同处:都对自然界感兴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k3cn55mamg.webp)
![开启凡尔赛宫虚拟实境之旅[图文] 开启凡尔赛宫虚拟实境之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lwa1nwfl3u.webp)

![感受郑板桥[图文] 感受郑板桥[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tne3czx3xo.webp)
![梵高多幅画作隐藏科学谜题[图文] 梵高多幅画作隐藏科学谜题[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u1fd1hmr5g.webp)
![被法老诅咒过的五大稀世珍宝[图文] 被法老诅咒过的五大稀世珍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kq0hrsqy1s.webp)
![大器晚成的大家黄宾虹[图文] 大器晚成的大家黄宾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tshrq0v2wf.webp)
![画家杨之光微博指认赝品 其中一件拍出29.9万[图文] 画家杨之光微博指认赝品 其中一件拍出29.9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0bwjokniky.webp)
![两幅黄庭坚:真假美猴王[图文] 两幅黄庭坚:真假美猴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bjyvnm4zgl.webp)
![毕加索的裸女画在欧洲机场引起风波[图文] 毕加索的裸女画在欧洲机场引起风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vu5hcrduyx.webp)
![百元大钞水印上毛主席在微笑[图文] 百元大钞水印上毛主席在微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0uuqvpytvi.webp)
![《蒂凡尼早餐》房间卖585万美元[图文] 《蒂凡尼早餐》房间卖585万美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1j00po1w43.webp)
![拍卖史上最血腥的画3.5万英镑成交[图文] 拍卖史上最血腥的画3.5万英镑成交[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u0sbcen2re.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