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一种最重要的见证媒介,它的镜头谦卑地面向世界,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记录我们轻松地称之为“现实”的事物。在新千年的知识与技术条件下,客观真实的概念不断受到挑战;而在后摄影时代的作品中,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分界线持续被僭越。
后摄影时代是一个时刻,不是一种运动。在此我们提到的一些摄影家——鉴于有些艺术家并不通过照相机来制作照片,或者准确地说,这些从事摄影工作的艺术家并不服膺同一种制像哲学。不过,尽管他们的作品源自21世纪的各种不同观点,它们却的确处在同样的社会与技术背景下。

《无题》妮可·贝勒,出自《雷夫·桑切斯》,2008
2012年,位于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举办了题为“艺术之诱惑”的展览。这次展览对摄影作品与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同等重视,显现出在摄影即将迎来200周岁生日时,高贵严肃的艺术体制终于接纳了这种一直被视为“暴发户”的艺术形式。但如果说摄影正从艺术机构那里获得更多的认可,那它其实还面临着更多来自广义文化的压力。毕竟,每一个人都能拍照;而且,在数字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做。现实生活中到处是照相机;视觉世界里充溢着摄影图像。

《追捕》阿里奇·布雷恩,2009
21世纪,很多人都拥有智能手机,他们按下快门,随即就秀照片。跟这些业余摄影者相比,昔日那些大师如尤金·史密斯在匹兹堡项目中的狂热行为,加里·维诺格兰德在洛杉矶可笑的自拍如今看起来都太不张扬了。这些业余摄影者申请一个社交网络账户,就可以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秒钟的状态都用相机记录下来。“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记录,故我存在”。如今摄影已经是一种极为平民化的行为,“自拍”甚至成了2013年牛津词典的年度热词。

《暴饮暴食的非正常增长》鲁内·古纳佑森,2009
在后摄影时代,“拾得图像”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而互联网则成了重要的图像制作实验室。分享是数字时代的关键词;挪用——或者有些人可能更喜欢称之为“窃取”,则是后摄影时代的重要策略。这些富有创意的、变革性的“窃取”行为使得网络环境成为重要的“狩猎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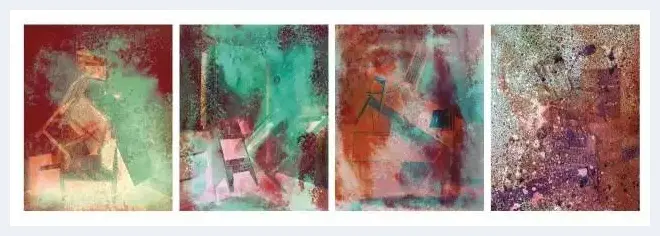
《休伊特的一大堆》斯蒂菲·克伦兹,2012-2013
浏览并创造性地将他人的图像吸纳至自己的作品中,如今这种实践成为很多摄影师(应该说从事摄影工作的艺术家)的主要工作。“ABC有很多卓越的艺术家,如安德列·施密特、米什卡·汉纳、赫尔曼·席格纳,他们都会大量使用搜索引擎和网络资料库去‘窃取’他人的照片,”里维斯继续说道,“在最近的阿尔勒摄影节上,我们参与组织了一次主题为‘从这里开始’的展览。这次展览的宣言开头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都成了编辑。我们都会回收、剪裁、重新合成以及上传。只要有眼睛、大脑、照相机、手机、笔记本、扫描器,再加上一种观点,我们就可以利用图片做任何事情。我们编辑的不是我们自己拍摄的图片,我们制作的照片数量却远胜于过去,因为资源无穷无尽,新的可能性层出不穷。互联网上充满创造活力:深刻的、美丽的、恼人的、荒谬的、琐碎的、民间的以及私密的,无所不具。’我逐渐认可了这种思想,现在我本人已经不怎么使用照相机了。”米什卡·汉纳对此做了阐释:“关健就在于‘拍照’这个短语。即使是从传统意义上来理解,这个短语也几乎不言而喻地暗示着图像早已存在,只待摄影师自己去发现、获取。所以我没看出太大区别。”

《无题》莱昂斯·拉斐尔·阿波德鲁,出自《约鲁巴族假面舞会》,2011
在2011年的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上,由摄影记者转型为艺术摄影家的迈克尔·沃尔夫因其作品《一系列不幸的事件》获得荣誉奖,引发争议。该作品是他在电脑屏幕前使用谷歌街景拍摄的。沃尔夫对《英国摄影杂志》的记者说:“我们的世界充满图像,这是未来影像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处理,对其去芜存菁,或者将其吸收到我们的作品中。我认为,未来我们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对所有这些图片进行精挑细选。你能想象今天我们到底有多少图像吗?这个数字是不可估量的。100年后,会出现一门叫做‘硬盘矿工’的职业,他们的任务就是在电子垃圾场找寻硬盘,并开发出新软件以对这些图片进行分类梳理。到时就会设立新的艺术项目和社会学项目,以利用这些从电子库存中挖掘出来的图像。这种对巨量图片去芜存菁的想法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火柴剪影》迦勒·哈兰德,出自《理解与争论》,2009
为了跟上图像制作的这种新形势,大量作品与作品系列将摄影师定位为编辑、策展人。“借鉴与创新”涵盖从约阿希姆·施密德作品中主人公们相似的观看行为,到克莱蒙特·瓦拉在《来自谷歌地图的明信片》中进行的先锋数字探索。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创造性借鉴这一主题,比如在《古卢现实艺术工作室》中,玛蒂娜·巴奇伽鲁普将拾得图像用于传统的新闻摄影。还有使用甚至滥用数字技术的,比如戴维·伯金富含数码故障的作品《嵌入》系列。

《费米斯顿露天煤矿,卡尔古利-博尔德,西澳大利亚州,澳大利亚》
戴维·托马斯·史密斯,出自《人间世》,2009—2010
人们最不可能从摄影中获取的就是客观真实。不过要说照相机比人能更客观地反映世界,这种说法也总是错误的。毋宁说,照相机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观看世界,而这也是很多摄影大师钟爱这门艺术的原因所在。加里·维诺格兰德说:“要是从取景器里看到很熟悉的画面,我会想办法把它摇开。”相机独特的观察方式是“现实的层列”。从奥利沃·巴尔比埃利使用移轴镜头和直升机,到李在镕探索数字叠加的潜力,这些技术形式都欲撼动我们的现实观。

茱莉亚·博里索娃,出自《奔至边缘》,2012
对新闻摄影界来说,2012年11月1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2012年8月份的《时代周刊》在其纸质版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张由iPhone拍摄的照片,由此宣告了摄影工具与摄影方式的重要变革。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并非普通的公民记者,而是颇受欢迎的战地摄影师本杰明·罗伊。近些年来,报纸和杂志纷纷将其摄影部门关闭,并训练记者们使用iPhone摄影(这是为了应对数字领域之扩张,因为后者已令其入不敷出)。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变化是悲剧性的;而另一些人则视之为解除禁锢,因为很多在传统新闻摄影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图像生产者如今正积极寻求新的方式去报道重要的新闻或思想。就克里斯蒂娜·德·米德尔来说,这涉及她对20世纪60年代赞比亚的太空计划所拍摄的视觉文件乃是公然的“伪造”(且引发争议)。这一项目及其他类似的充满想象与突破性价值的项目主题便是“后现代新闻摄影”。

《迪拜塔,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局部)、《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美国》(局部)
戴维·托马斯·史密斯,出自《人间世》,2009—2010
“你不是在拍照片,你是在制作照片。”伟大的美国风景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这样说道。这一提法在近二三十年内日益得到肯定,虽然亚当斯本人对此并没有很明确的设想或实践。毋庸置疑,数字领域中比比皆是的业余摄影者所带来的压力促进了当代艺术摄影中“管理模式”的发展。如果你对这个充斥着过量图像的日常世界感到失望,那你为何不建构一个自己的天地并且将它记录下来呢?艺术家们从事的工作中“整个世界都是舞台”。茱莉亚的项目“文档对象模型”(DOM,即Document Objective Model)亦是为此目的而做。

茱莉亚·博里索娃,出自《奔至边缘》,2012
艺术家们的确还在使用照相机,但是有种观点认为,仅仅拍照是远远不够的了。一些艺术家建构出他们所认为的现实,然后再拍摄;另一些将其拍摄的图像变成物体,艺术家再用手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干预。“摄影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正如同20世纪四十年代绘画领域中出现的抽象表现主义: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实体的、物质性的照片,而不仅仅是一张图像。”阿里奇·布雷恩说。对这位艺术家来说,穿孔机的地位跟任何一架照相机的地位同等重要。“这是因为我们身边充斥着大量的摄影图像,因此我们能够去考虑图像的材料,而不仅仅是图像本身。”当代摄影行为中的这种“物质性”倾向便是“手与眼”的主题。

《勃然大怒3》朱莉·科伯恩,2012
布雷恩的作品吸收并融汇了本书所考察的当代艺术摄影的不同发展倾向。在她那些明显更具“原创性”的作品中,这种对他人作品带有一定立场的观看产生的就是这种微妙的影响。与其说《十个彩色圆点之杰作》(仿委拉斯开兹)是对经典大师作品的挪用,不如说艺术家对经典绘画作品的构思与形式投入了时间与心思。布雷恩说:“我挑选一些绘画作品对其进行再加工,它们的创作者在绘画时探索了颜料的效果与物质性。这些贴上去的彩色圆点突出了图像的表面及错觉艺术的手法。这就跟用厚涂颜料的方法突出艺术家本人的存在,突出所有图像都体现的抽象本质是一样的。圆点还让我想到了所有机械复制图像中那些颜料的小点点。当我们对数字像素应用越来越多时,照片本身就成了彩色颜料的彩色小点,被困在纸张之中,由灯光来显示。”

![赵半狄称要办“猪选秀” 电影海报将用猪当模特[图文] 赵半狄称要办“猪选秀” 电影海报将用猪当模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agd0qwuqj1.webp)
![枣强七旬老农和他的碳粉画[图文] 枣强七旬老农和他的碳粉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ufpq1sig5y.webp)
![有个画家把苹果公司“法律条文”画成了漫画[图文] 有个画家把苹果公司“法律条文”画成了漫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fqekngsvsz.webp)
![千年前最大规模维京宝藏发现 暑假带娃却挖到黄金[图文] 千年前最大规模维京宝藏发现 暑假带娃却挖到黄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1sr3hjms41.webp)
![解密齐白石画作之谜[图文] 解密齐白石画作之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vp0wu1yjs1.webp)
![男子收藏上千把弹弓 市场估值近百万元[图文] 男子收藏上千把弹弓 市场估值近百万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ckdybt2op2.webp)
![上海将建设更新这8个艺术场馆 你最期待哪一个[图文] 上海将建设更新这8个艺术场馆 你最期待哪一个[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zl1gvuw4aj.webp)
![西湖无不佳[图文] 西湖无不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kpter2p5j1.webp)
![归根结底 街头班克斯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图文] 归根结底 街头班克斯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tlogb0w0vx.webp)
![李迪《狸奴小影图》:宋人有多爱猫?[图文] 李迪《狸奴小影图》:宋人有多爱猫?[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nlqfkle4se.webp)
![逛博物馆 我们吃点啥?[图文] 逛博物馆 我们吃点啥?[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clcqthq3tc.webp)
![唐风图:为诗经唐风绘制的插图[图文] 唐风图:为诗经唐风绘制的插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hjc3pm1b52.webp)
![福州关于郑和的两件国宝[图文] 福州关于郑和的两件国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jg10lxqr41.webp)
![丝路上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图文] 丝路上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ydf14sjkuf.webp)
![古钱币浓缩中国趣味[图文] 古钱币浓缩中国趣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n0swsghybj.webp)
![黄永玉配合一岁小孩画国画 无心之笔顿时有故事[图文] 黄永玉配合一岁小孩画国画 无心之笔顿时有故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mgcndtjcl5.webp)
![7000牛奶盒做成环保雕塑[图文] 7000牛奶盒做成环保雕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fsoa1belbt.webp)
![牧羊犬嘴刁奶瓶给羊喂奶[图文] 牧羊犬嘴刁奶瓶给羊喂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2i5snsgsa0.webp)
![康熙60大寿臣子送青花万寿纹尊 每个寿字都不同[图文] 康熙60大寿臣子送青花万寿纹尊 每个寿字都不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ecsuykwdz5.webp)
![趣闻:我国第一张全裸人体艺术照[图文] 趣闻:我国第一张全裸人体艺术照[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yn1vuzcjes.webp)

![茶叶也能当颜料 莫斯科艺术家创意惊人[图文] 茶叶也能当颜料 莫斯科艺术家创意惊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rk0bajb1d2.webp)
![另类车模[图文] 另类车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31x4rxyffe.webp)
![康有为故居叫价1000万背后:因康有为贵了一倍多[图文] 康有为故居叫价1000万背后:因康有为贵了一倍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5zuh5na1ty.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