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文心,《内存腐蚀》截屏,2017.
“不可退出”是当下社会状态中隐而不现之物,同时也是流媒体平台的扭结所在。
“让我在自己家里变成一扇门,我可以永远出门永远进门。”——金武林《变形记》
几个月前,我的手机收到好朋友杨紫发来的一张在线影院观影票。由他策划的这个题为“梦饮酒者”的线上观影单元共由11部影像作品组成,作者均为当代艺术家,片长从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扫码进入“影院”,却发现上映内容很难一次性看完,实际上在第三件作品出场之后,我就遭遇了强烈晕眩感的袭击,并直接招致了一段计划外睡眠。该反应与主题如此契合,如同策展的一部分。以随手分享影票图片的方式,二维码如同墙上的门,规定了观众的进入方式。在健康码尚未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之前,少有人意识到我们通过它只能进入,而无法退出。正如在此之前,我也从未意识到在真实的展厅中,那扇可以随时退出的大门在观展体验中竟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在“梦饮酒者”中,除非粗暴地退出程序,否则进度条就是一条你被卷入其中的翻涌的河流,在势能耗尽,百川入海之前无法被释出。
“不可退出”是当下社会状态中隐而不现之物,同时也是流媒体平台的扭结所在。尚未微型化的台式甚至柜式计算机曾试图伪装成普通家具,使自己驻留在“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一富有希望的修辞之中。随着计算机微型化和存储量激增,社交网络大行其道的背后则是不加选择的本地存储。不再是门的微型化手持媒体成为了一个个昏暗的地窖,通过疯狂存储,我们也被二维码不断地吸入到其他存储空间中。在公共场所每天都会被跌落的手机吸引片刻注意力的我们,却神奇地未曾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种“不可退出性”的单向度进程。
“不可退出”或“无法退场”,如果没有触及到这一真相,任何一种所谓“线上策展”都会因为低效的观看体验而趋于平庸,因其仍将微型或手持媒介视为现实空间的通道。如同大银幕与流媒体之间的致命差别一样:一种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持续对抗在现实空间中以象征性的形态发生,而流媒体则重新唤回了被影像最大限度拆除的“第四面墙”,变成了一种自我专制与他人专制之间的无缓冲对抗。相比于被导演与剪辑师处理过的影像,对于在特殊社会状态下失去现实空间的艺术来说,“第四面墙”的复魅伤害是更为致命的。在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看来,策展人曾以公意之名管理象征性空间,观众作为该空间(它必须与可退至的外部空间保持连通)的所有者对抗着艺术自律的专制。正是在艺术的“法的门前”,策展人用“专门为观者所设的门”的方式稀释着“第四面墙”。他的任务在于保持真实界与想象界不会直接撞击:前者是艺术家施于作品的数据编码,后者是观众所渴望的自控与认同。“不可退出”是象征界的消失,少有人有意识地体验过象征界消失的世界(虽然很多人曾经在娄烨的手持镜头中体验过这种生存状态)。

周岩,《我们俩:游戏漫游》截屏,2018-2019.
人们通常倾向于把“梦”与“醉”理解为一种或迷狂或优美的审美范畴,却忽略了“不可退出”才更精确地描述了这类体验,除了等待这一空间自行将你排出体外绝无中止的可能。将空间性的艺术装置复归于媒介中的数据流态,艺术作品自身的媒介性就被取消了,正如晕眩感(娜塔莉·杜尔伯格&汉斯·博格在《How to Slay a Demon》中通过切割第一人称视角所带来的)和对专注度的直接捕获(周岩,《我们俩:游戏漫游》中的画外音和引导观者打开开关的设定),它们因为象征界的消失而凌驾于作品的“意义”之上。而观者则直接被吸入数据流内部,主体性如在留声机的转盘上被甩干。
事实上,真实界对于想象界的直接铭写早在1900年左右就曾以“影响机器”(influencing machine)的形态出现过。当时最著名的偏执症患者法官丹尼尔·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人类灵魂藏于身体神经之中”的观念如何迫使他不断幻想各种电信通讯模型以形成自己的宇宙论。在德国媒介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解读中,这种妄想表达了一种避开感性干扰,直接记录真实界的可能,等待某种类人书写机器将其无损解读。这一极其类似于弗洛伊德“力比多灌注”(libidinal cathexis)的妄想曾令后者感到不安,它暴露了“心理分析”所掩盖的梦的原始机制。在“影响机器”幻想中,还存在着一种对于上帝在这一信息网络中威胁自身存在的担忧:上帝本人无法区分潜藏于人心底的死寂的自我(在弗洛伊德处被伪装成童年经验的东西)和此刻活着的人,从而无法得到被甄选的高效信息回馈,被缠绕于过分冗杂的神经之中。在那一代人朴素的臆想中,他们形容上帝会“拨错电话”(在阿米尔汗的电影《P.K.》中,他使用了这一隐喻来说明宗教冲突)。“梦”的媒介机制实际上困住了信息的发出者与接收者两级,艺术家所编织的信息闭合之网,同时也为自己所做。
某种意义上说,新媒体艺术趋向于信息铭写(被视为心灵感应)妄想的最终达成,凸显这一旧时妄想的当下结界化便是此类艺术与策展要给出的东西。于是,如果说在过去的“批判艺术”时代,艺术的任务在于揭露某种虚假意识,告诉人们“真实实为妄想”,那么新媒体艺术则需要告诉人们“妄想已然为真”。但从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那里回退一步,“不可退出”所带来的“无法享受”仍是我们能意识到的问题。新媒体艺术家们在偌大的工作室中使用着家具一般的工作站,自认仍站在新世界的门前,在建模和渲染的工序中穿梭于作为象征界的私人记忆——如张文心在《内存腐蚀》中所呈现的艺术家作为自己记忆之策展人的意图,却可能未曾想到其中所生成的媒介压迫(比如对于手持终端的使用者),以及艺术家的自我剥削。我们必须对这种数字经济中的数量级压迫有所意识:一种新的数字艺术体制中的阶级意识,同时也是这个时代阶级意识的新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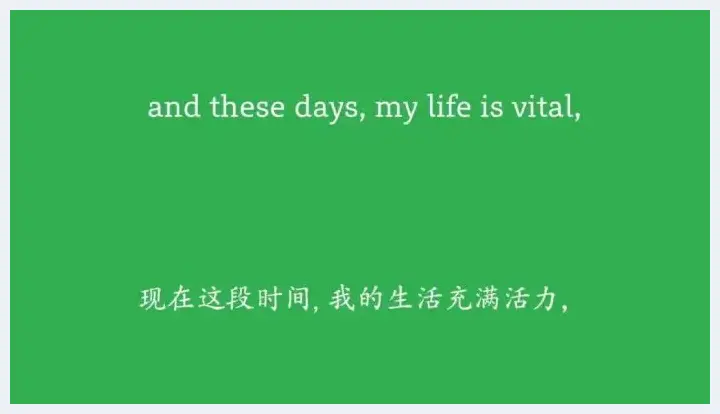
赵要,《有神的信号 - 抑郁症,我们分享的秘密》截屏,2018.
“梦饮酒者”似乎在寻找传达这一危机的方式,策展人也似乎有意地对这一封闭的媒介空间中的生存姿态进行了融合:旋转对于注意力的捕捉(陈天灼,《拉西亚》)、私人空间中的亚空间跃迁(《我们俩:游戏漫游》)、第一人称视角的切割(《How to Slay a Demon》)、匀速行进的数码有机体(《内存腐蚀》)……假如普遍性(哲学与科学)与个体性(艺术与经验)不再被肉身的我们所中介,这样的世界是可以承受的么?在“梦饮酒者”的终章(赵要,《有神的信号》),被之前所有作品消耗得精疲力竭的我,舒适地读完(听完以及看完)了所有字句。这样的字句或者说信号,也会遵循“黑暗森林”法则,被某种对抑郁症怀有敌意的存在所抹杀么?不,也许更为糟糕,由于“不可退出”的社会机制不再有一个可被想象的外部,即使是一种值得时刻警戒的鲜活的外部威胁都是不可得的,当下时代的威胁更多地来自于内部,也湮灭于内部。这也是新媒介潜藏的暴力所在:被时刻上传,而又时刻无法上传或表达。
当艺术力图拆除“第四堵墙”,以便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时,这面墙到底是被摧毁了还是被重置了?在被作为拆迁补偿的反思判断力失去了现实连接之后,我们又何尝不处于“成为墙”这件事本身的诱惑之中?也许在经典美学家那里被承诺为反思判断力的东西,在新媒体艺术家及其策展中应被转为一种穷竭一切的行动力。就像《内存腐蚀》中行走的躯体,却需要一种更快的匀速……
比如想象自己是一道光,只遵循最基本的光学原理,被不断的折射与反射,直到探明所有的墙。

![老腔古韵的承载--华山李澎书法新作[图文] 老腔古韵的承载--华山李澎书法新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kb01fvl5ed.webp)

![美媒:中国艺术品被加税 美商人难接受[图文] 美媒:中国艺术品被加税 美商人难接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i4ravdknyw.webp)
![文化认定与价值立场:考古学对历史文献的态度[图文] 文化认定与价值立场:考古学对历史文献的态度[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1bmuk3apqw.webp)
![现代主义画作 知人知世界[图文] 现代主义画作 知人知世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sigt3c0l52.webp)
![全民艺术普及 为何从年轻人下手[图文] 全民艺术普及 为何从年轻人下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egd5zbkncq.webp)
![安尼施·卡普尔:从概念主义到激进主义[图文] 安尼施·卡普尔:从概念主义到激进主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veg4bahuvo.webp)
![迟日摄影节 | 寒凉降临之日的摄影节[图文] 迟日摄影节 | 寒凉降临之日的摄影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lmql2sdblz.webp)
![艺术品租赁谁怕谁跑了:前景雾里看花[图文] 艺术品租赁谁怕谁跑了:前景雾里看花[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p3ynerdwm2.webp)
![衔思往 与时偕行[图文] 衔思往 与时偕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sabecyd4mb.webp)
![行走在大地之上的艺术[图文] 行走在大地之上的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peasdk4xju.webp)
![王羲之:大橘大利 新春快乐[图文] 王羲之:大橘大利 新春快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3bnfo5j4ew.webp)
![新一代亚洲媒体艺术造访德国 重思科技塑造的“新感官体验”[图文] 新一代亚洲媒体艺术造访德国 重思科技塑造的“新感官体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i5dsil5sbz.webp)
![吉州窑木叶盏:一片叶子告诉我们的事[图文] 吉州窑木叶盏:一片叶子告诉我们的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c0h0qpiorf.webp)
![感受深厚底蕴——人民艺术家朱继善国画欣赏[图文] 感受深厚底蕴——人民艺术家朱继善国画欣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hsgcdehfzm.webp)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齐白石花卉册页[图文]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齐白石花卉册页[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pzow4tmkwk.webp)
![不断崛起的东南亚艺术[图文] 不断崛起的东南亚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vxoc0x51sn.webp)
![透过自画像窥探著名画家内心世界[图文] 透过自画像窥探著名画家内心世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fanq25naga.webp)
![布尔乔亚:爱恨交织的生命痕迹[图文] 布尔乔亚:爱恨交织的生命痕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t1t3utrez3.webp)
![浅聊朝鲜刀剑的变迁[图文] 浅聊朝鲜刀剑的变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5mxsxjkg5u.webp)

![【文脉华彩·罗建泉】时代颂歌|罗建泉国画艺术[图文] 【文脉华彩·罗建泉】时代颂歌|罗建泉国画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dzx5sdzolt.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