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斯奎亚是高风险“艺术赌场”中的最新的野牌。图片致谢: Kenny Schachter
巴斯奎亚是高风险“艺术赌场”中的最新的野牌。图片致谢: Kenny Schachter
伦敦这座城市以金汤力(编者注:原文是 gin and tonic,作者的冷幽默)、培根与弗洛伊德、吉尔伯特和乔治、达米恩与翠西·艾敏而闻名。当我在2004年移居英国时,伦敦展现出的拍卖市场是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并被认为正逐步接近日渐衰微的纽约成为艺术市场的中心。但是,正如乔治·哈里森在1970年所唱的那样(也许他影射的是只是天气):
但一切不会总是如此,如此灰暗。
一切终将逝去。
一切终将随风而逝。
因为对市场完全不抱有信心,佳士得决定从伦敦的传统六月当代艺术拍卖中退出(在他们多年来企图说服苏富比也这样做之后),并将其注意力集中到远离其老牌地盘的地区,比如纽约和中国。而在我洞察一切的目光下,伦敦拍卖场的魔力正在逐步瓦解。这种势头似乎变得愈发不加掩饰。也许我还得对佳士得心怀感激,因为他们的退出让我可以少费些精力关注这场拍卖。
所有的拍卖行都让他们的拍品达到了他们拍卖估价的上限(即使是富艺斯与邦瀚斯也是如此),而去年大体上变好的成交成绩也呈现了一个乐观、健康、成熟的具有国际延展度的市场。但是这一切仍不能让我们逃避一个事实,这个市场已经不能产生火花甚至微小的能量。即使在伦敦拍卖市场成功的时刻,其衰退速度也已经超过了一座老庄园里马车凳上印花棉布的磨损程度。同样的,我也不能想象大多数画廊能卖出大量作品。
 R.B。 Kitaj’s 《地域之铃》(The Bells of Hell), 1961,26.5万英镑。图片:致谢Kenny Schachter
R.B。 Kitaj’s 《地域之铃》(The Bells of Hell), 1961,26.5万英镑。图片:致谢Kenny Schachter
噢,等等,其实我们还有伦敦大师艺术博览会(Masterpiece fair)和紧随着柏林(以及北京)脚步的梅费尔艺术周末(Mayfair Art Weekend)。尽管这些活动都有最好的初心,但这一切也许都会归于徒劳无功?大师艺术博览会也许更像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名词错搭,且夹杂着一些欺骗性的广告。但即便如此,我仍觉得其中有值得一看的点。在以艺术品鉴赏扬名的Offer Waterman画廊有一幅早期的原波普艺术家R.B Kitaj(我个人不是他的超级粉丝,我相信许多其他人也不是)的优质作品与一些Patrick Caulfield的画作,其估价在25万至45万英镑之间。我没能去走访很多画廊,但可能的话,我会去Sadie Coles画廊看望Nicola Tyson,他是上世纪90年代一起共事的工作伙伴。
拍卖与赌场中的冒险下注类似,每一场买卖都会产生新的赢家与输家——而每次的输赢局面都会依据骰子与转盘的翻转而改变,就像任何一种其他形式的赌博一样。艺术圈的这种微型循环和赌场上的局面没有任何区别。David Stockman是第一位(和唯一一位)明星级的预算部长官,他支持的是被人称之为里根经济学的理论。他赞同滴漏理论,也就是说为富人减税能为每位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带来连锁式的积极效应。(特朗普至今还不懂得这种政策如何导致了财政赤字)而尚·米榭·巴斯奎亚的流星式的市场膨胀就是一个艺术圈经济自下而上发展的最佳案例。在艺术世界里总是腰缠万贯的人得到的更多。
膨胀到失去控制的巴斯奎亚的艺术市场,引发出了关于这位艺术家的一切事物和内容,包括巴斯奎亚/沃霍尔的合作等等。市场往往会对艺术界的合作抱以质疑,尤其是在双方的主要合作不是一加一等于一的模式时。汤米·席尔菲格最近就将各大拍卖行变为了卸载自己艺术收藏的私人设计清仓商铺。(我听说他十分执迷于建造一艘超级游艇)汤米在苏富比的晚间拍卖出售了自己的一对巴斯奎亚/沃霍尔的画作,其中一幅的成交成绩还超过了预期值。
 汤米·席尔菲格的巴斯奎亚/沃霍尔在苏富比晚间拍卖以5737769美元成交,远高出估价2328590美元。图片:致谢 Kenny Schachter
汤米·席尔菲格的巴斯奎亚/沃霍尔在苏富比晚间拍卖以5737769美元成交,远高出估价2328590美元。图片:致谢 Kenny Schachter
估价在140万至180万英镑之间的《甜味辛辣》(Sweet Pungent),明显是汤米的出售的两幅画作中更优质的那一幅,其最终成交额在443.375万英镑(573.58万美元),创下了这个系列画作的第四高价。此系列的售价最高纪录是于2015年当代艺术市场高峰所创下的1136.5万英镑。那幅画也许被挂在了富艺斯的某位客户的客厅里,因为该记录的产生源于那家拍卖行。
另一个关于巴斯奎亚所引发的骚动的分支事件是沃霍尔与卢森堡画家Michael Majerus(1967-2002)合作画作的复制品。Michael Majerus和巴斯奎亚一样也在年轻时悲惨死去。他在一次商务航程途中飞机失事,与22名乘客中的19名一起命丧黄泉,那次的事件是卢森堡航空业历史上发生的最悲惨的事故。Majerus喜欢创作超大尺幅的画作,大胆、色彩绚丽的图案和文字是他创作的特征,看起来就像是一所广告代理机构制作室里的大爆炸。而“艺术只关乎艺术的调试与运用”则是他作品的另一条支线。
 Michel Majerus对于巴斯奎亚和沃霍尔的合作的挪用,上面有额外的绿色条带,这个作品为艺术家创下了记录。图片:致谢Kenny Schachter
Michel Majerus对于巴斯奎亚和沃霍尔的合作的挪用,上面有额外的绿色条带,这个作品为艺术家创下了记录。图片:致谢Kenny Schachter
在苏富比拍卖场上,估价在5万至7万英镑之间的《Mom Block Nr。 53》最终以23.675万英镑(30.68万美元)成交。这个成交价几乎是Majerus去年成交纪录的两倍。这个拍卖系列由巴斯奎亚/沃霍尔的缎面画附加多彩、粗犷的笔触点缀于画面之上而构成(包括蓝色、绿色、红色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上的条纹为绿色,那是一种通常被艺术市场所憎恶的颜色。Majerus以加上他自己的印记的方式与合伙人们进行合作(一种合作之上的协作),从而产生一种协助式的胜券在握,一场观者应尽力逃脱的动乱与不安。
在长久以来建立的艺术品原作价值高达数百万的评估体系中,你将如何衡量买卖之中的价值几何呢?最引人瞩目的行家出手从来都是大手笔。这一点在拍卖纪录上展现得尤其明显: Sturtevant(1924—2014)所收藏的安迪·沃霍尔所作的玛丽莲·梦露就在2015年以509.3万美元成交。而Mike Bidlo (b.1953)收藏的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则在2007年以42万美元成交,还有Richard Pettibone (b.1938)则在2006年以68.8万美元将自己收藏的波普派大师们的艺术合集像迷你饼干包装那样打包卖出。
 更多的猫王等于更少的钱:Richard Pettibone收藏的两个版本的沃霍尔的《猫王》,都是由苏富比售出,左边的一个价格为22.68万美元,而右边的价格则为其一半。图片:致谢Kenny Schachter
更多的猫王等于更少的钱:Richard Pettibone收藏的两个版本的沃霍尔的《猫王》,都是由苏富比售出,左边的一个价格为22.68万美元,而右边的价格则为其一半。图片:致谢Kenny Schachter
Pettibone收藏的估价在1.5万至2万英镑之间的安迪·沃霍尔的《猫王》(Elvis, 1964)最终在苏富比的拍卖上以17.5万英镑(22.68万美元)售出。而另一幅相同尺寸的相似画作(重复出现4次而非2次)在一周前的另一场苏富比拍卖上只以几分之一的价格售出。读者可以自己去查询。
另外,富艺斯晚场拍卖的满员程度看起来是其之前拍卖的两倍。由于拍卖场地中半数之多的座椅被搬走,参与富艺斯拍卖的人群看起来便像海市蜃楼般壮观。而拍卖场中的音响设备又是那样无可救药地糟糕,以至于你能听见卖场中每次竞价时的各种谈话声。尽管整场拍卖既没有华美的吸引力,又未能出现重磅的竞拍者,但富艺斯仍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即使它未能获得高古轩本人的青睐,或是被卓纳、豪瑟、Nahmads家族和Mugrabis所看好。
当一首流行或摇滚歌曲成为潮流趋势之初,它总能得到播完的机会,直至其受欢迎程度被大众熟悉后,最终被下一个新流行取代,艺术市场也是如此。伴随着摄影师Wolfgang Tillmans(b。 1968)近期于泰特和贝耶勒基金会举办的展览,这位艺术家便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而接二连三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Tillmans的作品在伦敦拍卖场上一共售出了7件,全部超过了其售前估价(除了一件作品是接近售前的上限估价)。这7件作品中包括了创造新拍卖纪录的《Freischwimmer#84》,其估价在20万至30万英镑之间,最终以60.5万英镑(78.551万美元)成交。富艺斯的一位拍卖商对此表示困惑,并声称:“关于这个成交额,我觉得我应该再去核查一下”。所以,Wolfgang的这碗意面能牢牢黏在墙上吗?还是这种拍卖的甜头会像一张曝露在阳光下的照片一样蒸发而去吗?一位拍卖经销商将Tillmans比喻为“当下的艺术家”,因为这位商人认为Tillmans的市场前景并不光明。而他也不想花时间等待去验证自己的想法,而是发展起音乐事业并为之陷入一片狂热之中。
在富艺斯的拍卖场,观众由16名成员组成。而在艺术圈里,往往只需几条电话热线与网络连接就足够组建一个市场。正因如此,当我在拍卖场上撞见画廊主HarryBlain时,我问起他为何出现在那儿,他如是回答:“为了上厕所”。我觉得他当时是开玩笑的(但我也不能确定)。
 Oscar Murillo,如何在三年之内,把5.5万美元变成4万美元。图片:致谢Kenny Schachter
Oscar Murillo,如何在三年之内,把5.5万美元变成4万美元。图片:致谢Kenny Schachter
现在来一段对艺术圈内幕的剖析:在僵尸形式主义(Zombie Formalism)的鼎盛时期,我的双手也沾满了污垢,因为我牺牲了常识去追求利益。我买入了包括Lucien Smith、 Christian Rosa、Israel Lund和一幅小尺幅的Oscar Murillo画作在内的一些作品。我喜欢Oscar,我不觉得他不诚实。但是当时我决定清理房屋,于是将一幅小尺幅的《无题》自2012年起放在了富艺斯售卖,并且希望能于2014年依靠此画挣取5.5万美元。但最终这幅估价在3万至5万英镑之间的作品以3.75万英镑(4.94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并给我造成了一笔损失。我也许应该考虑开设一个对冲基金,因为这些作品现在都在逐步贬值。
另一件出现在富艺斯晚场拍卖的Murillo的作品估价在15万英镑至25万英镑之间,最终以18.5万英镑(24.02万美元)成交,而在2015年11月的一场拍卖上这件作品的成交价就已达到24.5万美元。那么,唯一一件由卓纳画廊所拯救的极富盛名的僵尸派(Zombie)作品是否也正临着一场暗地中进行的重新评估呢?
 Sarah Lucus的《新宗教》(New Religion); 如此活泼的主题也再次被证明失败。图片:致谢Kenny Schachter
Sarah Lucus的《新宗教》(New Religion); 如此活泼的主题也再次被证明失败。图片:致谢Kenny Schachter
我是SarahLucas的粉丝与藏家。她的作品《新宗教》(红)是一口由不同颜色的(像Majeur喜欢做的那样)霓虹灯组成的棺材。那时曾两次买入这件作品的我的朋友试图将其出售,并希望将估价定位在10万至15万英镑之间。尽管我的朋友逐渐降低了他的期待值,但他也没有把局面弄糟到接受低太多的价格去卖。于是,在2006年有一位买家拿出了高出5万至7万英镑估价的9.6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这件作品。这件嗡嗡作响的三维霓虹棺材像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物的生动提醒,它也从不是一场简单的售卖。而现今再看,当年的这件作品已变成无价之珍贵。
无论是从社会还是政治的角度,伦敦都在逐渐左倾,随之而来的是其对境外与本土财富日益增长的敌意。但是无论其政策喜好如何,大笔的资金都是伦敦艺术行业的支柱。现在英国未入籍流民的可逗留期限已经从17年减少到15年,英国试图建立一个高贵的游民族群,一个反难民的难民群。而伦敦的拍卖市场则生存于这众多的灾祸(除高端住宅型物业外)之中。英国人喜欢瞄准射击,但他们此刻正在射击自己的双脚。
伦敦会逐步成为下一个科隆吗?那座曾经前沿的欧洲艺术中心现今甚至很难在国际艺术日历上留下一笔印记。而《金融时报》的头条如是总结上周伦敦的诸场拍卖:“来自亚洲的资金为伦敦带来了稳定”。但也许应该说正是亚洲的资金展现出了伦敦的过气与老态。再过一百年(甚至更短),从前城市里拍卖场中的遗迹也许会与最新的《人猿星球》的场景类似。然而因为原创艺术品价值连城,就算个人藏家在生意中损失数千或是伦敦失去了其商业中心的位置,也不能阻挡艺术界在这个夏天继续向前迈进,甚至比往昔势头更强劲。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沉住气、坚持下去。
文:Kenny Schachter
译:Phyllis Zhong
编:Cathy Fan

![启功曾炮轰书法界乱象:文化底子差还到处卖弄[图文] 启功曾炮轰书法界乱象:文化底子差还到处卖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taad3cypb2.webp)
![如何看懂当代艺术装置[图文] 如何看懂当代艺术装置[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tfu0043bbv.webp)
![收藏近代银质文房用品需关注纹饰[图文] 收藏近代银质文房用品需关注纹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ky3ml5ygip.webp)
![剑川石窟造像赏析[图文] 剑川石窟造像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2rndwzn121.webp)
![开局不利!新冠疫情下的艺术市场[图文] 开局不利!新冠疫情下的艺术市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gccr3vpo1w.webp)
![程大利:我的山水画观[图文] 程大利:我的山水画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edpl412qqs.webp)
![感受深厚底蕴——人民艺术家沈人诗书法鉴赏[图文] 感受深厚底蕴——人民艺术家沈人诗书法鉴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stpj2cj0ef.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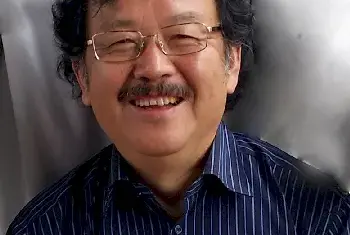
![高剑父:中国20世纪革新国画“教父”[图文] 高剑父:中国20世纪革新国画“教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sjylthfv4n.webp)
![名家风采 当代水墨写意人物画家:于立学[图文] 名家风采 当代水墨写意人物画家:于立学[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ftyx4lw23k.webp)
![四大拍行发家成名时刻简集[图文] 四大拍行发家成名时刻简集[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kv3s2mimys.webp)
![珂勒惠支版画影响中国现代艺术进程[图文] 珂勒惠支版画影响中国现代艺术进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nsi0mcavt4.webp)
![李冬君:宋代绘画中的士人人格共同体[图文] 李冬君:宋代绘画中的士人人格共同体[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ezzqjhqfnt.webp)
![2023年度书画焦点人物 —— 么相林[图文] 2023年度书画焦点人物 —— 么相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35013qznpt.webp)
![李人毅:感言中才丹青[图文] 李人毅:感言中才丹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3rect4hl2r.webp)
![达利欲念之作 《加拉丽娜》袒胸露乳[图文] 达利欲念之作 《加拉丽娜》袒胸露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3g1qlfyd2n.webp)
![潘天寿“一棵松树”2亿多![图文] 潘天寿“一棵松树”2亿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3jj5gxzogt.webp)
![透过自画像窥探著名画家内心世界[图文] 透过自画像窥探著名画家内心世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fanq25naga.webp)
![我国艺术品市场三大融合趋势[图文] 我国艺术品市场三大融合趋势[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2giimmqtaw.webp)
![2019年艺术市场方向:投机主义与大型画廊的主导[图文] 2019年艺术市场方向:投机主义与大型画廊的主导[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yt302hx30s.webp)




![用泥土和火焰绽放敦煌艺术---艺术家罗红[图文] 用泥土和火焰绽放敦煌艺术---艺术家罗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3ybozkgybz.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