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画定价殊不易也。米芾尝言:“书画不可论价。”(《画史》)但商定一个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又是进行交易的前提。
明嘉靖年间,王忬(1507—1560)所购《清明上河图》赝品的成交价,据田艺蘅(1524—?)说是“千二百金”(参见《留青日札》卷三十五),据李日华(1565—1635)说是“八百金”(参见《味水轩日记》卷一,第30页);江苏昆山顾氏(即顾梦圭、顾懋仁父子)家藏《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成交价,据文嘉(1501—1583)说是“千二百金”(参见《钤山堂书画记》第255页),据孙矿(1543—1613)说顾氏“实获千金”(参见《书画跋跋》续卷三,第991页)。《清明上河图》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明嘉万年间的书画价格有何特点?

《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原版)
明代怎样给书画定价?
为书画定价殊不易也。米芾尝言:“书画不可论价。”(参见《画史》第148页)但商定一个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又是交易的前提。
虞和讲过一个故事:“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直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云:但云王右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论书表》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卷二,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一),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39页)“字索一百”就是张彦远所说的“约字以言价”,(参见《历代名画记译注》卷二,第112—120页)即书法作品以字数的多少来定价。
这个标准也被后世沿袭,如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世时,作品就是按字数多少论价,“一字白银五分”。(参见《书画跋跋》卷一,第936页)《戒庵老人漫笔》中有一条记载,为我们探究书法作品的定价留下了重要线索:
逸少《二谢帖》真迹凡七十六字。后有赵清献公抃并苏子容等跋。字画亦无残缺。但墨气已尽。此余乡顾山周氏先世物,子孙欲求售,特携以问价于文衡山。曰:此稀世之宝也。每字当得黄金一两,其后三十一跋每跋当得白银一两,更有肯出高价者吾不论也。(参见《戒庵老人漫笔》卷五,第173—174页)
文徵明的定价标准也是“约字以言价”,王羲之的行书《二谢帖》在当时每字值黄金一两,其后的题跋每跋值白银一两。该帖共七十六字,其后有三十一跋。价格当为七十六两黄金又三十一两白银。
明末文震亨(1585—1645)有言:“书价以正书(即楷书、又称真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抵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黄庭》《画赞》《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记以字数。”(《长物志校注》卷五,第139—140页)其实,“书价以正书为标准”的提法源于唐人张怀瓘的《书估》,《书估》以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为例,论及书法的定价:
如大王(王羲之)草书字值,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书,偏帖则尔。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篇》《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惟鉴别之精粗也。他皆仿此。近日有钟尚书绍京,亦为好事,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洁库行书五纸,不能致真书一字。(《书估》,载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主编《书学集成》(上),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张怀瓘的定价标准是楷书(即真书)比行书贵,行书比草书贵。形成这种定价标准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王羲之的楷书存世量极少。在唐代“数百万贯钱”已经“不能致真书一字”了。其二是楷书的书写较行书、草书而言更为耗时。
明代张丑所著的《清河书画舫》(约成书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也沿袭了张怀瓘的说法,他说:“(王羲之)草十行敌行书一字,行十行敌真书一字耳。”(参见《清河书画肪》,第145页)可见“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在当时是受到广泛认可的。根据这个标准,楷书的价格要高于行书与草书,如明代张凤翼的楷书润例是写满一个扇面一钱银子,但行书八句却仅要三分银子(一两等于十钱,一钱等于十分)。(参见明·沈瓒著《近事丛残》,北京广业书局,1928年,第29页)李日华的一个细楷扇面要银一钱,单条草书每幅仅要五文钱。(《六研斋三笔》卷四,第243页)
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名价品第》中讨论了绘画的定价问题:
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即约字以言价,画则无涯以定名。况汉魏三国,名踪已绝于代,今人贵耳贱目,罕能详鉴,若传授不昧,其物犹存,则为有国有家之重宝。晋之顾、宋之陆、梁之张,首尾完全,为希代之珍,皆不可论价。如其偶获方寸,便可椷持。比之书价,则顾、陆可同钟、张,僧繇可同逸少。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以晋宋为中古……以齐、梁、北齐、后魏、陈、后周为下古……隋及国初为近代之价……若铨量次第,有数百等……夫中品艺人有合作之时,可齐上品艺人;上品艺人当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虽有合作,不得厕于上品。(参见《历代名画记译注》卷二,,第112—120页)
这段话有三层含义:其一,画价高于书价,因为“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明代的谢肇淛(1567—1624)也说:“盖世之学画者功倍于书,而世之重画者价亦倍于书也。”(《五杂组》卷七,第133页)其二,创作时间早晚(上古、中古、下古、近代)是古画定价的标准之一。元人汤垕在论及古画价值也说:“得伯时(李公麟)画三纸,可敌吴生(吴道子)画一、二纸,得吴生画二纸,可易顾陆(顾恺之、陆探微)一纸。其为轻重相悬类若此。”(汤垕:《古今画鉴》,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二)) 其三,艺术价值高低(铨量次第)也是古画定价的重要标准。书画定价和鉴赏品评往往联系密切。在初刊于明天启年间的《绘事微言》中,作者唐志契也论及绘画的定价:
画有价,时画之或工或粗,时名之或大或小分焉,此相去不远者也,亦在人重与不重耳。(《绘事微言》卷下,第66页)
这句话也有两层含义:其一,绘画作品是以绘制的工粗、画家名声的大小来定价的,即“时画之或工或粗,时名之或大或小分焉”。如仇英(1494—1552)的画作就以工细著称,他的画作在当时价位很高,据陈继儒(1558—1639,明代文学家、书画家)说可以和赵伯驹(1120—1182,南宋画家)抗衡。(陈继儒说:“今仇之声价,亦与千里抗行,谁谓古人相远也。”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但他画一幅画所耗时日也极长。他为周六观作《子虚上林图卷》“卷长几五丈,历年始就”,获酬百金。(参见《清河书画舫》;笔者注:另有一说《子虚上林图卷》耗时6年,依据为《眼福编二集》所记“嘉靖丁丑孟春夏六月始,壬寅秋八月朔竟,吴郡仇英实父制”,(此事参见杨恩寿著《眼福编二集》卷十四,徐娟主编《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其二,决定绘画作品价格的关键还在于买家的好恶,即“亦在人重与不重耳”。张彦远说:“但好之,则贵于金玉;不好,则贱于瓦砾。要之在人,岂可言价?”(《历代名画记译注》卷二)郑板桥(1693—1765)说:“方其富贵日,价值千金奇。及其贫贱来,不足换饼糍。”(参见郑板桥著《骨董》,载王锡荣编注《郑板桥集详注》)皆为洞见。
画价还因题材不同而有所区分。如明代高濂所言:“山水为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鸟竹石又次之,走兽虫鱼又其下也。”(《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文震亨也说:“画,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又说:“画价亦然,山水竹石、古名贤像,可当正书;人物花鸟,小者可当行书;人物大者,及神图佛象、宫室楼阁、走兽虫鱼,可当草书。”(《长物志校注》卷五)
从项元汴(1525—1590)的标价来看,同一作者的山水画价格远高于花鸟画价格。以元代画家钱选为例,项元汴为他的两件作品标过价格。一幅山水标价三十两银子(钱选《山居图》);一幅花鸟标价十两银子(钱选《梨花图》)。两幅画的尺寸大致相同,但山水画的价格是花鸟画的三倍。
画价还受尺幅大小影响。据《元明事类钞》(清·姚之骃撰)说:“王冕善画梅,不减杨补之,求者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元明事类钞》卷十八)可见,王冕就是根据尺幅来确定画价的,这可能是以尺幅大小为定价标准的最早记载。这种定价方式也被后世沿用,如清代书画家郑燮的润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周积寅、王凤珠编著《郑板桥年谱》,山东美术出版社,1991年)当然,在具体交易的时候,消费者更看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非尺幅大小。正如汪珂玉所说:“古人得佳画,不限于大小幅。”(《珊瑚网》画录卷七)

《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原版)
给《清明上河图》定价
上述定价标尺也可以用于《清明上河图》。首先,它是一幅宋画。按张彦远的三古标准,它比元画和明画珍稀。其次,它是一幅人物画。人物画分大小,它属于“人物小者”。按高濂的标准,它仅次于山水;按文震亨的标准,它可当行书。第三,它是一幅长卷。按王冕的标准,它比小尺幅的画作要贵重。

仇英(据陈继儒说他的画价可以和赵伯驹抗衡)
此外,《清明上河图》“卷前后钤宋人印数十上下”。(杨仁恺(1915—2008):《关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又“有徽宗御书‘清明上河图’五字,清劲骨立,如褚法。印盖小玺”。“卷末细书‘臣张择端画’,织文续上御书一诗云:‘我爱张文友,新图妙入神。尺缣该众艺,采笔尽黎民。始事青春蚤,成年白首新。古今披阅此,如在上河春。’又书‘赐钱贵妃’。印‘内府宝图’方长印。另一粉笺,贞元元年月正上日,苏舜举赋一长歇,图记眉山苏氏。又大德戊戌春三月,剡源戴表元一跋。又一古纸,李冠、李巍赋二诗。最后天顺六年二月,大粱岳浚、文玑作一画记,指陈画中景物极详。又有‘水村道人’及‘陆氏五美堂图书’二印章。知其曾入陆全卿尚书笥中也。”(明·李日华著《味水轩日记》卷一)这些钤于画卷前后的累累印记,以及题字、题跋都会让《清明上河图》凭附增价。
“凭附增价”语出唐人孙过庭的《书谱》。至迟在唐代,“凭附增价”已经蔚然成风。李白说荆州长史韩朝宗“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李白:《与韩荆州书》,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六)海内豪俊“一识韩荆州”,就可以“声誉十倍”,可谓典型的“凭附增价”。书画如果经过名人题识也可以“凭附增价”。北宋画家王诜就说:“东坡学士,天资敏慧,博雅好古,一经鉴赏,价高十倍。”(清·方浚赜:《梦园书画录》卷一,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十二))元大德年间,李珏携王维《辋川图》郭忠恕摹本去大都,“名公相一见,赏识鉴定,价增十倍。”

![以媒介的方式敲打媒介[图文] 以媒介的方式敲打媒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zzebv3s0vp.webp)
![宋徽宗与宋高宗书法艺术考论[图文] 宋徽宗与宋高宗书法艺术考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z2dle25yzp.webp)
![苏东坡的《木石图》估价4亿港元[图文] 苏东坡的《木石图》估价4亿港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iiyeaxuee2.webp)
![转角——2022芳之陈艾美人画展[图文] 转角——2022芳之陈艾美人画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nl31jgzls1.webp)
![浅聊朱德群作品价格走向[图文] 浅聊朱德群作品价格走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rm3o3ddww4.webp)
![艺术品估值的逻辑[图文] 艺术品估值的逻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zjje51hguy.webp)
![党旗飘飘 喜迎国庆——著名画家邱文银[图文] 党旗飘飘 喜迎国庆——著名画家邱文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yolo0ftdc5.webp)
![借机抬价的老物件古董新作有价值吗[图文] 借机抬价的老物件古董新作有价值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qvfffr13cq.webp)
![丁秋发刘智峰的北漂艺术解读[图文] 丁秋发刘智峰的北漂艺术解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q1yekg44lx.webp)
![断臂维纳斯 何以成为杰作?[图文] 断臂维纳斯 何以成为杰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kmo1ffohqk.webp)

![创作无能让艺术家沦为商人[图文] 创作无能让艺术家沦为商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mkfyzx51x4.webp)
![浅析版画收藏[图文] 浅析版画收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verjgow0sy.webp)
![刘玉来:齐白石心理十探—齐白石有仇官情结吗?[图文] 刘玉来:齐白石心理十探—齐白石有仇官情结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a5cl3lbagl.webp)
![中国画到底是什么?[图文] 中国画到底是什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0pghead4ir.webp)
![吴冠中《双燕》与孤独的文艺青年[图文] 吴冠中《双燕》与孤独的文艺青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alrhbdkqzl.webp)
![重在意境的民国田鹤仙粉彩梅花图瓷板画[图文] 重在意境的民国田鹤仙粉彩梅花图瓷板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roioj5u0f0.webp)
![布尔乔亚:爱恨交织的生命痕迹[图文] 布尔乔亚:爱恨交织的生命痕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t1t3utrez3.webp)
![展览结束后 艺术品都去了哪里[图文] 展览结束后 艺术品都去了哪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zrmepgyii4.webp)
![走向世界的苍松画家禹化兴[图文] 走向世界的苍松画家禹化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b0jxnkzfzy.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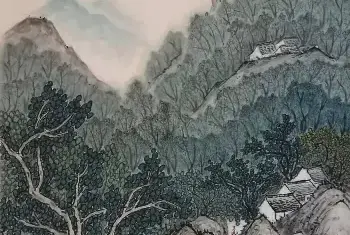
![用泥土和火焰绽放敦煌艺术---艺术家罗红[图文] 用泥土和火焰绽放敦煌艺术---艺术家罗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3ybozkgybz.webp)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阮礼荣[图文]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阮礼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1mmkjdegx1.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