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镜子》两季六集,一集一集地看下来,对我来说,一个不同以往的观片体验是,那重复了六次的片头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这篇观感必须从它谈起。
在我看来,“黑镜子”作为被强大科技支撑着的现代媒介的隐喻,是不可言说的言说,是不可视之视,而片头则将片名的隐喻可视化了。伴随着那段低沉的、混合着不规则音响的音乐,观看的心理自动地调节到恐惧、焦虑、激动、期待相混杂的状态,字幕的闪现是破碎的幻象,随着一声短促而清脆的声响,黑底的色块上一个裂纹呈现出来,如一道闪电照进黑暗,也如一把魔术师手中变出的利刃准备一露锋芒。于是,深广周密的黑镜子世界,闪电和利刃在它无边的身躯上留下一丝裂隙,透露一道光,让我们有机会一瞥其真容。
我们瞥见了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六集剧情的话,它们分别是:公主被绑架后绑匪胁迫首相与猪性交并电视直播,黑人小伙泄愤秀场却意外地成为节目主持人,植入体内的记忆芯片搅乱家庭,生者与死者实现语言和身体的交流,精神错乱者被置于精心设置的围观情境,名叫沃多的玩偶卷入政治竞选的漩涡。所有这些展示了从开放的公共领域到私密的个人空间,从思想到身体,从想象到实在,从日常到疯狂,从爱到恨,媒介无所不在的强大存在。那些夸张的、重口味的、神奇的、聪明的、骇人听闻的、不可思议的想象,有着高度一致的方向,也就是媒介及其背后的技术。关于黑镜子——现代媒介的想象可以说是这部剧集的全部驱动力量,它一个点一个点地铆足了劲地敲击,敲出了百般花样,也冲击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睁大了眼睛,试图看清媒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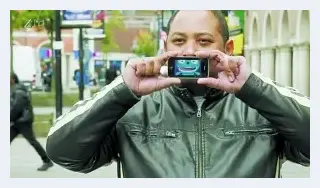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经过两次大战,媒介问题就是政府与政党、政客与学者、企业与组织都非常重视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怀其利,传播学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为一门显学。但是,还从来没有像《黑镜子》这样,媒介产品的生产者本身将媒介的隐秘、深广的联系抛诸公众,以一种“片面的深刻”令其面对那些多少有些令人不愉快、尴尬、愤怒、忧伤的东西,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最日常的生活,从生到死的一切,被媒介这个巨无霸控制着,我们在这样的控制中浑然不觉,它让我们感到如此自由以致我们将自由拱手相让,我们严重地依赖它,迫切地需要它,习惯地消费它,开心地享受它,心安理得地接受它的按摩同时也接受它的剥夺——不仅剥夺时间和金钱,而且剥夺思想和灵魂,如“沃多”那样的恶搞和搅局也只是游戏,如宾德森那样想与它作对,碰得头破血流不算,最后还被它收入囊中,为其服务,而他原先的真诚和单纯则成为最好的节目素材。

媒介这个词无论是从它的英文来源,还是中文本义来看,都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中介,它外在于主体,为主体所把握和运用。它如一面镜子照见主体的面容,人在其面前确立自我。但是,当它成为黑镜子,人站在它的面前,已无法确立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黑镜子》让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宣称的“人之死”。某种看不清、说不明的力量改变了媒介的外在性,媒介成为历史和现实的主体,而人成为媒介的附庸,技术的奴隶。当年麦克卢汉说出“媒介是人的延伸”时,可谓不乏乐观浪漫的精神。《黑镜子》接过麦克卢汉的话题,确实也让我们看到媒介对人的延伸——譬如,耳根下植入的记忆装置让人超越时空,电脑里模拟的程序让你完成穿越,无所不在的视频令人难辨真假……但是,《黑镜子》更强调的是在延伸之后对人的谋杀,媒介表面上依附着人,实际上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并暗渡陈仓,悄然谋取主体的地位。
实际上,媒介背后的技术伦理难题,一直困扰着文明社会。当活人实验秘密地进行,当原子弹对广岛的毁灭性打击,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直到最近的日本海啸引发核泄漏……科技进步里一直难以祛除的恶的力量,总是在一个又一个突发性事件中震慑人们,但事过境迁,灾难迅速地淹没在历史的暗夜。与这样的突发性、毁灭性不同,媒介技术更为日常化,它温情脉脉,体贴入微,投你所好,为你服务,给你快乐,甚至带来狂欢。在这样的表象下,一些我们从道德的角度称之为“恶”的东西,潜滋暗长,弥漫开来。《黑镜子》中不止一次地让我看到,搞笑的消息、丑闻上了Facebook或者Twitter,是如何迅速地像癌细胞作为物种自身在其转基因的环境中疯狂地、迅速地繁殖。
这一切何以发生?为什么会这样?《黑镜子》有颇多提示。第一季第一集中UKN电视台对绑架勒索事件急于播出的理由,第二集里戴墨镜的评委劝服宾德森的那套以节目为中心的逻辑,还有第二季第三集里那个从华盛顿赶来劝詹米继续从事“沃多”的说辞,等等,让我们感受到媒介混杂的各种声音背后,最为强大和清晰的声音是利益和权力的机制,它一旦启动就不会停止,不顺从它的逻辑将会引来灾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黑镜子》对政治、资本、产品这些宏大问题的涉及或暗示,更多的是缝合在对人的脆弱、人的无助、人的顽劣、人的易于被操纵这些特点的表现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黑镜子”扮演的是魔鬼的角色,而其“恶”之力的源泉便在于对芸芸众生的唤起,一种反启蒙。对人来说,这是真正的绝望之处,所幸的是,《黑镜子》依然让我们看到真诚的眼泪、刻骨的爱恨、抑制不住的愤怒,甚至还包括《白熊》里女主人公疯狂的呐喊……也正因为这些,对媒介黑色世界的敞露,哪怕是匆匆一瞥,才有其意义,才不至于陷于将虚无绝对化。
现在,稍稍回过神来,我们很容易想到,作为影像文本的《黑镜子》本身与它所敲击的对象实际上是同根同源的,它似乎是以穷尽关于媒介的一切黑暗情境来成就一部媒介产品,仿佛是一个反刍动物从胃里将自己吃下的东西吐了出来,在它没吞下之前我们看见了。这就是《黑镜子》的悖论,我们可以说,它充满了娱乐精神的产品是为了拆解娱乐;充满了技术炫耀的想象是为了拆解技术,充满了对媒介化生存的冷嘲热讽是为了拆解人心深处的魔障。
建立于如此悖论之上的媒介产品,应该享有“艺术”的称号,因为它是智力高超者的游戏,也是思想深邃者的追问。媒介大师麦克卢汉在谈到自己的秘诀时说,他面对媒介采取的是艺术家的态度,“艺术家的头脑在大家都认可的文化中对现实扭曲的暴露总是最敏感和最机智的”。麦克卢汉如果在世,不知道会对作为艺术作品的《黑镜子》作何感想。
链接
《黑镜子》第二季继续了第一季令人胸闷的黑色风格。陷入丧男友之痛难以自拔的Martha使用智能软件生成了一个克隆男友(第一集《马上回来》BeRightBack),参与绑架谋杀儿童的女罪犯被催眠一再模拟体验被追杀迫害的经历(第二集《白熊》WhiteBear),为了提高收视率电视节目组让一头蓝色的卡通熊参加下议院竞选(第三集《沃多时刻》TheWaldoMoment)——三个故事都从灵机一动不经意间的尝试发展成了不可收拾的黑色噩梦,噩梦的不可收拾来自真切无情的逻辑推演。
事实上,黑镜系列所处理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现代的特殊新问题,即使让山顶洞里的原始人看了这些剧集,从根本上而言他们也并不会有特别大的惊讶和费解。因为,我们如何知道现在的自己是真实的自己?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而不是黄粱一梦?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这是自古以来人类身处其中的问题和迷惑。黑镜的故事,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个与人类同样古老的基本问题——我们的所见所闻,是真实存在,还是仅仅是我们自身所分泌的想象世界?
与那些古老的真幻之问略有不同的是,黑镜系列所身处的世界已经被互联网、电视这样的现代媒介所包围,这些媒介使得人类自身所分泌的念想变成了可见可闻活生生的现场。而这些通过智能软件、剧场模拟和卡通虚拟所建立的角色一旦成为现实材料进入真实生活,真实本身却发生了破裂,变得虚假。
当Martha接起智能软件模拟已故男友Ash打来的电话时,无论观众抑或剧中的Martha本人都难以分辨出这嗓音、这吊儿郎当半是认真半开玩笑的调调与活着时的Ash究竟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如果那个活生生的Ash并未在车祸中丧生,而只是驾车到了另一座城市,Martha所能得到的情爱与温情,不就是这些电话中的俏皮话和邮件中的问候吗?一个活着的Ash事实上可能也就是这些互联网和大气电波中传播过来的电信号。因此,对于Martha而言,一个真实的Ash又出现了,他活在她的手机和电子邮件里。
真实就这样被模拟和重建起来,以至于电子的机器对于Martha而言成为了生命,当Martha一次不经意间将手机摔落在地时,她惊吓不已,忙不迭地向手机道歉。但诚实的人工智能告诉她,“我并不在手机里。”这个人工智能甚至哪里都不在,只需要下载到哪里,它就在哪里。它会调情说话但它没有嘴,只是一连串的数字而已。至此,Martha事实上已经触碰到了虚拟那背后不存在的实体,一具没有尸体的尸体,提醒她,那个她以为依然活着的Ash(该词本意,也是“灰烬”)事实上只是一团数字烟雾。但Martha显然过于投入了对电子幽灵Ash的这段感情,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致命的提醒,因此,她购买了升级服务,让人工智能按照Ash生前的所有视频、照片、网络发言克隆了一个有血有肉的Ash给她。
当那个按照网络所记录的生命痕迹所组建起来的克隆Ash出现时,悲剧就开始了。失去的生命,那个真实的Ash凶猛地涌现了,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从胸口的痣到各种习惯应答,无论这个克隆人怎么逼真地模仿Ash,Martha都觉得自己面对的绝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台假模假式的机器。因为真实的Ash不单会顺从和爱怜Martha,也会冷落和谩骂她,会朝她发怒,会毫无来由地莫名沉默——这些都不是那个人工智能所能演算和模拟的。
真实、独一无二的生命就这样证明了自己的不可复制,因为他是有死的,不可延续的,莫名其妙不可预估的,甚至是如此之易碎而类似梦幻泡影,一场车祸就彻底消失,无论多少兆的生命记录都难以挽回。只有承认这梦幻泡影般的虚无性,承认Ash已经彻底不存在,Martha才能真正地面对和把握那个真实的Ash。
我把评论大半的篇幅都给了《马上回来》并非出自个人偏爱。它在三集剧集中是情绪和意味最为丰富,最具有黑色幽默感,对真实与虚拟界限问题的探讨也是最为深入和细致的。第二、三集——《白熊》和《沃多时刻》在这个根本动机上的展开都并未突破《马上回来》的深度,只是在政治色彩和剧情的惨烈上加重了口味,但情节逻辑的推演展开更像Martha所执迷的那个人工智能程序本身,一个方案一个逻辑一条道走到黑,显得相对简单和缺少了变化。就根本问题而言,能说的话,其实在第一集中都差不多说尽了。

![莫奈最后的人生:看不见色彩 看得见哀伤[图文] 莫奈最后的人生:看不见色彩 看得见哀伤[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qpna5z0jux.webp)
![中国书画真假问题一直是软肋[图文] 中国书画真假问题一直是软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zuisjd4goa.webp)
![多年不见的金猴邮票 互联网大佬周鸿祎买了一整版[图文] 多年不见的金猴邮票 互联网大佬周鸿祎买了一整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o4mlifjw1h.webp)
![巴黎画派为什么至今无法超越[图文] 巴黎画派为什么至今无法超越[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pjdzgej3pe.webp)
![张仃焦墨画“离骚”——读《巨木赞》[图文] 张仃焦墨画“离骚”——读《巨木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so5d4t2qgf.webp)
![靳尚谊: 弘扬中华美育 塑造美好心灵[图文] 靳尚谊: 弘扬中华美育 塑造美好心灵[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2ok0wwtw11.webp)
![美神宫主薛林兴倾情央视美女主播[图文] 美神宫主薛林兴倾情央视美女主播[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2jxhqoeeec.webp)
![5G到来 艺术界将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图文] 5G到来 艺术界将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e4l3v2qxd1.webp)
![盗墓与气候变化双重夹击下的蒙古考古[图文] 盗墓与气候变化双重夹击下的蒙古考古[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4dxiw204tl.webp)
![在山水经验中探究艺术 科学与思想的关系[图文] 在山水经验中探究艺术 科学与思想的关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tib1z14to5.webp)

![冷军临摹的俄罗斯油画《春潮》赏析[图文] 冷军临摹的俄罗斯油画《春潮》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x5juvwbpih.webp)
![章太炎与乐清人朱镜宙的翁婿情[图文] 章太炎与乐清人朱镜宙的翁婿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oc5e2xsnxn.webp)
![如何与空间交流 对蔡磊个展“景别”的回顾[图文] 如何与空间交流 对蔡磊个展“景别”的回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venhwgziwk.webp)
![高原画魂——高原画派一代宗师马西光[图文] 高原画魂——高原画派一代宗师马西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2px3lm5dbs.webp)
![浅聊朝鲜刀剑的变迁[图文] 浅聊朝鲜刀剑的变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5mxsxjkg5u.webp)
![好的人物画必有技术难度[图文] 好的人物画必有技术难度[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omtcb4cs3h.webp)
![走向世界的苍松画家禹化兴[图文] 走向世界的苍松画家禹化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b0jxnkzfzy.webp)
![不断崛起的东南亚艺术[图文] 不断崛起的东南亚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vxoc0x51sn.webp)
![郑忠后抽象水墨画解读[图文] 郑忠后抽象水墨画解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nbazsn1wu5.webp)


![丝绸之路北方行·赵文元研究八[图文] 丝绸之路北方行·赵文元研究八[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r23mjylez2.webp)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阮礼荣[图文]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阮礼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1mmkjdegx1.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