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摩图》(明代吴彬,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达摩图》(明代吴彬,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射雕英雄传》里,江南七怪数千里跋涉,终于在蒙古找到了郭靖,夜里在荒山上等着考验他的时候,不意间发现了草丛中的三堆骷髅头骨,头骨上还有五个手指插出来的窟窿,不禁大惊失色。“黑风双煞”的骷髅头道具,记得在看电视演绎时,带来的恐怖效果确实非同一般。
但要是回到明代,可能就不会有这般的恐怖效果,有一段时期,骷髅头骨还是送礼的流行呢。万历十四年(1586),王世贞在生日时为避宾客,躲在青浦的泖塔中诵经焚香,不料还是被好友张佳胤获得踪迹,派人送来了两样生日礼物:一个“异僧颅骨”,一套白玉杯盘。颅骨颇费好友搜寻苦心,尤显珍奇,王世贞于是欣然收下(《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四《赠张肖甫司马》)。颅骨即“骷髅法碗”,以高僧头颅骨作为饮器,盛净水作供奉佛祖之用(续稿卷一百八十七《张助甫》)。佛舍利供奉并不鲜见,头颅骨、头顶骨作为法器,则源于明代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番僧,所带来的流行。
顶骨数珠、骷髅法碗等,在很长时间内,是番僧进贡所献的常规物品。倪岳《止番僧疏》说:“为纠劾事内开法王领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污我中华礼义之教。锦衣玉食,靡费钱粮。前拥后诃,擅作威福。献顶骨数珠,骷髅法碗,以秽污之物,冒升赏之荣。”(《皇明名臣经济录》卷十三)宫廷的流行波及开来,加之番僧也有夹带的贸易,就形成了一种风尚。《水浒传》中,武松假扮行者避难,是从孙二娘处,得了一位头陀的“一百单八颗顶骨数珠”。金圣叹对这位头陀的来历,甚感兴趣:“又见张青店中麻杀一头陀,竟不知何人,吾又胸前弥月不快。”(《金圣叹评水浒》第四十九回)番僧进贡本有定规,准其名位高者国师、头目等入贡。但各朝政策宽严不定,规定也形同虚设,成了一本糊涂账。宣德、正统间每次入贡三四十人,景泰间增至三百人,天顺间达到二三千人。由于赏赐丰厚,有很多伪造护照身份,冒充番僧来领赏的(《明宪宗实录》卷二十一)。所以,也活该金圣叹郁闷了,因为作者是照着明代的环境写的,戴着顶骨数珠的番僧,并非稀奇到必有名姓可查;况且这头陀的身份,极可能来历不明,或者本来就伪造身份,故此落单在内地乱窜。
比江南七怪更无语的遭遇恐怕是嘉靖皇帝了。嘉靖十五年,皇帝打算拆掉宫城内的佛殿,改建成太后居所,派几位大臣进去看看选址如何。结果发现里面贮藏着无数的佛头、佛骨、佛牙,有用金银盒子装着的,也有散落的。已经无法用件数来清数,只好称重,计有“一万三千余斤”(《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五月)。大臣们的意思是拿去埋了,毕竟有“佛骨”之名。但在追求长生、肉体不灭的道教徒嘉靖的眼中,这分明就是一万多斤的骷髅枯骨,还堆在寝处其中的紫禁城,怎么想都还是恨难消,于是下令拿出宫外焚烧扬弃了。
在十五年的清理佛骨后,又于嘉靖二十二年,下令拆毁了靠近宫城而建的大慈恩寺,驱逐居停其中人数众多的番僧,把这所宣德年间重建,能登高望远的宝刹名胜,拆得“寸椽片瓦亦不存,今射所是也”。(《万历野获编》卷一)沈德符说嘉靖皇帝虽然驱逐了番僧,可惜他自己设醮修玄,恐怕十倍于正德皇帝事佛。但他忽略了经济账,嘉靖皇帝修玄,即使是十倍不务正业于正德,但从费用说,绝对是节约了的。我怀疑从王府上来的嘉靖皇帝是这么算账的:修仙虽然要花费,但让大臣们写写青词,也是物尽所用,总比赏赐番僧另外开销要划算。正德时,居留在京城的番僧人数已达到万人左右,而且都需内库拔银供养,这是一笔不菲的开销。而且国师、禅师们的酒、肉类饮食补贴,由宫内光禄寺供给,一天至有来领二次三次者(《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这也是道教徒嘉靖皇帝所不能忍的,终于把几朝积下来的大麻烦,用一句“不喜欢”给结束了。
嘉靖皇帝去了眼前烦,把京城中的番僧驱逐了,大慈恩寺拆了,但朝贡番僧人数,并没有如预算减少。嘉靖初,曾把番僧入贡人数限在三百人内(《大明会典》卷一百八),照《实录》的记载来看,并未能执行规定,还是年年超额,有多达千余人入贡的。往往是对四川地面的起送官、巡抚等,进行申斥批评了事。也有查到地方官贪污受贿,多卖名额的,但也未见严厉处罚,因为事涉“怀柔远人”,上下都有点含糊其辞应对。嘉靖十年,又改为六百人。当时加上其他女直等部,“例应一岁入贡者不下五千四百人,赏赐彩币不下五千五百余匹”。(《明世宗实录》嘉靖六年十月)
道教徒嘉靖皇帝治下,番僧入贡一项开支如此可观,到佛教徒万历皇帝时期,甚至又请番僧入宫内诵经了,但番僧入贡人数却大大减少了。这要得益于张居正的政策,如他写信给甘肃巡抚面授机宜,告知处理番僧入贡的意见,一是不鼓励,请他们不要来了。二是假如非要来,人数不可参照其他入贡的部族。三是规定时间、地点,由陕西境入,冬来春回。四是内库赏赐,都要由张居正本人审核过目(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答甘肃巡抚侯掖川》)。又多次告知宣大巡抚郑洛,让其坚持番僧本没有入贡的先例,给赏只是特恩的原则(《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三)。张居正是能臣,能定策略,又有一批忠心(臣服)于他的臣下,把贯彻他的“旨意”作为第一要务,反倒是番僧,还要通过顺义王向张居正求请,才得到入贡的机会。
朝贡体系中,番僧一项受批评最多,引起反感最强烈,耗费巨大是一个原因,而番僧居留期间的不法行为,是更重要的原因。正统年间姚夔奏章“礼部为陈言兴利除害事”中提到番僧入贡时的诸多不法:挟带私货,劳扰驿递。成群结党,行凶打人。勒要财物,强淫妇女等等(姚夔《姚文敏公遗稿》卷十)。而且赏赐之丰厚,与国内民生凋弊的惨象对比,更触目惊心。如成化二年四月,巡按河南监察御史娄芳陈言事宜云:“如今淮、徐、河南等处人民鬻男卖女者,沿途成群,价直贱甚。甚至夷人番僧亦行收买。乞出内库银帛赍付巡视都御史设法收赎,及禁约边关,不许番僧人等夹带中国人口出境,仍给本价,赎还原籍。”(《明宪宗实录》)遇到灾年,老百姓卖儿卖女,番僧反而用朝廷赏赐的银两,沿途买入人口,带出边境(为奴),这在儒家官员眼中,实在有失国格体统,只好再动用内库银两买回,庶几不失面子。又嘉靖三年四月,当年番僧入贡总人数1423人,其中167人进京,1256人留边(就是少数代表进京,领很多人的赏赐)。同月,户部上奏,安徽、江苏地面的水旱灾荒,已造成“垂死极贫者四十五万,以疫之死者十之二三”(《明世宗实录》)。而番僧赏赐的人均额度很高,参照万历年间来看,人均4两至12两不等(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九),即七品至四品官年俸间的波动均值。这种对比,拿着俸禄的官员也很难不愤怒。
从历朝奏疏来看,有很多反对番僧入贡的大臣及章奏,除了张居正等少数几位能臣,大多也只能提供些批评意见,而提不了“建设性”意见的。皇帝们也远没有洋洋自得于“天朝”的欣喜,反而是焦头烂额,无计可施。但也只能闭目塞听,无视入不敷出,民不聊生的现实,让这一政策懒惰地随着王朝苟安下去。

![2020年迪拜世博会韩国馆 参观者也是设计者[图文] 2020年迪拜世博会韩国馆 参观者也是设计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eygug34r0y.webp)
![南京六百年明城墙试跑黄包车引争议[图文] 南京六百年明城墙试跑黄包车引争议[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q3ui14vqqr.webp)
![10位自杀画家的遗作 你能看出端倪吗[图文] 10位自杀画家的遗作 你能看出端倪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zjq1akh2jc.webp)
![“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图文] “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iqsvzgwnh1.webp)
![债王前妻用自己临摹的赝品替换毕加索名画[图文] 债王前妻用自己临摹的赝品替换毕加索名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dl0pa0te4q.webp)
![抽得如此之像,以至于死活看不懂![图文] 抽得如此之像,以至于死活看不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51z2lpvocj.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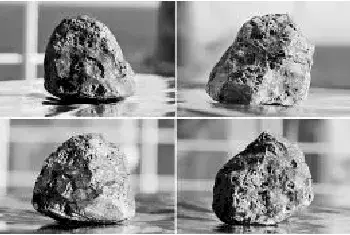
![绚烂的色彩 梦幻的旅程[图文] 绚烂的色彩 梦幻的旅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ut05qhfuty.webp)
![电缆公司买壶送股东并承诺一年回购[图文] 电缆公司买壶送股东并承诺一年回购[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t1phgxatf1.webp)
![咸丰重宝背满文宝浙当头十 当头百大钱鉴赏[图文] 咸丰重宝背满文宝浙当头十 当头百大钱鉴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nyffsmrvpd.webp)
![艺术家用3万伏高压 “捕捉”到你灵魂的模样[图文] 艺术家用3万伏高压 “捕捉”到你灵魂的模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usy2jktpfm.webp)
![公园57万元挂牌转让花梨木引热议[图文] 公园57万元挂牌转让花梨木引热议[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wxe3k2jphd.webp)
![保安抄书练书法11年写500万字 书法本摞起高1.5米[图文] 保安抄书练书法11年写500万字 书法本摞起高1.5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m2pxdh3ujd.webp)
![从西周玉鱼略考看中国玉文化[图文] 从西周玉鱼略考看中国玉文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z1ddnp4eky.webp)
![熊猫金币沉的越久价值越高[图文] 熊猫金币沉的越久价值越高[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nk3xzrnibm.webp)
![Lady Gaga被比作美国的毕加索[图文] Lady Gaga被比作美国的毕加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35x205ox5r.webp)
![向京:我是丈夫瞿广慈的铁杆粉丝[图文] 向京:我是丈夫瞿广慈的铁杆粉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uvifuf4jgo.webp)
![美一女子攒16400件高跟鞋造型饰品[图文] 美一女子攒16400件高跟鞋造型饰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yfvujfsfe5.webp)
![赵薇微博发油画作品 画内女子温婉恬静[图文] 赵薇微博发油画作品 画内女子温婉恬静[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ostx2c3f3x.webp)
![藏家青睐脸谱艺术品[图文] 藏家青睐脸谱艺术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5byiadcszj.webp)
![可乐男15年收藏千个可乐瓶不少是孤品[图文] 可乐男15年收藏千个可乐瓶不少是孤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1s3kad5xkf.webp)
![那些动漫里拟真的场景[图文] 那些动漫里拟真的场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iz0x5i3low.webp)
![趣闻:我国第一张全裸人体艺术照[图文] 趣闻:我国第一张全裸人体艺术照[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yn1vuzcjes.webp)
![两幅黄庭坚:真假美猴王[图文] 两幅黄庭坚:真假美猴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bjyvnm4zgl.webp)
![广西一下岗工人自创稻杆画 将“稻草变金条”[图文] 广西一下岗工人自创稻杆画 将“稻草变金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zuf40qavxl.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