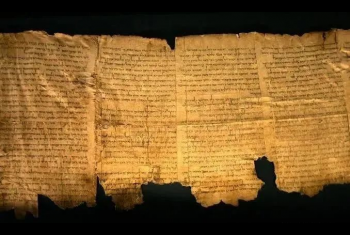在这五幅浮雕中,我们看到了几近相同的图画。于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便产生了,这就是在这几位国王统治的各不相同的历史时期,果真发生了如此相似的历史事件吗?令人愈加注目的是,在从第五王朝到第二十五王朝的大约两千年的时间跨度里,利比亚国王的妻儿居然拥有相同的名字,而且每个人都有两个儿子,这难道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综观埃及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重复先王历史功绩的事情在王室艺术作品中屡见不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内容重复的王室艺术作品呢?我们已经知道,古代埃及人没有历史这一概念,在古代埃及语中也没有“历史”这一单词,但是古代埃及人也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记录那些对于他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于是他们便采取了对某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重复再现的特殊方式,来记录和纪念这一事件(注:W.A.Fairservis,"A Revised View of the Narmer Palette",in JARCE,Vol.28,1991;D.O'Connor,A Short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ittsburgh,1990.)。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五幅浮雕是对比它们的年代更久远的某一历史事件的再现,以使其流芳百世。
那么,除了以上五幅浮雕外,还存在比它们的年代更为久远而又主题相似的文物吗?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把目光重新转移到纳尔迈调色板上。在本文的开篇我们就指出,传统上人们把这块调色板视为纳尔迈统治下的上埃及征服下埃及进而统一埃及的有力证据。这个结论的主要理由是,埃及国王头戴红王冠和白王冠的两个不同形象同时出现于这块调色板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头戴白王冠的统治者正在杀戮被认为是下埃及国王的人(注:Edwar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1,Part,Ⅱ,Cambridge,1971,pp.6-7;W.B.Emery,Archaic Egypt, 1961,pp.43-45;A.Gardiner,Egypt of the Pharaohs,1961,pp.403-404;Hallo and Simpson,Ancient Near East, 1971,p.204;Pritchard,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Picture,1954,p.283,296;M.A.Murry,The Splender That was Egypt,London,1964,p.13;W.S.Smith,Art and Architecture,Baltimore,1965,pp.17-18;C.Aldred,Egyptian Art in the Days of the Pharaohs,3100-320 B.C.,London,1980,pp.34-35.)。
然而,现今学者对这种理解的可信度提出质疑。事实上,我们惟一可以确信的事实只有一个,那便是被杀戮者的名字瓦沙。调色板上还刻有一行文字,即“荷鲁斯战胜了沼泽之国”,在此“沼泽之国”就是指瓦沙统治下的国家。在调色板上瓦沙与其他被征服者一样,都是几乎全身赤裸地跪倒在地。这种描绘并不代表种族歧视,它只表现了被征服者那种卑微凄惨的境地。
从外形上看,这些被征服者既像埃及人又像外族人,但是我们却有一些间接的证据把他们同利比亚联系起来,或直接把他们同利比亚人等同起来。在纳尔迈调色板正面部分被毁的墙体中刻有一个象形文字符号(附图);在攻城调色板(Siege Palette)所描绘的城防工事中也刻有一个与之类似的象形文字符号(附图);另外在攻城调色板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译为“利比亚”的象形文字符号(附图)(注:Gardiner,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ca,Vol.I,Oxford,1947,p.119.)。公牛调色板(Bull Palette)、盖博尔·埃拉·阿拉克(Gebel el Araq)刀柄和战场调色板(Battlefield Palette)所描绘的敌人,同纳尔迈调色板上的敌人一样,除了腰间系了一条短小的围裙外全身几乎赤裸(注:A.R.Schulman,"Narmer and the Unification:A Revisionist View",in Bulletin of Egyptology Study (以下略为BES),Vol.11,1991/1992,pp.79-105.),而在文明的早期,这种特殊的服装只限于利比亚人。结合已经提及的内容相似的五幅浮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包括纳尔迈调色板在内的所有前王朝的考古资料所表现的系短裙的敌人,就是外国人,确切说是利比亚人。如果笔者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对纳尔迈调色板将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纳尔迈调色板主要揭示的历史事实是,瓦沙死于纳尔迈之手,而非“征服”和“统一”,实际上它是“埃及国王杀戮利比亚统治者家庭”的更早版本,直到第五王朝的萨胡拉统治时期,这一版本才被完全确定下来。与其他几个版本相比,纳尔迈调色板缺少关于敌酋之妻和牲畜战利品的描绘,但是在其反面底部的两个试图逃跑的男人,应该就是后来版本上的敌酋之二子。如果纳尔迈调色板的确是“利比亚统治者家庭”的早期版本,那么它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原始本还是对一个更早事件的再现?由于前王朝时期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大多把利比亚人描绘成敌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导致“统一”的“征服”的确发生过,发生的时间应该在纳尔迈统治之前的前王朝的某一个王统治时期。换言之,打败和杀戮名字为瓦沙的利比亚统治者和征服他的国家是一项如此伟大的功绩,以至于成为埃及王权神话的一部分(注:W.A.Fairservis,"A Revised View of the Narmer Palette",in JARCE,Vol.28, 1991, pp.179-180;D.O'Connor,A Short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ittsburgh,1980,p.185.)。因此“征服”和“统一”的对象应该是利比亚。众所周知,现代利比亚位于埃及的西部,而纳尔迈调色板所展示的被征服之敌却来自于埃及的北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前王朝时期利比亚的地理范围与现代利比亚的地理范围存在着差异。其证据如下:第一,在埃及语中含义为利比亚国和利比亚人的单词有这么几个:“泰赫努(Tjehenu)”,意为“橄榄油之国”(注:A.R.Schulman,"Narmer and the Unification:A Revisionist View",in BES,Vol.11,1991/1992,pp.116-119, no.A 239.),“泰姆胡(Tiemchu)”意为“北方之国”,“亚麻布之国”(注:A.R.Schulman,"Narmer and the Unification: A Revisionist View",in BES,Vol.11,1991/1992,pp.114-116,no.A 238.);在攻城调色板的另一面刻有意为利比亚的象形文字符号(R),这个符号的原意是橄榄树(注:A.R.Schulman,"Narmer and the Unification:A Revisionist View", in BES,Vol.12,1991/1992,p.117.),这块调色板的其他地方还刻有牛群、毛驴和山羊等从敌城中掠获的战利品,也就是说,它们是利比亚人的牛群、树木和城市(注:E.Oren and I .Gilead,"Chalcolithic Sites in Northeastern Sinai",in Tel Aviv,Vol.12.1985,pp.28-29;J.M.Weinstein,"The Significance of Tel Areini for Egyptian-Palestinian Rel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ronze Age",in BASOR,Vol.256,1984,pp.61-68.)。第二,从外貌上看,这些资料所表现的敌人很像埃及人,但是他们却穿着利比亚人特有的短裙,所以他们更像利比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