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自薿 秦川社火 布面油画 120×110cm 1994年

张自薿
拜访张自薿老师,正是杭州春夏之交的好时节,繁花烂漫,草木正兴。林立高楼间的一处静室,就是她生活、作画的场所。干净、通透,正像她本人,年过八旬的她,方一开门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问候。齐耳根的短发,利落地别在耳后,浅灰蓝的宽松大外套,工作室窗明几净,几片大落地窗接纳了整个春天的美好。墙上、画架上,一大朵一大朵盛开的花,芭蕉、兰花、向日葵……那些叫得出叫不出名字的花朵一股脑儿从油画布上蓬勃而出,优雅生长,生机勃勃地各自悠扬。即使是干了的花朵,颜色已经枯黄,也被定格在了生命盛开的最美姿态——她把它制成了小小的标本,保存在墙壁的一角。她说,“年纪大了,也走不了很远,你看窗外、小区里的花花草草多好看,我就开始研究,仔细地去看,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都有自己可爱的地方。”就这样,一草一木,在她的手里有了生命的可爱和尊严。
3个女人,年龄差了两代人,却用一个下午翻开了大半个世纪的柔软时光——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云淡风轻的讲述中,串联起的是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女画家一生的春华秋实。
学生时代 蔓蔓日茂
1935年春,张自薿出生在江西萍乡市。家中7个孩子,她是老幺。她笑说,“家里的男孩子取名都是金字旁,女孩子都是草字头,是不是有些重男轻女呀。”这草木,恐怕有着金石无法比拟的柔韧与坚忍。父母没有过多的时间关注每个孩子,就放手让他们自由成长,“草字头”的自薿,就像春花春草一样自顾自地“野蛮生长”。
“初中时候,我很崇拜我们的美术老师。她给我们介绍达·芬奇、拉斐尔的素描,让我看到与火柴盒上画得不一样的东西,感觉到艺术是很神圣的。这让我的起步能够高一些。”回到家,她就把茶几斜靠起来,模仿画板画架。这位女老师,打开了关于艺术的第一扇窗。
1950年春,高二的张自薿只身北上,投奔身在北京的哥哥。正值中央美术学院春季班招生,“报名的人很多,考试要求每个人带一面镜子,画自画像。发给大家一盒木炭条、一块馒头。当时不知道馒头干嘛用的,以为给我们吃的,后来才知道是用来擦木炭条的。就这样稀里糊涂考进了美院,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画是很可笑的,整张纸就是一张大脸。”100多名新生,10几个女生,张自薿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徐悲鸿、韦启美、吴作人、董希文……先生们的才华横溢、宽厚大气、平等无私深深影响了每一个学生。“你们班都在拼命往前走,你简直在跑步嘛。”韦启美先生的鼓励让张自薿更加勤奋;“我的第一张油画还没你画的好呢”,吴作人先生的鼓励让她拾起油画的信心。
她说,“留校当研究生的时候,每周六吴作人先生家里都要请模特儿,他也邀请我们一起画。先生们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们都很平等,教育我们人不要分等级;画画也是,向好的学,相互学习。美院学习的那几年收获很大,最主要的是奠定了好的品质。”
收获爱情 连理相依
校园时光不仅收获了眼界学识,也收获了纯真爱情——她与同年级的蔡亮走在了一起。大学本科、读研深造、留校任教、郎才女貌,原本是一条多么让人羡慕的未来路途。然而毕业后蔡亮受到政治批判,分配到西北工作。20岁出头的张自薿只留下一句“蔡亮是个好人”,就毅然放掉了那些别人的“羡慕”。没有婚礼、没有浪漫,登记结婚,两个年轻人从此成了彼此的依靠,手里攥着两张火车票,踏上了西行的火车,等待他们的是黄土高原的苍茫未知。
我们感叹,那时的生活很苦吧?“我真没觉得很苦。我从小是城市长大的,去了农村反倒觉得特新奇,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开阔世界。大概因为年轻,一天劳动完了有饭吃、有个地方睡觉就很满足。”他们被分配到省群众艺术馆工作,下乡创作、搞美术班、去发现民间的优秀艺术品、推广群众艺术,与当地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春天插秧秋割麦,这是新的体验;遇上跳蚤、蚂蟥也不怕,原来老乡们有好办法解决;走夜路遇上狼,老乡家里遇到猎狗,都是惊心动魄的回忆;后来文革期间下放到南泥湾劳动,养鸡养鸭,“他们叫我‘鸡司令’,小鸡小鸭一看到我就围上来,小动物也是有感情的”。那么正能量,她总是能找到生活里的阳光,因为她爱着脚下的土地。老乡们健康、阳刚;小娃娃们精神、开朗。这些美好的形象和记忆成了《南泥湾》(1961年)里的劳动号子;成了《铜墙铁壁》(1972年)里小羊倌的阳光朝气、关中汉子的爽朗雄健;成了《延安儿女怀念周总理》(1977年)的悲痛深情;成了《安塞腰鼓》(1984年)的锣鼓喧天……成了黄土地的厚重,成了万里山河的磅礴。
蔡亮与张自薿,这一对在苦难中走来的艺术伉俪,在那个动荡年代,留下了关于陕北红色摇篮里最为动人的绘画,不光在生活上相互扶持,也在艺术创作、精神上相互启迪。“我们的合作过程没有太大的矛盾。我跟蔡亮有一定分工,他擅长构图,造型能力强;我给他出主意,画小构图一块比较。如果他画的形象不满意,我就直接上去改;有时候我画不下去,他就接着画,相互都没有意见。那时候就想通过画画把自己的理想、兴趣、对美的感受表达出来,很简单。”因为彼此风格同步,追求相近,他们共同创作了太多的经典。
她说,“画画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传达出自己想说的话,如果别人能够理解,就产生了共鸣。比如《铜墙铁壁》里拿着羊鞭子的小羊倌,当时很多人喜欢,觉得他很可爱。我就很开心,我也是因为他可爱才想画他。另一种情况,是我画想表达的东西,观者从自身的感觉、经历出发,产生共鸣。比如我画过一位陕北的老汉,系里的另一个老师看了说想起自己的爷爷,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画的老汉,他的淳朴能让观者想起自己的亲人。我觉得这种共鸣对画家来说是最大的奖励。”
同窗师长 十步芳草
1982年,张自薿与爱人蔡亮先生一同调到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张先生安静少语,务实而坦诚,大家都十分喜欢这对从黄土高原远来的著名画家”,这是许江院长在2015年《艺心如噎——写给张自薿先生画展》一文中叙述的。从西北来到江南,那份对生活的爱,化成了对学生的情。“教学生,我觉得重要的是,根据每个人特色去教,不能有模子。后来西方的一些文化进来,学生中有各种思考,作为老师,我们应该宽容。”一次教学检查,有位学生画的肖像加入了自己的思考,有些“歪歪扭扭”,检查的老师说要拍照当反面案例,张自薿就劝说,这画还没画完,等画完有问题再拍,“同学的一些想法要尽量去保护,要有独立的想法,不能扼杀在摇篮里”。她回忆蔡亮先生有句经典的话,当时蔡先生因事一周没去教室,等周一回来,一看学生们的作业:“哎呀!我没来,你们画的更好了。”造型不准?但是用笔很结实;构图不好?但是有感情;立体感不强?就去学平面……她总是能发现每个年轻人心中萌芽的独特之美,宽容地保护,让学生们走出了自己的路途,桃李天下。
她说:“能够真正触动观者的画,很不容易,哪怕画的手很生、很粗糙,但还是能感受到里面的情绪,这可能就是天赋。”她说:“小事不要太计较,把住大局原则,给了自由发挥得更好。”
这种“把大局的自由”在家庭生活中也很明显,她说作为长辈,自己“在家里权威不高,对孩子们也都是放手”。在客厅的墙上,挂着她与蔡亮先生的合影、家族的合照、孙子和外孙小时候的画作……那些时光的小点滴,被她视若珍宝,那份亲情,春风化雨。她的宽容、她的“放手”也让家里的孩子们自由自在、海阔天空。孩子们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人生,从事不同的行业,走向八方四面。
“来,手机扫一扫,我们加个好友”自薿先生笑着拿出手机,打字、语音不在话下,发个朋友圈是生活的分享。十几年前外孙小学一年级时,她跟着外孙学会了拼音;她说现在正捣鼓电视机顶盒,要自己放节目看。
遇事宽容一点,世界大得很,要有好奇心。退休后的她,研究起花花草草,即使在一室一园中,她也能用好奇心,去发现这一花一草中的大世界。是啊,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世界就像花开,心花若怒放,开到荼靡又何妨。

![翰墨丹青:品读孙阳老师的国画艺术[图文] 翰墨丹青:品读孙阳老师的国画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ijnrrl0hmt.webp)
![手稿是不是书法 名人手札拍卖的法规困局[图文] 手稿是不是书法 名人手札拍卖的法规困局[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olkbsk1v4m.webp)
![2022年中国最具影响力人物专题报道:方坤[图文] 2022年中国最具影响力人物专题报道:方坤[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fes1edi3d2.webp)
![不再避讳商业诉求 全球化时代的新艺术很亲民[图文] 不再避讳商业诉求 全球化时代的新艺术很亲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ujh1r4ozd1.webp)
![“变装秀”的乾隆仿古行乐图[图文] “变装秀”的乾隆仿古行乐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tzp5j0c1lj.webp)
![玛丽安娜谈莫奈日出·印象:六年前不确定日出日落[图文] 玛丽安娜谈莫奈日出·印象:六年前不确定日出日落[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53qnzm53tz.webp)
![台湾插画家郑晓嵘:清澈的迷幻异想[图文] 台湾插画家郑晓嵘:清澈的迷幻异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ptlgiun4he.webp)
![第十一届“鸿儒杯”海峡两岸书画大赛铜奖范德宏作品赏析[图文] 第十一届“鸿儒杯”海峡两岸书画大赛铜奖范德宏作品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g3wtlezitk.webp)
![李艾:爱笑女人的优雅情怀[图文] 李艾:爱笑女人的优雅情怀[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zruf2nsdz4.webp)
![陆一水的山水世界[图文] 陆一水的山水世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ujzlkln2l0.webp)
![赵连志画胡杨的三个特质[图文] 赵连志画胡杨的三个特质[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f3u522ajay.webp)
![拥有善本书就像坐拥繁华路段地产一样[图文] 拥有善本书就像坐拥繁华路段地产一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ehtgkwsbso.webp)
![米巧铭油画个展《无相》在泰国曼谷成功举办 [图文] 米巧铭油画个展《无相》在泰国曼谷成功举办 [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lyvmb5xd5o.webp)
![文玩核桃:奢侈的雅兴[图文] 文玩核桃:奢侈的雅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r05do1kje1.webp)
![2023年度最具收藏价值书画家——杨小灵[图文] 2023年度最具收藏价值书画家——杨小灵[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ctf2vb3npv.webp)
![花鸟情淋漓 丹青意天成[图文] 花鸟情淋漓 丹青意天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ychfvvo4qr.webp)
![亨利·摩尔:纯粹与自足,雕塑拥有自己的生命[图文] 亨利·摩尔:纯粹与自足,雕塑拥有自己的生命[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sclrrfxcpd.webp)
![荣宝斋上海拍品赏析:林风眠《双鹭》[图文] 荣宝斋上海拍品赏析:林风眠《双鹭》[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ywmjiqziov.webp)
![冯 远 “国博百年·中国雕塑百年作品展”述评[图文] 冯 远 “国博百年·中国雕塑百年作品展”述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0snlujumjv.webp)
![上海一年300多场艺术特展背后的秘密[图文] 上海一年300多场艺术特展背后的秘密[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g5114x0x5w.webp)
![传艺术之大美——特邀著名书画家张春青[图文] 传艺术之大美——特邀著名书画家张春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rmpgnrsnvp.webp)
![观物取象--翁道胜绘画艺术创作方式研究[图文] 观物取象--翁道胜绘画艺术创作方式研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wxvd1s1cyb.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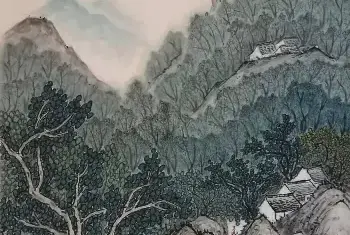
![我武惟扬 神骏赞歌·赵文元研究二[图文] 我武惟扬 神骏赞歌·赵文元研究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xfa1kb5amb.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