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每年一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前两次会议的主题分别是宋代绘画研究、世界早期文明中绘画的起源与初期发展。今年研讨会名称为“中国收藏与鉴定史”,这源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过程中的思考。
 乔松平远图轴
乔松平远图轴
由浙江大学主办,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承办,《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辑委员会、浙江大学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筹)协办的“中国收藏与鉴定史国际研讨会”上周在浙大举办,邀请到17位来自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专家以及浙江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布朗大学和欧洲的学者各自作了专题报告并进行了深入讨论,共计1000余人赴现场聆听。
自2014年以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每年一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前两次会议的主题分别是宋代绘画研究、世界早期文明中绘画的起源与初期发展。
其中2014年的宋画会议、本次的中国收藏与鉴定史会议,都是由《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编纂而产生的话题,并且都获得了艺术史界学者与公众的热情响应,体现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对推动当代学术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大系所收资料的陆续公布,未来将有更多与大系相关的会议。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缪哲教授表示,将研讨会的名称定为“中国收藏与鉴定史”是源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过程中的思考。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刊登研讨会中几位专家学者发言报告的内容摘要,以了解他们对于中国收藏与鉴定史这个大主题下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我对日本藏传李成《乔松平远》及传李唐《山水》双幅之私见
傅申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流传至日本的传宋代李成《乔松平远图轴》(澄怀堂美术馆藏)及传为宋代李唐《山水》双幅(高桐院藏),向为西方乃至中国的美术史学者所关注。经本人考证“李郭派”中属于“寒林平远图”风格的几件作品之后,通过比较《乔松平远》和《早春图轴》中相似元素的细部,如小枯枝、点数叶等,再比较郭熙在其他博物馆所藏传世绘画的轮廓线条、山石造型等,确认传李成《乔松平远图轴》与《早春图轴》同为郭熙真迹;而高桐院所藏传李唐(款)《山水》对幅,早期与一张观音图被作为整体保存,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吴道子所绘画。岛田修二郎于1952年发现在树叶处有“李唐画”的款,但画款下隐约还有被洗去的老款印迹。1972年,艺术史学者班宗华提出,将山水双幅左右对调拼合,其实原为一个整体。我不这么认为,虽然山石结合无缝,但树石处却明显有异。另外,这幅《山水双幅》中树枝处的飞白画法在12世纪初是非常罕见的,反而在宋末元初的衣褶或山水中有运用,加之与两幅画一同流传的观音图被日本学者定年在元代。因此依据绘画的时代风格及技法、质地、款识,发现与李唐的基准作品《万壑松风图轴》有明显差异,并推测该画的创作年代不但晚于李唐,甚至会晚至南宋末甚至元初。
宋代金石收藏与研究起源
孟絜予(Jeffrey Moser) 布朗大学
清代考证学家阐述金石学的历史时,将欧阳修的《集古录》及赵明诚的《金石录》视为其学术源头,并以清人对于金石学的认知去理解宋人的研究。现代学术界大体上继承了清人对此学科的界定。若是我们撇去清代金石学的脉络,将宋代金石着录视为独立的文本,重新阅读欧阳修、赵明诚的着作,将会发现一些长久以来被忽略的面向。
欧阳修与赵明诚看似收藏了类似的拓本并以相近的格式着录,但细读其着录的内容,便会发现两人对于金石拓本的本质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欧阳修对于金石拓本采取一种视觉性的关注模式。他将所收藏的拓本视为物件,关心拓本如何记录碑石的质地、刻文的磨损以及书法的质量。对他来说,无论是青铜器、石碑、刻帖或拓片,物件本身是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而金石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物质痕迹如何承载历史并影响我们对于过去的认知。赵明诚的关注则不同。他将拓本视为文本,只关心拓本所记载的内容。对他来说金石的价值在于提供较可靠的历史材料,而刻工、拓工、书法的质量则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赵明诚的《金石录》经常引用欧阳修的《集古录》,并继承了《集古录》的格式。若是我们通过《金石录》去理解欧阳修,自然容易误解两人的金石研究是一致的。
自宋之后赵明诚的《金石录》被视为将《集古录》发扬光大的着作,并成为清代金石学依据的主要渊源。赵明诚只在乎文本而不讲究拓本的物质性,认为无论拓本质量、版本如何,都有文本价值。因此人人都可以研究金石,家家都可以收藏拓本。若是依照欧阳修对于物质性及视觉性的重视,则拓片本本皆不同,必须看到、摸到好的版本才有意义。这样一来进入门槛较高,拓本收藏便很难流行起来。因此可说,赵明诚重文本、轻拓本的视角促成了金石拓本的收藏风气。但也正因为清代金石学是建构于赵明诚对于欧阳修的理解之上,欧阳修对金石材料物质性的重视被忽略,最终造成了后人对于宋代金石学只注重文本的误解。
一个肆无忌惮的收藏家与两个改动的董其昌印章
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
自古以来,有很多例子显示,一个收藏家为了抬高他藏品的身价会用各种形式作假,以使它看起来更古旧,更稀有,或更有名。但是在一个艺术史年鉴里绝无仅有的例子中,有一个收藏家恰恰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他故意选择了一件真迹,并且将它改头换面以使人们怀疑它的真实性。
根据我对明末赵左的《枕石漱流图》的研究,有两方董其昌的鉴藏印引起了我的兴趣,并认为是有人故意将两方董其昌的真印改为了假印,其中一方从“玄赏斋”改为“宝鼎斋”,另一方从“董氏玄宰”改为“董氏思白”,这两处改动十分巧妙,都用了董其昌有可能使用但事实上从未用过的印章。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贩画者为了将这件真迹倒卖出中国而故意作假,以方便它通过海关的审查。
从《万岁通天帖》管窥
唐宋皇室女性鉴藏品位与性别文化空间
李慧漱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
书圣王羲之的片纸只字,自古以来为藏家奉为珍宝,可是王羲之的书学启蒙老师卫夫人,其书风究竟如何无迹可循。更甚者,对于王书之搜访、宝爱与宣扬不遗余力的唐太宗,倾王朝之力,将王书尽归内府,更诏令以兰亭为殉,种下千年不解的“兰亭论辩”,蔚为脍炙人口的美谈韵事。反观与唐太宗同时的一代女皇武则天,亦致力于王书之收藏,而且更进一步摩拓、复制、保存与流传;存世书林真品“王氏一门七十人帖”——《唐摩王羲之一门书翰》,因征集、摹拓于武周万岁通天二年,故又名《万岁通天帖》,是为有力的见证。于今,原作淹没不存,王氏一门书迹,幸赖武后懿行得以保存,然而武后的这段鉴藏美行,却鲜被提及。
这种在文化叙述与历史书写上的价值论断与性别落差,也显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书画鉴藏史与论着中。尤其是近年来蔚为风尚的鉴藏史研究学风,从徽宗到乾隆的宫廷收藏活动,以及民间私人的鉴藏大家,都已渐具规模;可是唯独女性的鉴藏活动,除了1980年代傅申先生领军研究的蒙元大长公主之收藏,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近日推出的“公主的雅集”大展之外,想来乏人问津。
从幸存的史料与有限的宝物显示,唐宋之际的皇室女性,如武则天、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以及宋朝的后妃们都已经积极并深入地参与了各种鉴藏活动。我将围绕存世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万岁通天帖》实物,以及促成此双钩廓填摹本的艺术推手武则天,并其周遭皇室女性,管窥唐朝皇室女性之鉴藏取向与性别文化空间。其中尤其要强调的是唐朝皇室女性在中国艺术与文化传承中,自有其特殊意义。她们与男性成员之间,亦步亦趋,交融互动之外,甚或扮演着颠覆与超越的关键角色。
从陶瓷谱册看乾隆皇帝的陶瓷收藏与鉴定
余佩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共收藏四本陶瓷图册,它们各有转述题名,分别为《埏埴流光》、《燔功彰色》、《珍陶萃美》和《精陶蕴古》。今日透过《活计档》纪事和《陈设档》登录的清单,而得以逐一追溯出乾隆皇帝在不同时间降旨绘制和加以组合的经过。
其中绘制于乾隆二十至二十一年之间的《埏埴流光》册是其中最早完成的范例。其中收录有十件瓷器,分别为两件汝窑、两件南宋官窑、两件哥窑、两件定窑、一件宣德红釉高足碗、一件成化官窑。其绘制形式基本为:图片、品名、乾隆闲章以及藏品说明。藏品说明又包括器物尺寸、前人品评以及物主的观感。其中形式与前人品评很多都参照《遵生八笺》中的记载,但亦流露出对于图册中的器物的帝王专属和作为物主的特性。不论是想要怡情还是建构知识体系,这本图册仅仅是乾隆想要构建清宫收藏的一个例子。以后还要关注图册完成后所放置的空间位置,才能进一步反映出他这样做的目的。
信息、票号、运输:晚清收藏的信息元素
白谦慎 浙江大学
异地交易现在可以迅速完成,然而在晚清官员收藏中,私人收藏家如何获得异地古董的信息?在成交后如何支付货款?付款后又如何取得所购古董?为官者在外履任时,如何将藏品带到任官之地?这些问题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收藏活动的规模。我将以清末吴大澂为例,从信息、票号和运输三个方面来研究晚清收藏中的异地交易。
吴大澂于1873-1876年任陕甘学政,其间广收文物。离开后,他依然和陕西友人和文物商人保持密切关系。在给苏州文物上徐熙的一封信中显示就是托他买文物,也体现出当时收藏者之间的竞争激烈,信息的独有性非常重要。虽然晚清已经有了电报,但是异地信息的获得依然通过信件传递。然而,不同于晚明官员主要通过友人带信,晚清官员可以通过官方的邮寄系统来传递自己的私信,传递速度也进一步提升。
另外,当时各地使用银两的标准不同,即便在同一地区,也未必通用统一的银重和成色标准。这对于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行会带来极大的不便。银行和钱庄对于各地城市之间不同的银价标准必须了如指掌,他们在两地之间进行业务上的汇票往来或者现银交易时,都要为自己留出充分的余地。
最后,运输问题也是官员异地收藏要面临的问题。在清代,官员不仅要到异地任职,还经常轮换。吴大澂在他每一个担任的职位上都没有超过三年,这些藏品该怎么办?事实上吴大澂在任官期间,视任期长短、路途的远近、水路还是陆路,来决定带多少和什么样的艺术品。比如在1886年去吉林时,因为走的是陆路,任期较短,吴大澂仅仅带了些图书和拓片,而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则放在天津。
可以说,这种网络使得晚清官员学者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他们的收藏活动,而和他们收藏活动相关的学术活动,也体现了一种新的规模。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由陈诗悦根据大会发言及摘要整理。感谢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提供演讲摘要。)

![浮世绘为什么这么火?[图文] 浮世绘为什么这么火?[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jmb2ba3los.webp)
![海昏侯文物展启示录:先辈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图文] 海昏侯文物展启示录:先辈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3frqlyvgvh.webp)
![空谷长钟——当代水墨之李纲个案[图文] 空谷长钟——当代水墨之李纲个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f3vshuoxqz.webp)
![七夕节——中国情人节我们要读的情书故事[图文] 七夕节——中国情人节我们要读的情书故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d10iboc51j.webp)
![乾隆官窑青花盘赏析[图文] 乾隆官窑青花盘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cy3wdnab5c.webp)
![惊艳卢浮宫的创作才子李丝云[图文] 惊艳卢浮宫的创作才子李丝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uw2iotzrte.webp)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图文]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mt3m4oyjzh.webp)
![翟杰辉 助力互联网+中国画 创新发展[图文] 翟杰辉 助力互联网+中国画 创新发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y5jvwvrcaz.webp)
![齐白石诗:自主性灵 托于题画[图文] 齐白石诗:自主性灵 托于题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rjrqjnmqst.webp)
![齐白石的篆刻好在哪[图文] 齐白石的篆刻好在哪[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w2mal23dsl.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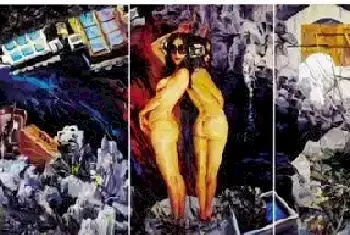
![青年山水画家王健峰作品的艺术审美[图文] 青年山水画家王健峰作品的艺术审美[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4r3lwnbgoo.webp)
![天地玄黄,金墨无界——刘毅臻在古今中西之间构建永恒[图文] 天地玄黄,金墨无界——刘毅臻在古今中西之间构建永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x0edvzveuf.webp)
![李鱓花鸟画《蔷薇花石图轴》赏析[图文] 李鱓花鸟画《蔷薇花石图轴》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yjhhrkiulq.webp)
![多角度解析董元两幅山水画[图文] 多角度解析董元两幅山水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espjbcrc5o.webp)
![内地秋拍挖掘“生货”进行时[图文] 内地秋拍挖掘“生货”进行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i2tccbse3x.webp)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文房四宝及书画[图文]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文房四宝及书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krfppptclw.webp)
![一个自由艺术家 吉尔格楞[图文] 一个自由艺术家 吉尔格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ivr1c0zecb.webp)
![古壁画描绘盛唐贵妇的闲适生活[图文] 古壁画描绘盛唐贵妇的闲适生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waj0iih3ii.webp)
![亨利·摩尔:纯粹与自足,雕塑拥有自己的生命[图文] 亨利·摩尔:纯粹与自足,雕塑拥有自己的生命[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sclrrfxcpd.webp)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李秀峰[图文]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李秀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rbjqpjha5x.webp)
![陈振,以写意笔墨为精神气韵,把热带雨林花鸟描写的生动而传神,自由而生机[图文] 陈振,以写意笔墨为精神气韵,把热带雨林花鸟描写的生动而传神,自由而生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xmokwpvj2l.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