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80年代,即《南京条约》签订后的40年,上海几乎已经变成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事实上,在1870年底之前,至少有20个国家抢滩上海。此时的上海,有来自中外各地的商人及移民, 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复杂而刺激的地方之一。这样一个通过国际贸易而繁荣的城市,不但催生了一批有力的商人中产阶级,而且在另一方面,追求新奇刺激 、特别是跨国情调式的享乐,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众景观。这样的生活,是一种复杂的新旧与中外经验之混合物。如果把任伯年的边塞画放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会惊讶于其之传统。任伯年边塞画的风行,足以提供我们一个理想的个案来了解上海如何作为一个文化的接触带。在这个接触带中,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再造,往往透过跨越或沿袭原有的文化界限来表现。
在我们所谓的边塞画中,任伯年特别喜欢三个主题:“苏武牧羊”“关河一望萧索”及“风尘三侠”。就让我们从款署1880年、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苏武牧羊》开始。关于苏武故事,主要自班固《汉书 ·苏武传》演绎而来。唯对于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此处不再重复。在这幅画中,苏武巨大的身躯由画幅的底部擎天而起,配合其紧握的节杖,形成一向上的力量。其膨胀鼓起的右肩膀,稍稍遮住下巴,显示出一种戏剧性的、由左下到右上的形式。相较于苏武魁梧而令人敬畏的形象,前景的羊群则柔顺地随从苏武的手势,向画面的深处移动。虽然苏武和羊群置身于一个抽象的留白之中,但表现羊群的前缩法,却创造了完美的空间感。任伯年显然非常熟练于操纵透视及观者的观看方式。

任伯年《苏武牧羊》(1880年,故宫博物院藏)
这幅画纵149.5厘米,宽81厘米,虽然不算一张小画,但就中国画而言,也并非一件大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画家如何借由透视、观赏方式及其他的一些细节,如人物宽阔的肩膀以及转折方硬的衣纹线条,赋予苏武一种英雄的感觉。 然而,任伯年描绘的苏武,远比一个单纯的英雄形象要来得复杂。其身躯背对着观者,两眼却转向观者,这不仅是一种动势,也造成一种犹豫的感觉。苏武伸出手臂,将羊群赶向远方,其魁梧的身躯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保护着持拿的节杖。类似的形象同时也可见于任伯年所创作的其他苏武画作。通过同较为传统的苏武形象之比较,我们更容易了解这个特色。
以18世纪扬州画家黄慎描绘的苏武为例,不同于任伯年的苏武略带摇摆而显得有距离感的身体表情,黄慎笔下的苏武嘴巴微张,显得放松而专注。相较于此,任伯年的苏武形象则显得机警,高大的身躯,似乎构成了一道心理上的屏障。这种身体的紧张感与防卫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一则常被传引但出处不详的题款,据说原题于另一幅任伯年《苏武牧羊》上,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些灵感:“置身十里洋场,无异身于异域。”虽然这幅画已经不可考,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问:任伯年是否有可能表达出这样的感叹?
第一,就用语习惯而言,关于租界的俗称,自1843年以来经历过几次变化。早期上海人习惯称其为“夷场”,后来,尽管1858年的中英条约明确规定官方往来文书中,不许出现“夷”字,但“夷场”这样的词汇还是常见于小说笔记、旅游杂记或当时风行的竹枝词中。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十里洋场”这样的词,至少以《申报》为例,已经几乎全面取代“夷场”。所以,就用语而言,虽然我们无法由此确定这则题跋与任伯年的关系,但是至少不能由此就否定其作为19世纪80年代任伯年最喜欢的题材之一的可靠性。

黄慎《苏武牧羊图》(苏州博物馆藏)
第二,就脉络上的推理而言,上海商人暨任伯年的赞助者章敬夫,曾经在向任伯年订制的《五伦图》上作一后记,引述了任伯年对上海社会的感触:“窃有慨今士大夫,用夷变夏,习与俱化,甚至倡平权自由之说,举我中国素重之伦常,不堪为轻薄少年,问是谁之责耶?因是触目感兴。思我中夏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历尧舜三代以来,以导以教,化人以深。何世变日移,滔滔是也。 ”对这样的“滔滔世变”,尤其是外来文化的影响,任伯年显然无可奈何。
虽然,在任伯年的例子中,言说与表现常常充满了矛盾和讽刺,但至少在言说的层面上,任伯年选择了一个极为保守的立场,且在面对上海处处所见的外来势力时,不时反映出其对民族危亡的忧虑。
(本文节选自《跨界的中国美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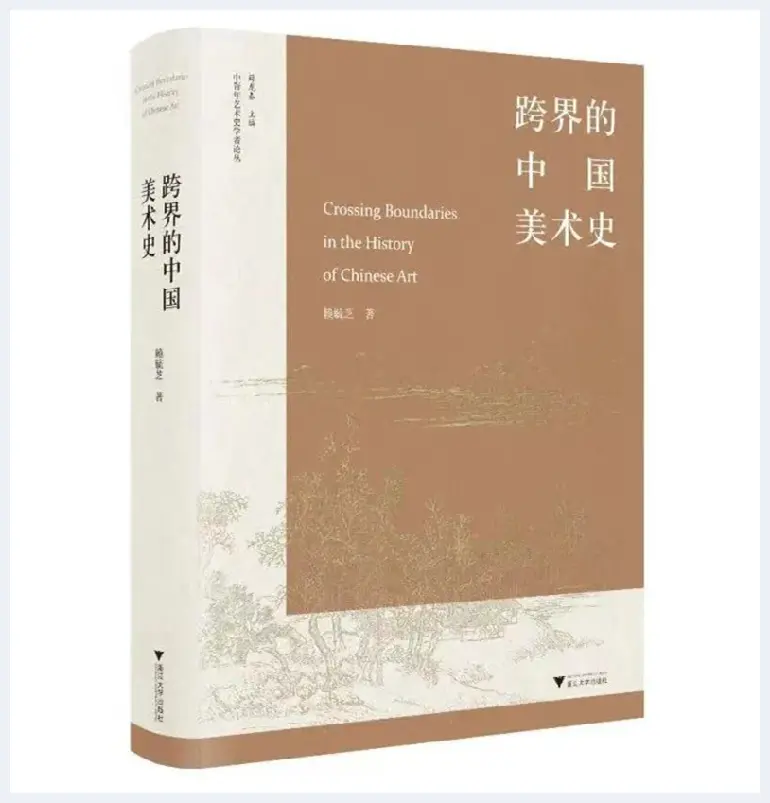
《跨界的中国美术史》
赖毓芝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所关注的重点在于美术史中的中西交流,主要注重其中之图像即视觉文化领域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本书分为三个主题,其一是什么是异域?作者通过对卷轴画、钱币等物质性材料上的异域图像,试图解答当时民众眼中的异域形象。其二是新选择的出现。异域图像的传入,自然刺激了本土的艺术家,并成为他们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其三是图像的全球流动。图像的不断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知识之间的融合,这一变化首先体现于本土图像的变化之中。本书从全球视角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观察美术史的视角。

![敢以豪情写春秋 ——刘宏章先生书法略谈[图文] 敢以豪情写春秋 ——刘宏章先生书法略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5sqkszgeif.webp)
![美神宫主薛林兴倾情央视美女主播[图文] 美神宫主薛林兴倾情央视美女主播[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2jxhqoeeec.webp)
![艺术品收藏首先要懂得鉴赏[图文] 艺术品收藏首先要懂得鉴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wejusjojof.webp)
![天地玄黄,金墨无界——道金平在古今中西之间构建永恒[图文] 天地玄黄,金墨无界——道金平在古今中西之间构建永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tzanla0yep.webp)
![新藏家如何收藏古典绘画作品?[图文] 新藏家如何收藏古典绘画作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rnz1xdarkx.webp)
![收藏故事不可尽信[图文] 收藏故事不可尽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njubglryce.webp)
![当代著名画家卢成之作品欣赏[图文] 当代著名画家卢成之作品欣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whao3auudr.webp)
![在三件拍品中窥探疫情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图文] 在三件拍品中窥探疫情对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pnfdwbtjte.webp)
![艺术史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淘汰赛”[图文] 艺术史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淘汰赛”[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fhd3setuh5.webp)
![植物思维:时间的另类记录模式[图文] 植物思维:时间的另类记录模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nq5dkbjt2o.webp)
![观庞莱臣藏画展梳理山水画发展脉络[图文] 观庞莱臣藏画展梳理山水画发展脉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ifmdesegmg.webp)
![万一股市崩盘 为什么是买艺术品最佳时期[图文] 万一股市崩盘 为什么是买艺术品最佳时期[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xsw4r45x5v.webp)
![宋画之中 领略文人的慢生活[图文] 宋画之中 领略文人的慢生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d5y05f1bsl.webp)
![博物馆“蹭凉”莫忘文明相伴[图文] 博物馆“蹭凉”莫忘文明相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4xjyzbzakz.webp)
![新城公主墓中的《天象图》[图文] 新城公主墓中的《天象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djwxcxl4rs.webp)
![不断崛起的东南亚艺术[图文] 不断崛起的东南亚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vxoc0x51sn.webp)
![冯少协:油画写真千年古镇[图文] 冯少协:油画写真千年古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i0dftsimsn.webp)
![论博物馆创新维护的重要性[图文] 论博物馆创新维护的重要性[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zw4qnhzr14.webp)
![冯 远 “国博百年·中国雕塑百年作品展”述评[图文] 冯 远 “国博百年·中国雕塑百年作品展”述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0snlujumjv.webp)
![彩墨丹青 董春莲老师泼墨作品赏析[图文] 彩墨丹青 董春莲老师泼墨作品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zqjsv5celz.webp)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李秀峰[图文]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李秀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rbjqpjha5x.webp)

![丝绸之路北方行·赵文元研究八[图文] 丝绸之路北方行·赵文元研究八[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r23mjylez2.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