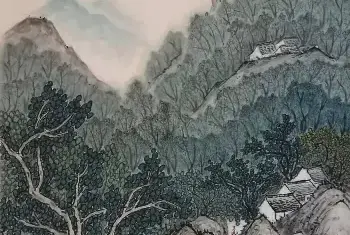1910年前后的珂勒惠支。 图片:H?nse Herrmann, Kollwitz Estate ?K?the Kollwitz Museum K?ln
1910年前后的珂勒惠支。 图片:H?nse Herrmann, Kollwitz Estate ?K?the Kollwitz Museum K?ln
并非有很多艺术家可以在去世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可以引发关于政治的激烈争辩,但德国20世纪早期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1993年,德国时任总理科尔(上个月去世)下令在位于德国柏林交通要道Unter den Linden上由普鲁士建筑师Karl Friedrich Schinkel设计的新岗哨内,安装一尊珂勒惠支大型的宗教主题青铜雕塑《母亲与死去的儿子》(Mother With Her Dead Son)。当时两德统一只有几年,而这个岗哨楼——本来是1930年作为一战纪念碑的建筑,在1960年被东德政府改造成了法西斯及军国主义受害者纪念碑——被重新命名为了德国联邦共和国战争及独裁受害者中央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很快就成为了争议的焦点,而作品的选择无疑是原因之一。
令人吃惊的是,科尔通过选择了珂勒惠支作品,成功地用左派的标志性人物来对其发出了挑战。几十年来,珂勒惠支创作于1920年代的“No More War!“(不要战争)海报就经常出现在西德发生的和平抗议中。在东德,这位艺术家(在二战结束前不久的1945年4月去世)则经常被政治力量以民族英雄的形象歌颂——对于她日记内容经常在西德被引用依然不屈不饶,仍在日记中争取艺术独立与政治之外的自由。
 珂勒惠支,《女人与死去的孩子》,1903。 图片:?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urtesy Ikon Gallery
珂勒惠支,《女人与死去的孩子》,1903。 图片:?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urtesy Ikon Gallery
珂勒惠支1867年7月8日出生于哥尼斯堡(现加里宁格勒),在女性不被艺术学院接纳的时代就开始学习艺术,在柏林及慕尼黑的女性艺术家学校学习。1898年,她因为“纺织工起义“组画一举成名。这组纸上作品六张一套,以Gerhart Hauptmann的舞台剧《纺织工》为题材。她差一点就获得了Grosse Berliner Kunstausstellung(相当于巴黎的绘画沙龙)大奖,但是威廉二世大帝否定了评委们的选择而转投了其他作品。(“秩序与荣耀的象征属于那些应获得荣誉的男人,”他曾经这样说。)
这并未停止她的创作。1919年,她成为了现代时期首个入选普鲁士艺术学院的女性,后来成为了那里首位女性教授(1928年开始执教)。到这个时候,在一战当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彼得的珂勒惠支已经是一位公众人物了。她的政治性作品经常出现在报纸和海报当中,并逐渐被大众所熟知,她也因此取得了成功。1933年,纳粹因为她的盛名而迫使她辞去学院的职位、禁止她的作品展出。
到了1950年代中期,离她去世还不到10年时,她那些与社会紧密相关的作品在艺术圈中就已经丧失了地位。美国艺术理论家Lucy Lippard说,珂勒惠支从大家的视线当中消失,是因为她并未遵从战后艺术圈的常见套路,而是一如既往地扎根在真实的生活之中:她并未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天才或局外人的形象,而是依然以贫穷、饥饿、母爱、死亡、丧亲之痛作为创作的主题。
 珂勒惠支,《革命1918》,1928。图片:?K?the Kollwitz Museum K?ln
珂勒惠支,《革命1918》,1928。图片:?K?the Kollwitz Museum K?ln
1967年,她的百年冥诞之际,德国评论家Gottfried Sello在西德周刊《Die Zeit》中这样评价她的这种创作方式:“虽然观念激进,但是珂勒惠支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艺术家。“但是,这种看上去的保守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在与历史、美学、以及政治的复杂关联当中,珂勒惠支的绘画、蚀版画、铜版画、木刻版画、以及雕塑可以得到迥异、甚至自相矛盾的解读:德国保守派人士敬仰她的艺术创作技巧、以及其中因为见证了凯撒时期的德国而产生的那种若有若无的怀旧之情。而同时,左派人士也对她的反战立场以及作品中反映出的阶级观点大加赞誉。另外,女权主义运动也将珂勒惠支当作反抗当时艺术机构陈规、为后来女性艺术家开拓道路的行为标杆。
不过,当代德国对于珂勒惠支的认知并非围绕着政治,而更关注她的生平与创作。史学家Yvonne Schymura出版的一部重要传记(C.H。 Beck在2016出版)将珂勒惠支描绘成了一位“不受政治和个人冲突所影响“的人物。今年在德国两家珂勒惠支博物馆举办的150周年纪念展也呈现了这样的观点,将焦点置于她的自画像(科隆珂勒惠支博物馆)、以交友圈(柏林珂勒惠支博物馆)上。同时,在柏林Prenzlauer-Berg区 Galerie Parterre的特展——这也是她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则关注与她与柏林这座城市的关系。(《K?the Kollwitz und Berlin》最近由Deutscher Kunstverlag出版)。
而在美国,她的作品似乎代表了某个特别的历史时期,比如即将于7月末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幕的“一战与视觉艺术“展览中,这个由Jennifer Farrell策划的展览将会把珂勒惠支的作品与Otto Dix、Fernand Léger、George Grosz、以及Edward Steichen的作品一起展出。
英国大英博物馆与Ikon Gallery则将在9月推出“艺术家肖像:珂勒惠支“。据新闻资料介绍,这个展览的主旨是呈现“一位艺术家保持创造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珂勒惠支,《暴乱,Plate 5》,1893-7。蚀版画。 图片:?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urtesy Ikon Gallery
珂勒惠支,《暴乱,Plate 5》,1893-7。蚀版画。 图片:?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urtesy Ikon Gallery
对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家、2017年柏林艺术学院珂勒惠支奖得主Katharina Sieverding来说,珂勒惠支作品的最大特征就是充满感情。“珂勒惠支关注社会与政治问题,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发挥作用,“Sieverding说。“影响其他人的效果在这里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她的生活和工作,自我决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Sieverding看来,珂勒惠支在当代艺术圈鲜少被提及的重要原因是大家关注的是她的个人生平而不是作品。
实际上,这似乎显示了某些艺术家最好要回避的问题。据珂勒惠支传记(Bertelsmann,2015)的作者Yury与Sonya Winterberg介绍,“No more war,no more Kollwitz!“(不要战争,不要珂勒惠支!)的口号多年以来一直出现在德国的艺术学院当中。很明显,(珂勒惠支)对于无产阶级惨痛处境的同情与情感联系与许多德国艺术家们嘲讽、享乐主义的自我定位格格不入(特别是从马丁·基彭伯格开始)。
实际上,基彭伯格1984年创作的一个系列绘画作品(1990年代再次出现)呈现出的就是这种态度:这些名为《Krieg b?se》(淘气战争)的作品,呈现的是各种圣诞老人与被涂抹的战舰在一起的主题。他也许是在拿安塞尔·基弗的风格开涮,但是也很可能在以珂勒惠支著名的反战海报当靶子。
1980年代中期,游击队女郎小组用珂勒惠支的名字为其中的一个成员命名,以表达自己对她的崇敬。(虽然这个团体的成员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保持匿名,但是他们会使用“代号“来相互区分。她们选择的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女性艺术家,比如弗里达·卡洛、艾娃·赫斯、Paula Modersohn-Becker、Gertrude Stein、或者乔治亚·欧姬芙)。
当下,作为抗议和抵抗形式出现的艺术家身份受到了长久未曾出现过的关注,但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珂勒惠支一直在这种关注和议论中缺席。与Corita Kent (1918–1986)、Alice Neel (1900–1984)或者与珂勒惠支同时代的美国画家Florine Stettheimer(1871–1944)这些充满激进政治思想的艺术家不同,艺术圈常见的对不知名人物的再发掘、再认识、重新评价似乎对珂勒惠支都是免疫的。
问题的关键也许是,先决条件应该是不知名。就像柏林的策展人Hans-Jürgen Hafner对artnet新闻所说的,珂勒惠支的作品“不可能再被有效地重新拉回主流视线。“因为珂勒惠支的名字一直出现在德国各地的学校、大街、广场上,她的形象出现在邮票上,作品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因此,她从来没有被真正忘记过。在她150周年冥诞那一天,谷歌的德国网页甚至专门用一个涂鸦向她致敬。
 珂勒惠支,《死亡与女人》(1910)蚀版画。 图片: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urtesy Ikon Gallery
珂勒惠支,《死亡与女人》(1910)蚀版画。 图片: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urtesy Ikon Gallery
珂勒惠支经久不衰的流行秘密何在?而为什么少有当代艺术家会以她为参照?“在我看来,“科隆艺术家Claus Richter——也是少有的几个公开承认自己热爱珂勒惠支的人——说:“珂勒惠支是一个出色的观察者,她的作品充满了力度,但同时有着无与伦比的细节。虽然这并非当下‘好‘艺术的考量标准,但我总是被她的绘画和雕塑打动。”
这么多年来,珂勒惠支将自己的艺术发展到了普世的人道主义视觉语言。从早期精细的蚀版画,到晚期表现主义的木刻版画与平版画和雕塑,灰色调慢慢变成了力量感十足的黑色。最棒的事情就是去临近你的藏有珂勒惠支作品的博物馆一窥究竟。想要以全新的方式来审视珂勒惠支的整体创作,首先要摒弃Betroffenheitskitsch这个经常被用来蔑视她作品(意思是“矫情的媚俗“)的德语词汇。随后,你会发现优秀、力量十足的艺术。

![汪吟泉《猴王宴乐图》赏析[图文] 汪吟泉《猴王宴乐图》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btczy5alq5.webp)
![美术博物馆应该引入市场化管理[图文] 美术博物馆应该引入市场化管理[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ul5kti4gxg.webp)
![我们逛博物馆的速度是否太快了[图文] 我们逛博物馆的速度是否太快了[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yh01zum40x.webp)
![生死劫难下,那个温柔而坚韧的女画家[图文] 生死劫难下,那个温柔而坚韧的女画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fizrn0xr10.webp)
![席镇: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图文] 席镇: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b0q3z34mz3.webp)
![传艺术之大美——著名画家朱汉云[图文] 传艺术之大美——著名画家朱汉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qnhwn0ur4p.webp)
![河南博物院恢复开放 5G互动带给观众全新体验[图文] 河南博物院恢复开放 5G互动带给观众全新体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zfailwhdgg.webp)
![指画:也叫文人画或者书房派画[图文] 指画:也叫文人画或者书房派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brlqzkfh1e.webp)
![成品市场低迷徘徊 原料市场高歌猛进[图文] 成品市场低迷徘徊 原料市场高歌猛进[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rcllu4gl2d.webp)
![善本碑帖的价值不是拍卖市场说了算[图文] 善本碑帖的价值不是拍卖市场说了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35frfjybgl.webp)
![浅聊疫情中的艺术创作规律[图文] 浅聊疫情中的艺术创作规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y1kusoe1qc.webp)
![画壁上的千年寻踪——浅谈敦煌壁画对当代工笔重彩画创作的启示[图文] 画壁上的千年寻踪——浅谈敦煌壁画对当代工笔重彩画创作的启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zuvnljwlw0.webp)
![叶浅予先生的速写启示[图文] 叶浅予先生的速写启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dkuc2ilpoo.webp)
![书法家孙若曦:且将鸿志寄诗书[图文] 书法家孙若曦:且将鸿志寄诗书[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ogsifp0pjb.webp)
![红木市场市场需求下滑:价格指数继续下行[图文] 红木市场市场需求下滑:价格指数继续下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rtrx5u0frp.webp)
![布尔乔亚:爱恨交织的生命痕迹[图文] 布尔乔亚:爱恨交织的生命痕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t1t3utrez3.webp)
![郑忠后抽象水墨画解读[图文] 郑忠后抽象水墨画解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nbazsn1wu5.webp)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4mhciphhag.webp)
![如何欣赏白石虾和悲鸿马[图文] 如何欣赏白石虾和悲鸿马[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04yciipfmm.webp)
![高调的《万山红遍》与低调的李可染[图文] 高调的《万山红遍》与低调的李可染[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pe31i4qaie.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