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置作品《每一扇门里都有鲜花2》150cm×235cm19世纪法国古董门2012年
从音乐到视觉艺术创作,艾敬的艺术创作不能称其为“转型”或“跨界”,更恰当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延续。艾敬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一方面延续着一贯对生活的敏感和对人类共通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在音乐、美术、文学等领域往来自由,形成了其创作的丰富多样。
商报:近日,您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个展,包括了近200件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从规模上看,本次展览更像是回顾展,这是否是您对10年跨界创作的一次总结性梳理?
艾敬:国博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那里收藏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宝贵的艺术遗产,而国博也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向全世界的艺术门类。在推动文化发展的政策下,我有了这次展览的机会,国博选择我作为这座艺术殿堂举办首个当代艺术展的艺术家,作品一定要有体量和质量,我的创作关注从个人微观出发的视觉记录,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风格。
我在艺术创作观念上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早期音乐创作的历程中。旋律与歌词、演唱与表演的演变,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经历和学习过程,音乐本身就是艺术,应用到观念和视觉艺术的创作上,只是不同材料和媒介的转换和使用。过去的经验可以运用到今天的创作中,而且随处可见。例如,我的作品《枪与玫瑰》、《ILOVEHAVEYMETAL》等,很多作品的灵感或名称都来自过去的音乐知识,这些都被自然的应用。因此本次展览也可以被看做是一次创作积累和回顾,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汇报。
商报:您在纽约生活多年,纽约的艺术氛围似乎对您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例如涂鸦,以及一些偏波普化的创作。同时,作品语言也日趋国际化,东方的生活背景和经验在您的创作中有怎样的导向?
艾敬:尽管我的表现形式是西方或者是国际化的,然而我的精神内核是中国的。我认为,首先当代艺术语言一定要有直观和直接的穿透力与沟通能力,就像伟大的思想家必定有简练易懂的语言一样。其次,作品的内容一定要结合对当下社会的观察以及态度,同时需要有与世界对话的能力,这个对话能力需要借助艺术家自身的民族和文化背景。
具体来说,我的装置作品《生命之树》是我对环境保护以及近几十年中国发展历程中需要探讨和关注的话题;《枪与玫瑰》是我对于和平的态度;《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是把家乡的地域文化以及个人情感重新提炼与展示;《棋子》则借助东方语汇,用当代的材料语言结合与西方的交流。
商报:很多人认为您是一位跨界跨得比较彻底的艺术家,多年的音乐创作经历在您作品的视觉呈现上有哪些影响,您创作的动机更多来自音乐还是视觉?
艾敬: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音乐的创作与传播力量,或者说音乐的创作形态,一直引领着视觉艺术的创作。我个人创作的转变是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游历西方美术馆和博物馆以及画廊等得到的艺术熏陶,也有自身对于艺术表现的纯粹性追求。1999年,我开始拿起画笔并逐步淡出乐坛时,并没有预料到今天艺术的繁荣景象。对于视觉艺术的创作投入,是出于我对此艺术语言形态着迷。
商报:不同于艺术家在正式创作前会经历多年基本功的训练,您似乎是直接进入创作状态,这种进入艺术的方式在您看来是否会带来一些缺失?
艾敬:创作能力不是单纯的训练便可以培养的,艺术家需要对很多门类的艺术形式都进行学习,技术服务于想法。
商报:著名当代艺术家张晓刚[早期曾就绘画对您进行指导,这对您此后的创作产生哪些影响?
艾敬:张晓刚给予我的帮助是把我引入艺术这扇大门,在这扇门里有着广阔的天地,这里的创作过程符合我的天性。这扇门的道路并不平坦,也很漫长,然而走到后来你总会看到鲜花。
商报:您的音乐带有很强的叙事性,而在艺术创作中您却偏好一些宏大主题和观念性的表达,艺术家和创作歌手对您来说似乎是两个独立的身份。
艾敬:我认为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做了哪些事情。我希望观看作品的观众能够受到启发,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潜能等待挖掘。
商报:在做音乐获得很大成功时,您选择了艺术,并一直坚持下去,并不是“玩票”。对您来说,音乐和视觉艺术在您的生活中是怎样存在的?
艾敬:我过去的音乐创作经验一直用于视觉艺术的表现,例如,雕塑作品《海浪》,在展示这件作品时,我注重观者的感受,将作品放置于一个相对黑暗的空间,借助视频海浪的画面和声音烘托对作品的理解和体验,而不是仅限于灯光对雕塑局部的投射。同时,我也曾经有《纽约的声音》和《上海的声音》等着重于声音的装置作品,我还会继续这种连接声音与视觉艺术相结合的变现方式。
商报记者周晓

装置作品《棋子》90cm×33cm紫铜、烤漆2010年

油画作品《ILovecolor》90cm×90cm2012年

装置作品《生命之树》350cm×350cm木材、钢2010年

![专家称红色收藏可重点关注抗战邮票[图文] 专家称红色收藏可重点关注抗战邮票[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y50xhtyqmw.webp)
![俄罗斯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绘画的启示与影响[图文] 俄罗斯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绘画的启示与影响[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yq3rzgrhrc.webp)
![王羲之米芾颜真卿等古代书法大家的签名精选[图文] 王羲之米芾颜真卿等古代书法大家的签名精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shj2gnzi0r.webp)
![“黑科技”助力川博千年文物焕生机[图文] “黑科技”助力川博千年文物焕生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lswldr1zps.webp)
![版画是现当代艺术中的硬通货?了解下[图文] 版画是现当代艺术中的硬通货?了解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jvksalsdaw.webp)

![为“瓷母”正名!乾隆“大花瓶”很丑?[图文] 为“瓷母”正名!乾隆“大花瓶”很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4lwmlr51hz.webp)
![孔达达之笔墨探索:气象之下,法度之外[图文] 孔达达之笔墨探索:气象之下,法度之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bi4czwsjvi.webp)
![凝重唯美,富有张力——崔泉溪作品赏析[图文] 凝重唯美,富有张力——崔泉溪作品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ddgy5pjbby.webp)
![许彦君写意花鸟画作品赏读[图文] 许彦君写意花鸟画作品赏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yon13bamdp.webp)
![为什么人人都爱弗洛伊德的“变态画”?[图文] 为什么人人都爱弗洛伊德的“变态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unqmpkabpo.webp)
![隐括众长,形神兼夺 —— 著名画家李治作品欣赏[图文] 隐括众长,形神兼夺 —— 著名画家李治作品欣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0v40vhla0a.webp)
![孟云飞:高校校名书法赏析之——北京师范大学[图文] 孟云飞:高校校名书法赏析之——北京师范大学[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5xmk0bpz1k.webp)
![【老骥伏枥 矢志艺道】特别推介崔培鲁先生的中国画艺术[图文] 【老骥伏枥 矢志艺道】特别推介崔培鲁先生的中国画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xlzkl5ekbx.webp)
![乾隆的古陶瓷品鉴定法[图文] 乾隆的古陶瓷品鉴定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y53brlgd5d.webp)
![古壁画描绘盛唐贵妇的闲适生活[图文] 古壁画描绘盛唐贵妇的闲适生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waj0iih3ii.webp)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 崔子范:新时期写意花鸟画的里程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4mhciphhag.webp)
![荣宝斋上海拍品赏析:林风眠《双鹭》[图文] 荣宝斋上海拍品赏析:林风眠《双鹭》[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ywmjiqziov.webp)
![陈履生:博物馆是面镜子 创造和维护特色很重要[图文] 陈履生:博物馆是面镜子 创造和维护特色很重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mnliuebg3w.webp)
![论博物馆创新维护的重要性[图文] 论博物馆创新维护的重要性[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zw4qnhzr14.webp)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纪萍[图文] 2024全国两会书画焦点人物——画家纪萍[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r2zvuofasd.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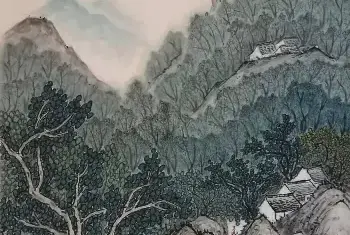


![【文脉华彩·罗建泉】时代颂歌|罗建泉国画艺术[图文] 【文脉华彩·罗建泉】时代颂歌|罗建泉国画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dzx5sdzolt.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