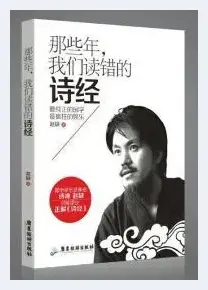
《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对《诗经》做出颠覆性解释
华西都市报:“硕鼠”是“诗经”时代的“网络谣言”;“窈窕”二字与“苗条”绝没有半分关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并非男女之间的誓言,而是男人之间的约定;“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的“伊人”不是“美女”,而是老翁……最近《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作者、诗人赵缺对《诗经》做出了全新的颠覆性解释。
在《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中,一些颠覆性的观点屡见不鲜。我们不禁好奇,这些观点是怎么考证出来的?作者赵缺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对于经典、国学,他又有怎样的观点?为此华西都市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尽力探索出《诗经》原本的意思”
华西都市报:谈谈你写《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这本书的过程吧。
赵缺:前后我写过3个版本。我先按照《诗集传》来翻译,但发现一些解释,或者在细节上无法成立,或者朱熹自己也回避了一些词、句的注释。之后我又按照《毛诗正义》译了一遍,当中的注解严谨很多,但同样存在问题,其中政治意味太浓厚。最后第三版,是我完全推翻了前两版,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结合平时大面积的阅读,详加考证,最后综合解读出来,希望能尽量贴近《诗经》原本的意思。
华西都市报:您说您看了近几十年来市面上对《诗经》比较流行或者比较权威的几十种版本,“发现全部翻译得非常可笑”。为什么《诗经》这本大众熟识度如此之高的经典,却没有一本靠谱的白话文注释本?
赵缺:在我看来,当今大学的教授几乎都不太懂《诗经》的内涵。无论他们怎么研究、怎么努力,都是缘木求鱼。某些“文化精英”,或为了迎合时势之需要,或为了成就一己之声名,往往会肆意地践踏经典、歪解《诗经》。名校学子、名师传人捧着谬误百出的教材,研习一辈子,也不可能读懂《诗经》。
华西都市报:您对《诗经》的研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受到谁的启蒙?您又如何保证您的解读是正确的?
赵缺:作为一个诗人,我自然很早就开始阅读《诗经》了。上中学时,我就读过朱熹的《诗集传》。我没有启蒙老师,我读诗、写诗,纯粹出于个人爱好。我虽然没上过大学、没拜过老师,但是读过的经传倒也不少。同时,我又是诗人、骈文家,平时就特别注意汉字的意义、用法,故而,我具备正解《诗经》的能力。我当然不能保证我所有的解读全都准确无误,不过,我可以保证,我的解读比当前任何一种解读都更接近《诗经》的原义。“在娱乐的过程中,获取纯正的国学知识”
华西都市报:为什么会选择采用显得比较“娱乐”的通俗风格,去表达你解读《诗经》的观点?
赵缺:我前面已经说过,国学对我而言,原本就是一种娱乐。我认为,娱乐化是复兴国学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一直力求令读者在娱乐的过程中,获取纯正的国学知识。《诗经》其实挺好玩的。我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一起“玩”《诗经》,爱《诗经》,“娱乐”《诗经》,最终读懂《诗经》。
华西都市报:在个人介绍中,您说自己“无师承,无高等教育经历。”您是怎么开始走上研究国学的道路?
赵缺:国学对我而言,原本是一种娱乐。我小时候没电脑、没网络,家里虽然有着电视机,可当时的电视节目实在无聊得很。我又不喜欢和同学一起出去瞎逛、打闹。因此,只能靠着读书来解闷!起初,我去书摊读连环画,后来长大了一些,就去图书馆借古典小说看。中学之后,觉得小说没劲了,就去我们那儿的文庙书市,翻看各种文言旧书。初中三年级时,我开始疯狂地作诗填词,至今为止,都写了二十多年了。研究国学,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还将出书解释《离骚》、《孝经》、《春秋公羊传》
华西都市报:对于国学,社会上的评价,比较极端,一阵子比较热衷,一阵子又有人批驳这股风潮。你自己是怎么理解“国学”这个概念的?
赵缺:20世纪不存在国学大师。一个真正的国学家,起码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能解读文言文原文;二、能创作出(非临摹出)合乎格律、章法严谨、对仗工整的诗词、骈文;三、至少精通一部经书。
华西都市报:除了《诗经》,您还会注释别的经典著作吗?就像《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这样的形式?
赵缺:目前是有这种计划。接下来,我还想写三本书:一、《离骚:一个自恋者的绝唱》;二、《孝经:国学入门第一课》;三、《春秋公羊传:我们其实是文盲》。其中,《离骚:一个自恋者的绝唱》的风格也许会类似《那些年,我们读错的诗经》。今人对于《离骚》、对于屈原存在着很大的误解。《离骚》的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用大白话翻译出来之后,感觉和“我爸是李刚”异曲同工。这是很搞笑的,这类笑点在《离骚》中屡见不鲜。写出来之后,大家一定爱看。至于《孝经,国学入门第一课》则是一部很严肃的作品。“孝”是中华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的集体信仰。《孝经》是绝对不能拿来娱乐的。
这些解读颠覆了我们所理解的《诗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里知名度最高的句子。今人流行的解释是,这是一个小伙子写给一位身材苗条的漂亮女孩的情书。但据赵缺考证,“好”读上声(hǎo),“逑”通“仇”,原义为“怨偶”(据《春秋左传》“佳偶曰妃,怨偶曰仇”)。一位穷“屌丝”苦恋“白富美”(“淑女”),求而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淑女”在“君子”的华丽攻势之下,最终成为一对“怨偶”。所以,赵缺认为,整首诗不是甜蜜的情书,而是充满自伤自怜的哀怨之作。他还发出感叹,“金钱、权力不能换取爱情,却能营造浪漫,而浪漫则是爱情的催化剂。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呜呼哀哉!”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组古老的经典诗句,不管是在婚礼上,还是在古典言情剧中,出现率都非常高。不过,如果赵缺告诉我们,这句话并不是指男女之间美好的契约,而是两个男人的恩怨,甚至还有“断袖之癖”的嫌疑。据赵缺考证,在先秦时期,“子”作为一种含有敬意的美称,略似于后世的“先生”、“您”,在古代男尊女卑的时代,普通人一般只会称妻子为“汝”或者“尔”,绝无可能在山盟海誓的时候突然客气起来,无缘无故,称妻子为“子”。于是赵缺认可这样的解释,这首诗是在一场古代战争中,“战士甲与战士乙牵手立约,希望彼此扶助,保住性命,平安到老。但是战士甲不守承诺,甩掉了战士乙,不管乙的死活。因此,满怀悲愤的乙,写了此诗。”在此解释的基础上,赵缺发出自己的质疑,“两个男人没事手牵着手,还要一直到老”,恐怕不只是朋友的关系。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并不是说两个人的互相依恋之深,而是表示两人一天不见,关系便已疏远。而“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的“伊人”,并不是“美眉”,而是“渭水边钓鱼的大周功臣姜太公”。

![81岁老人收藏两百多把铜锁 有的要对诗才能打开[图文] 81岁老人收藏两百多把铜锁 有的要对诗才能打开[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frqdzc4z0y.webp)
![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申遗成功:见证地球演化[图文] 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申遗成功:见证地球演化[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hx20loxjf1.webp)
![比利时与意大利博物馆计划于五月中旬开放[图文] 比利时与意大利博物馆计划于五月中旬开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ih0gpvjcxu.webp)
![吉瑞森教授西塘采风教学实录[图文] 吉瑞森教授西塘采风教学实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2kaq4xztdh.webp)
![踩画画家用脚踩出赵忠祥画像[图文] 踩画画家用脚踩出赵忠祥画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ifc3dux4ct.webp)
![工科男做精美纸雕 大学毕业前欲完成清明上河图[图文] 工科男做精美纸雕 大学毕业前欲完成清明上河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ngdv5rlo3g.webp)
![苏东坡在大观园“赏月”[图文] 苏东坡在大观园“赏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5imb5tqq5z.webp)
![水乡乌镇涌现水中国潮 互联网大会展现涵养魅力[图文] 水乡乌镇涌现水中国潮 互联网大会展现涵养魅力[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13mwivn1xq.webp)
![冯远×长城葡萄酒|无尽意的艺术人生,无尽意的葡萄风味[图文] 冯远×长城葡萄酒|无尽意的艺术人生,无尽意的葡萄风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ugb1teetir.webp)
![当世界名画只剩下背景[图文] 当世界名画只剩下背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btxjmuinnd.webp)
![引帝王追捧的薄胎玉器何方神圣[图文] 引帝王追捧的薄胎玉器何方神圣[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qyssx0ejpw.webp)
![莱昂纳多写书法 为电影荒野猎人宣传造势[图文] 莱昂纳多写书法 为电影荒野猎人宣传造势[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y3efoy0xw2.webp)
![和珅咋能顺走乾隆鼻烟壶[图文] 和珅咋能顺走乾隆鼻烟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a3opq2wyqs.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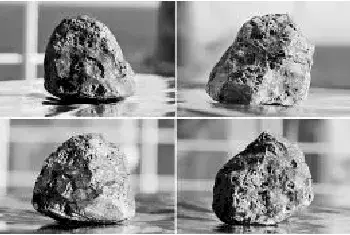
![7旬老人买下单元房打造收藏室:异石堆满屋[图文] 7旬老人买下单元房打造收藏室:异石堆满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dl0jkhzxsn.webp)
![被法老诅咒过的五大稀世珍宝[图文] 被法老诅咒过的五大稀世珍宝[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kq0hrsqy1s.webp)
![台湾1969年纪念币主角被找到[图文] 台湾1969年纪念币主角被找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cyy3vxrwsm.webp)
![揭秘特大名酒造假案:全球大藏家纷纷受骗[图文] 揭秘特大名酒造假案:全球大藏家纷纷受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3gzoravq3i.webp)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发掘明清档案精华[图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发掘明清档案精华[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xwbldvnwyn.webp)
![“神画”《忐忑》藏52幅画[图文] “神画”《忐忑》藏52幅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bgpn1ie5l52.webp)
![钻石与女人:色戒之殇[图文] 钻石与女人:色戒之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0kd2gkzxqt.webp)
![宋徽宗赵佶卖弄艺术风骚的轶事[图文] 宋徽宗赵佶卖弄艺术风骚的轶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otmx4lb1u2.webp)
![《蒂凡尼早餐》房间卖585万美元[图文] 《蒂凡尼早餐》房间卖585万美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1j00po1w43.webp)
![傅抱石名画历劫记[图文] 傅抱石名画历劫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abjkcu031b.webp)
![画家丁乙作品拍卖超千万 当年一幅画换一听咖啡[图文] 画家丁乙作品拍卖超千万 当年一幅画换一听咖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xsbybiruhd.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