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镶嵌狩猎画像纹豆, 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每次看故宫博物院的展览,老是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收藏珍品是怎么被积累并被保管起来的?比如在清皇朝被推翻前后,逊帝溥仪即以赏赐为名,将宫中的大量书画文物运出故宫,这证明当时皇禁不严,皇上可以任性地处理各种藏品,既如此,这官府收藏的规则何在?
商周时代起,王室与贵族就已经具有文明承传的意识,开始以收藏来积累文明的物质样态了。河南安阳殷代王宫遗址的发掘中,宗庙建筑的左右时见窖室,其中有许多器物尤其是青铜器在焉!但当时的确尚无体制,并无规矩可寻。西周时代则特设“天府”、“玉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较早”,“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在“天府”“玉府”有专职“藏室史”负责藏品归类整理并作“簿记”。其中,青铜彝器必然成为其中之大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哲学家老子曾为周之“守藏室之史”,更有“苏秦发书,陈箧数时,墨子南游,载车甚多。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梁启超语),如果这些还只是书籍收藏与应用,那么像司马迁“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观孔子之遗风”,则证明当时孔子有宗庙,“衣冠琴车书”一一生前的生活起居、著述、讲学诸遗物,受到“岁时奉祀”。这就是实物收藏的最早历史记录。
汉代特别建立“天禄”“石渠”“兰台”……诸台阁;汉武帝设“秘阁”,搜求天下法书名画和古物名品。尤其是后汉中期如陈遵辈手札尺牍久负时誉,于是受到从朝廷命官到士大夫的追捧。而在南朝梁武帝时的收藏,其规模之大,诚有今人想象以外者。隋文帝建“妙楷台” “宝迹台”,是皇宫书画分类贮藏的开端。但直到唐代,有萧翼赚兰亭故事,有兰亭殉葬昭陵故事,但关于唐代书画以外的古物尤其是青铜器收藏,却是语焉不详。北宋时期从宋太宗到宋徽宗,大批收藏书画而外,对青铜器古物的收藏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仿器的规模与质量,如大晟乐钟以及其宫廷演奏,还牵涉有名的词曲家周邦彦,实在是一个自古未有的涉及音乐与文学、兼合词史与乐史的大文化事件。不是修养深湛的宋徽宗,根本无法措手。当时士大夫阶层如欧阳修、刘敞、吕大临、米芾、薛尚功、王俅、赵明诚、李清照、李公麟等等介入收藏后,与文史相结合,遂形成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的宋代金石学运动。欧阳修有《集古录》十卷,李公麟收藏古代青铜器,考订世次,辨别款识,赵明诚、李清照则编《金石录》,集金周钟鼎彜器汉唐石刻拓本有2000多件;著名书法家米芾还开研究收藏史研究著述之先河,著《书史》《画史》流布世间,把这些私人收藏私人著述再与宋徽宗御撰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联起来看,或再与宣和画院等专业机构互为映照,说宋代是人文时代,在收藏、研究方面有大进步,应该不是虚妄之言。
元明清以下皇宫的收藏虽然没有“首发”优势,但只要看看金章宗那一手漂亮的瘦金书,和柯九思任画学博士等等,即可知文脉不断。
真正在王朝的收藏历史中再续辉煌的,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部《石渠宝笈》,一部《天碌琳琅》,一部《秘殿珠林》,一部《佩文韵府》,一部《佩文斋书画谱》,浩瀚博大,条分屡析,几十册巨著的详细著录,是古代收藏史中从未有过的典籍记载,与此相对应的士大夫民间收藏,也是规模宏阔。比如周亮工、顾炎武、安岐、黄丕烈、高士奇、张廷济、瞿中溶、吴云、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吴大澂……朝野交汇,遂成清代收藏奇观。其中士大夫民间收藏与王朝收藏也未必非常泾渭分明,比如安岐、高士奇的收藏,最后全部被强迫捐献纳入皇宫,皇恩浩荡,岂敢有半个不字?
许多青铜彝器古物,都铸有“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字样,反映出收藏家本人希望传之久远的美好愿望,但千百年来,有哪些古物最后是可以“永保”的?历代收藏家们的际遇与心态告诉我们,富不过三代,“永保之”其实也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而已。勿为物累,勿为心炫,顺势而生,随遇而安,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王朝如此,王朝的收藏亦复如此。
来源:杭州日报

![关于清代扳指 你了解多少[图文] 关于清代扳指 你了解多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1bhf4cq50m.webp)
![除了众所周知的《我住长江头》原来他的书法长这样[图文] 除了众所周知的《我住长江头》原来他的书法长这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awneqepzsu.webp)
![网友画拟人月饼 吐槽:五仁滚粗月饼界[图文] 网友画拟人月饼 吐槽:五仁滚粗月饼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1x2b5myo32.webp)
![惟妙惟肖食物清代仿生瓷[图文] 惟妙惟肖食物清代仿生瓷[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aztzhvkerc.webp)
![广东肇庆雕砚人变身齐白石齐门治印传人[图文] 广东肇庆雕砚人变身齐白石齐门治印传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fe511telp3.webp)
![追逐着灾难的艺术家们[图文] 追逐着灾难的艺术家们[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sumqtwxbde.webp)
![河北省书画艺术研究院在井陉于家石头村挂牌建立采风创作实践基地[图文] 河北省书画艺术研究院在井陉于家石头村挂牌建立采风创作实践基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soz2t3zqwd.webp)
![名画因显色情被移出英国画廊 接着会轮到毕加索吗[图文] 名画因显色情被移出英国画廊 接着会轮到毕加索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bnnzrgrz4p.webp)
![是谁包养了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图文] 是谁包养了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dhb11egoyu.webp)
![中国古代的瓷合[图文] 中国古代的瓷合[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1irlvh03zo.webp)
![放大镜作画笔太阳光当颜料 另类艺术家新奇作画法[图文] 放大镜作画笔太阳光当颜料 另类艺术家新奇作画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mzn2fpg5ac.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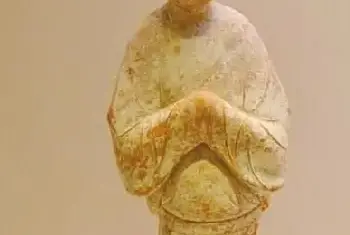
![李赞集:无私奉献 大爱无疆[图文] 李赞集:无私奉献 大爱无疆[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manff4ttzu.webp)
![纽约艺术家偷拍邻居私密生活并展示于众 遭群诉[图文] 纽约艺术家偷拍邻居私密生活并展示于众 遭群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jokm2yucws.webp)
![齐白石为争一幅废画 巧斗毛泽东郭沫若[图文] 齐白石为争一幅废画 巧斗毛泽东郭沫若[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b4czr2ss1z.webp)
![震旦博物馆:陆家嘴上班族新去处[图文] 震旦博物馆:陆家嘴上班族新去处[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zbrg1z03cf.webp)
![老人40年收藏毛主席像章2.8万枚[图文] 老人40年收藏毛主席像章2.8万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544uc2oq00.webp)
![张之洞也曾以润笔受贿[图文] 张之洞也曾以润笔受贿[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gaqv44dcpy.webp)
![杨澜老公15万收藏姚明葡萄酒[图文] 杨澜老公15万收藏姚明葡萄酒[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zazm3vmpdi.webp)
![道士邱处机与玉器行业[图文] 道士邱处机与玉器行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eunz5pbfy2.webp)
![女子9.99美金买到抽象画大师作品[图文] 女子9.99美金买到抽象画大师作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hmyyfyyfja.webp)
![毕加索的裸女画在欧洲机场引起风波[图文] 毕加索的裸女画在欧洲机场引起风波[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vu5hcrduyx.webp)
![民国女性的自我描摹[图文] 民国女性的自我描摹[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nqejjtbrzn.webp)
![纽约摄影大师和他的赤裸世界[图文] 纽约摄影大师和他的赤裸世界[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az1vqq4tha.webp)
![康有为故居叫价1000万背后:因康有为贵了一倍多[图文] 康有为故居叫价1000万背后:因康有为贵了一倍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5zuh5na1ty.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