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期参加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工作的学者,浙江大学教授缪哲在《“宋韵今辉”系列学术论坛·宋画与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会议上,谈到“宋画如何被认识”的问题。在我们的观念中,“宋画”的概念,理应产生于宋代。但缪哲说,“宋画”的概念,其实还很年轻,是在二战之后才塑造形成的。在明末至20世纪的几百年里,人们其实不太清楚什么是宋画,也不认为宋画是重要的。
缪哲 | 宋画是如何被认识的
(本文根据会议报告整理)
关于宋画的知识,我们可以用《全唐诗》来做一个比较。
康熙朝编纂的《全唐诗》,当时有900卷。1960年代中华书局排印之后,共有25册。1990年代初,中华书局又出版了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补编》,同样也是大32开本,只新增3册。也就是说,康熙朝的《全唐诗》,至今仍然是无法取代的,整体还站得住,后世只是补充了少量漏编的作品而已。
《全唐文》的情况也类似,它们仍是今人日用的史料。
但是如果康熙朝要把当时所认识的宋画,全部编纂起来,像今天《宋画全集》一样印刷出版,它能不能像《全唐诗》这样,还站得住呢?
肯定站不住。它会有两个大的问题:会收录进太多的非宋画,这个比例,我想应该在60%~70%之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漏收太多的宋画,这部分的比例,估计要占现在传世宋画的30%。
所以说,康熙朝即使编了一部《宋画全集》,在今天也只有学术史的价值,无法像《全唐诗》《全唐文》这样,作为研究的第一手史料。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不同?
这关系到对宋画认识的历史。这里有三个大的关节点:明末,20世纪初-30年代,二战之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宋画”概念,其实主要是在二战之后塑造形成的,不过几十年而已,还很年轻。
明末:大量浙派画被改款为宋代画
明代的朝廷,不怎么关心绘画收藏;民间的收藏,则集中于太湖、松江地区。这个地区由于地方传统的原因,偏好“元四家”“明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传统,对于什么是宋画,概念是比较模糊的。
与此同时,当时还流行继承南宋传统的浙派绘画。在晚明之前,民间对浙派的收藏还有不少,虽然没有元、明四家那么显赫。
但是到了17世纪末,情况突然就变了。
明末清初的鉴赏家顾复在《平生壮观》中回忆,他父亲曾对他讲,浙派的大师,如边文进、林良、吕纪等,继承的是南宋画院的传统,作品非常精彩。因此顾复年轻时,就很喜欢浙派。但是中年以后,他迷上了“元四家”的山水,对于浙派开始不太瞧得起。
恰恰在这个时候,顾复发现市场上浙派的作品突然少了。为什么呢?他听人说,浙派山水、花鸟作品,往往被拿去洗款、改款,然后伪装成宋画出售。

明 林良《锦鸡图》 155×92.6cm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从后来的研究看,顾复讲的个人经历,其实代表了明末清初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个时期,大量的浙派或者接近浙派的作品被改款为宋画,流入不同的藏家手里。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有过估计,说“这个数字应该在数百到一千多件”。
大家知道今天《宋画全集》收录的全部宋画,也才一千多件。所以班宗华提到的这个数量是巨大的。可见当时有一场庞大的造假运动,这一下子搞乱了人们对“宋画”的认识。
这样到乾隆开始建立他的收藏时,“宋画”这个概念变得很空洞、模糊——什么是宋画,什么不是,经常搞不太懂。
我们以范宽著名的《溪山行旅》为例。乾隆的内府中,有两件《溪山行旅图》;一件真的,一件是王翚的临本。但是乾隆朝的鉴藏家们在鉴定的时候,竟把王翚的定为原作。范宽的原作,反而被扔在一旁。

北宋 范宽《溪山行旅图》180×104cm 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 王翚 《(仿范宽)溪山行旅图》198×97cm 图片来源:inkston
现在我们知道,北宋的雄伟山水,每个组成之间都是相对独立的,前景和中景清晰地分割,同时有强烈的比例对比。
王翚的这幅山水,底下截了一段,前景和中景融合了——这时所谓龙脉观念的影响;比例也不对,山一下变小了。当然这些认识是我们后来获得的,但当时连最高明的宫廷鉴定家都不知道。
20世纪初到30年代前后:宋画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这一阶段跟之前阶段的主要区别,是对宋画意义的认识;对于“什么是宋画”其实也还不清楚。
20世纪30年代,对宋画的认识发生的变化是根本的,决定了我们今天对宋画的观念。
具体地说,就是把“宋画”理解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体现,或者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浓缩。这个认识的变化,跟当时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有关。
这个想法的灵感是从西方来的,尤其是德国,具体地说,就是黑格尔所说的“volksgeist(人民民族精神)”,以及和这个概念有关的一套理想。这套思想的核心是认为:一个文明的性格和精神,浓缩在它的艺术里。
这个思想传到中国之后,大家就开始在中国不同时代的绘画中,寻找一种绘画类型,用它来代表正在纳入世界体系中的中国。
最终被选中的就是“宋画”。
为什么是宋画呢?
跟元代开始的文人画相比,宋画更写实;在气质上,很接近西方文艺复兴传统所代表的那套写实绘画。
最早接受这个想法,开始鼓吹宋画的是康有为,后来有蔡元培、陈独秀等,最著名的,当然是徐悲鸿。
1918年,徐悲鸿和北大画法研究会的成员,去故宫古物陈列所看了一批书画,忘了是看前还是看后,他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中国画改良之方法》,认为15世纪之前,中国绘画一直是全球领先的,它的黄金时代在宋代,以后就没落了①。
这场报告可以说是关于宋画古今认识的一个分水岭,塑造了我们今天对宋画的认识:以前被推崇的文人画,开始被贬低。宋画则被抬到了国家民族象征的高度——当然这跟新文化运动的总体倾向有关②。
大家可能会问,具体是哪些宋画激起了康有为、蔡元培、徐悲鸿等人的这套想法?他们甚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绘画是受宋画影响建立起来的。
从我了解的一点点材料看,其实他们没有看到多少真宋画,或者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宋画。我猜他们看到的,大部分应该是晚明以来的那些伪宋画。
比如徐悲鸿演讲里称赞的宋画,大部分我都没有听说过。其中有一件作品,说是宋代林椿的《四季花鸟图卷》,这后来被证明是很晚的一件仿品。
演讲中徐悲鸿还大力赞扬了一件号称是宋代李相的《东篱秋色图》。这张画,从山体的融合程度上看,显然不是宋代的画法,比例也不是宋代的比例,应该是明代院体画家或者是浙派的一件作品。
总之当时被他们推尊的“宋画”,主要是一个概念。临到具体的作品,还往往受晚明人的骗。

明 佚名《东篱秋色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不仅是国内的理论家、鉴赏家,国外收藏中国画的观念也一样。在徐悲鸿推尊宋画的时代,美国开始系统性地建立中国艺术的收藏。其中的领袖,就是建立波士顿美术馆东亚部的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还有资助建立弗利尔美术馆的工业大亨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他们对于中国不同时期绘画重要性的认识,跟董其昌以来的本土传统截然不同,他们只注重宋画,排斥元明的文人画传统。
在1919年,也就是徐悲鸿发表演讲后的一年,弗利尔写信给上海的一个古董商——也是他的一个买手王鑑堂,对于王不断地送文人画来,大表不满,并指示说:"Don’t sent me any Ming or later pictures. I only buy Sung and earlier paintings(别再送明以后的画了,我只买宋或更早的画)."
这个趣味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从日本受到的影响③,也有西方文艺复兴写实主义传统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美国收藏,基本也是以宋画为追求,此外也包含元代继承宋画传统的画家,比如孙君泽、唐棣他们的作品。
但问题是,天下哪有那么多宋画?
大量的宋画,不过是明代改款的浙派而已。所以这个时期,大量的浙派画(当然其中有少量的真宋画)就以“宋画”的名义,流进了美国的博物馆,其中最主要的去向就是弗利尔美术馆。如今这个馆的大量浙派精品,就是这么来的。

弗利尔美术馆藏的一件明代“浙派”作品《湖畔消夏图》
这件作品曾经归于范宽名下。曾先后由王鑑堂、查理斯·朗·弗利尔收藏,1920年始藏于弗利尔美术馆
图片来源:弗利尔美术馆
二战之后:宋画的再发现
二战之后,天下太平,美国成了最先进、富饶的国家。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就率先在美国的博物馆、大学中繁荣起来,系统的学术制度也开始成型。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战前汇集起来的大批的宋画,或者所谓的“宋画”。这方面工作,最早从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开始,他当时是弗利尔美术馆的研究员,对战前汇集的200余件所谓的宋代绘画,作了第一次系统的甄别。一研究,不得了:他发现这些作品大部分应该归于浙派,不应该算宋画。
这样一来,“宋画到底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就冒了出来。宋画研究的热潮,也就开始了。
首先要做的,是将明末以来混进宋画的浙派作品一件一件地剔除。去伪存真之后,宋画才能逐渐露出真面目。
二战之后到90年代,所有重要的艺术史研究者,几乎都参与了这场被学界称作“宋画再发现”的运动。包括高居翰(James Cahill)、方闻、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李雪曼(Sheman E.Lee)、史克门(Laurence C.S.Sickman)等在内的中国画史研究学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之后,台北故宫也在李霖灿的领导下,开始了宋画和浙派的甄别运动。他们的甄别成果,专门做了一场展览《追寻浙派》。
在高居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班宗华用甄别出来的“浙派”画,在德克萨斯做了一个展览:《大明绘画》。
同时,日本以铃木静教授为主,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出版了《浙派研究》等。
大陆方面,在1960年代启动了对国家馆藏的鉴定,但是这个工作在六、七十年代一度中断。1983年,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几位老先生,对全国公立馆藏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作了第一次系统的鉴定,大量被标为“宋画”的浙派作品和更晚一点的其他作品,被甄别了出来。
1990年代,根据老先生们的这批鉴定笔记,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8开本,23册。
这样经过全球不同地区的努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宋画的真面目就基本清晰了。
我请大家去比较一下三本教科书:
费诺罗萨1912年写的《中国与日本艺术的纪元》(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陈师曾1922年写的《中国绘画史》;
喜龙仁(Osvald Siren)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大师与原理》(Chinese Painting: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
1990年代由杨新、班宗华、聂崇正、高居翰、郎绍君、巫鸿共同执笔的《中国绘画3000年》(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他们对宋画的叙述,引用的例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早期教材说的“宋画”,很多你都没听说过;看到图,你就知道那是假的。
因此宋画并不是从宋代以来就有的概念,很长时间人们不太清楚什么是宋画,也不认为宋画是重要的。过去一百年,我们对宋画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对宋画的认识,大体是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不过区区几十年,还很年轻。
所以说,康熙朝即使能像编纂《全唐诗》《全唐文》这样编出一套《宋画全集》来,在今天也是一部“无用”的书,它只有学术史意义。不仅康熙朝,直到20世纪70、80年代,这项工作也都还不太容易做。
浙江大学编纂《宋画全集》赶上了好时机,从2005年启动的相关工作,是在二战以来,全球不同地区系统、密集、坚持地进行宋画甄别、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缺少这些前辈学者的努力,一部能站得住的《宋画全集》不可能形成。虽然现在《宋画全集》收入的很多作品还可以再斟酌,但是基础已经比较好了。
编辑注
① 1918年3月,徐悲鸿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同事们一起观赏了紫禁城文华殿内的古代书画,写下了《评文华殿所藏书画》一文。(《中国美术》2021年第4期《“自能画”与“复心得”——徐悲鸿的古代书画鉴藏》)
1918年5月14日,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演讲《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此文在当月23日~25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美术界》202年第2期《中国20世纪初的“美术革命”以及关于“改良中国画论”的争议》)
② 比如当时力主变革传统的有很多学术界、文学界的大家,像康有为、陈独秀、鲁迅他们的言论措辞都非常激烈,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策略。
③ 19世纪末,以恩内斯特·弗朗西斯科·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为代表的日本艺术爱好者群体,使得波士顿成了美国顶尖的亚洲艺术研究中心。他们对日本艺术的兴趣源自1876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利坚独立百年展,日本艺术品在展览中大放光彩。
1894年,波士顿人首次接触到中国经典绘画。时任波士顿美术馆主任的费诺罗萨组织了一次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佛教绘画展。费诺罗萨和未来的波士顿美术馆董事登曼·沃尔多·罗斯(Denman Waldo Ross)以及著名鉴赏家、艺术商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一同参观了这次展览。贝伦森记录下了他们的欣喜之情:“这些画的构图……和最伟大的欧洲绘画一样简洁完美……我为之倾倒。”费诺罗萨在看画时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自己也神魂颠倒……罗斯这个小个子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乐不可支。我们泪流满面,不停地戳、掐对方的脖子。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艺术欣赏体验。”(《帝王巨观:波士顿的87件中国艺术品》简·波特 Jane Portal)

![读刘建的中国画:都市水墨的文化拓展[图文] 读刘建的中国画:都市水墨的文化拓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gveinxsrff.webp)
![赵青仲:情洒雪景纵情水墨[图文] 赵青仲:情洒雪景纵情水墨[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toj5sjecdc.webp)
![为什么那些看不懂的艺术却那么贵?[图文] 为什么那些看不懂的艺术却那么贵?[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35da1c4wcj.webp)
![横眉描丑陋 温情绘忠友[图文] 横眉描丑陋 温情绘忠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srznrmk22f.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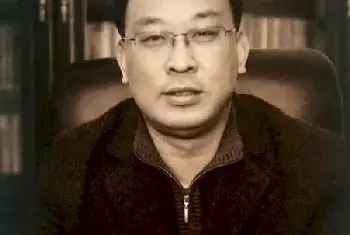
![迈克尔·莱杰:论波洛克的绘画[图文] 迈克尔·莱杰:论波洛克的绘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y5drrrfjpl.webp)
![面对眼盲——谜一般的苏菲·卡尔将目光投向不假矫饰的情感[图文] 面对眼盲——谜一般的苏菲·卡尔将目光投向不假矫饰的情感[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ycnq3batx0.webp)
![当代中西美术之比较[图文] 当代中西美术之比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zaklnjjkxy.webp)
![2024甲辰龙年——著名书画家钱小纯元旦特刊[图文] 2024甲辰龙年——著名书画家钱小纯元旦特刊[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k0av1ef4yy.webp)
![什么东西在香港拍卖市场卖得最好?[图文] 什么东西在香港拍卖市场卖得最好?[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yod4sb4ore.webp)
![投资热点·杨渝光[图文] 投资热点·杨渝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o2lb5suvqui.webp)
![端庄 俊秀 简约 洒脱一一李元博书法风格论析[图文] 端庄 俊秀 简约 洒脱一一李元博书法风格论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zdrrdi33az.webp)
![名家刻书画家用印收藏前景[图文] 名家刻书画家用印收藏前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ce3d03s43bo.webp)
![资本大运动下的十年拍卖市场[图文] 资本大运动下的十年拍卖市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vkizwqvl5m.webp)
![为什么没有皮色的籽料作品被市场冷落[图文] 为什么没有皮色的籽料作品被市场冷落[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yx0oghxib5.webp)
![高调的《万山红遍》与低调的李可染[图文] 高调的《万山红遍》与低调的李可染[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pe31i4qaie.webp)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齐白石花卉册页[图文] 海上雅集精品赏析:齐白石花卉册页[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pzow4tmkwk.webp)
![著名版画家阿太作品欣赏[图文] 著名版画家阿太作品欣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umbb3hb4qi.webp)
![「晶羚专访」张润萍和她温暖的猫[图文] 「晶羚专访」张润萍和她温暖的猫[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0h15gzu2pj.webp)
![冯少协:油画写真千年古镇[图文] 冯少协:油画写真千年古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i0dftsimsn.webp)



![刘玉来:提高素养更上一层楼[图文] 刘玉来:提高素养更上一层楼[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nutks51auq.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