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前卫艺术家致力于挑战艺术边界,艺术理论热衷于辩护这类艺术实践。但是,艺术家对艺术边界的消解并不彻底,因为艺术家挑战边界的效力来源于艺术家身份,而艺术家身份的获得建立在艺术边界的基础之上。真正消解艺术边界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工程师。在信息领域,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彻底模糊。通过艺术品来划出艺术边界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边界将彻底消失。或许我们可以从艺术家的角度来重新发现艺术边界。有鉴于此,针对艺术家研究的人类学,有可能取代针对艺术品研究的批评学。
艺术的边界,是将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的条件。之所以用边界而不用定义,原因在于在不能定义的情况下,艺术仍然可以拥有边界,艺术与非艺术仍然可以区分开来。诸如韦兹(Morris Weitz)、古德曼(Nelson Goodman)、卡罗尔(Noёl Carroll)等美学家认为,尽管艺术是不能定义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识别某物是否是艺术。对此,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给出了重要的启示。①根据家族相似理论,即使在缺乏定义性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将某些事物归为一类。例如游戏,尽管下棋、玩牌、打球等等之间没有任何共有的特征因而是不能定义的,但是根据交叉重叠的相似,还是可以将它们归入“游戏”这个类中。艺术也是如此,尽管绘画、音乐、舞蹈等等之间没有任何共有的特征可供定义,但是根据交叉重叠的相似,还是可以将它们归入艺术之类。尽管边界比定义的限定性要弱,仍然可以起到分门别类的作用。用艺术边界来取代艺术定义,事实上是对标新立异的艺术实践的一种退让。
一、艺术边界讨论的紧迫性
对艺术边界的挑战,主要来自艺术实践,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艺术实践。就像韦兹指出的那样,“正是艺术的扩张和冒险的特征,正是艺术始终存在的变化和新异的创造,使得确保任何一组定义属性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②换句话说,挑战定义和边界是艺术的本性,即使我们今天给艺术下了定义或者划出了边界,也不能确保它们明天继续有效,因为它们很有可能会激发艺术家的新的挑战。但是,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挑战艺术边界,或者艺术家的挑战之所以有效,原因正在于他的艺术家身份,而艺术家身份的获得又建立在艺术边界的基础之上。如果艺术边界消失,艺术家的身份也就自动失效,艺术家对艺术边界的挑战就将软弱无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情况:艺术家既挑战边界又维护边界。准确地说,艺术家挑战旧的艺术边界,建立新的艺术边界;艺术家挑战正统的艺术边界,维护异端的或者草根的艺术边界。从更长的时间范围来看,新的会变成旧的,异端或者草根会变成正统,又会引起新的挑战,如此循环演进,推动艺术史的发展。
这种通过挑战正统推动艺术发展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这在艺术史上可谓司空见惯,在科学领域更加突出,在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依据“图式与矫正”的原理来叙述艺术史,就与波普尔(Karl Popper)依据“猜想与反驳”来叙述科学史基本类似。③由此可见,无论在艺术还是科学领域,都存在对既成边界、权威或正统的挑战,进而形成新的边界、权威或正统,再出现新的挑战,以此推动历史的发展。边界的得与失,构成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如果边界的得与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煞有介事地讨论艺术的边界?尽管也有科学的终结的说法,但是科学的边界仍然是非常明显的,人人都是科学家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毕竟建立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没有适当的知识积累就无法涉足相关的科学领域。但是,艺术不同。艺术不依赖知识积累,而是依赖个人趣味和天才,因此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有可能的。④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艺术的各种可能性差不多已被穷尽,不断演进的艺术史业已终结,借用丹托(Arthur Danto)的术语来说,艺术进入了它的后历史阶段。后历史艺术(post-historical art),是一种没有统一风格的艺术,从而使得依据统一风格的艺术史叙事不再可能。⑤
根据丹托的后历史艺术概念,当代艺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艺术史的范围,从而摆脱了边界的建构与解构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束缚。换句话说,当代艺术只有对边界的解构和破坏,不再有对边界的建构和维护。大多数参观当代艺术展览的观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叹:人人都是艺术家,物物都是艺术品!正因为如此,对边界的讨论,在艺术领域比在科学、哲学、教育、历史等领域都更为急迫和热烈,尽管这些领域也有各种终结之说,但是只有在艺术领域边界的模糊成了一个主导性话题。
二、艺术的内部挑战
尽管艺术史本身就是由对边界的挑战与维护、解构与建构推动的,但是只有进入后历史阶段,才只剩下挑战和解构,而不再有维护与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略过艺术史上各种形式的边界建构和维护,集中考察后历史艺术对艺术边界的挑战。
丹托的全部艺术理论都受到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的启发,或者说都是在为沃霍尔的作品辩护。丹托承认,当他1964年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斯特布尔画廊(Stable Gallery)看到沃霍尔首次展出的《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的时候,就意识到艺术终结了,并开始思考和辩护《布里洛盒子》为什么会是艺术作品。“布里洛”是以色列生产的清洁块,专门用来擦洗铝制品厨具,美国引进后非常畅销,在超市经常有大量成箱的“布里洛”展示。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跟超市里的“布里洛”包装箱在外表上一模一样。唯一不同是,“布里洛”包装箱是用纸板做成的;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是用三合板做成的。但是,在丹托看来,这不是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成为艺术的关键。1964年丹托发表了著名的《艺术界》(Art world)一文,首次尝试辩护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是艺术。在丹托看来,沃霍尔的作品推翻了以往关于艺术的各种界定,完全取消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导致《布里洛盒子》是艺术而跟它一模一样的“布里洛”盒子不是艺术的原因,跟审美无关、跟认识无关、跟道德教化无关。丹托认为,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一种“理论氛围”(atmosphere of theory),也就是他所说的“艺术界”。需要注意的是,丹托所说的“艺术界”,并不是艺术作品内部所展开的世界,而是由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等等对作品所做解释构成的话语和文本世界,是从外部包围作品的世界。但是,丹托并不认为批评家可以点石成金,可以任意给某物以理论解释从而把它转变成为艺术作品。有关艺术作品的理论解释,必须是艺术作品暗示或者呈现出来的,用丹托自己的术语来说,是艺术作品所关涉的,是作品所具有的“关涉性”(aboutness)的展开。正因为有了这种“关涉性”,有了批评家由“关涉性”所做的理论阐发,在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周围形成了一种“理论氛围”,跟它完全一样的“布里洛”包装纸箱则没有这种“理论氛围”,由此决定了前者是艺术作品,后者则不是。为了证明两个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一样的东西之间仍然有所区别,丹托引用了青原惟信那段著名的语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⑥丹托想以此说明,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就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区别一样,它们在外显的或者可感知的特征上是看不出来的。从外显的或者可感知的特征的角度来看,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完全消除了。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彻底消除了。尽管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是艺术作品,但是跟它完全一样的超市里的“布里洛”包装纸箱依然不是。而且,丹托的“关涉性”概念,还隐含着“艺术界”或者“理论氛围”是由艺术作品指示出来的,因此也可以算是艺术作品所发挥的一种内在功能,而不能完全算是艺术批评家从外面赋予给它的。正因为如此,迪基(George Dickie)将丹托的艺术界理论视为传统艺术定义理论的最后残余。传统艺术定义理论都是从特征或功能上来做界定,丹托所说的“关涉性”也是艺术作品的一种功能,尽管不是审美功能。在迪基看来,包括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在内的传统艺术定义,都不能将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因为这些定义不完全是起分类作用,还起评价作用,即某物如果符合艺术定义,不仅意味着它是艺术,而且意味着它是好的。这种将分类与评价混为一谈的定义,永远不可能将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因为艺术作品中也有不好的,非艺术作品中也有好的。为此,迪基主张从程序上来界定艺术。程序定义只起分类作用,不做价值评判。只要通过某些必要的程序,某物就是艺术,但不一定是好的。迪基认为,从定义理论来说,依据程序的定义比依据功能或特征的定义要先进得多。迪基认为,某物要成为艺术作品,至少必须经过两道程序:首先要是艺术家有艺术意图的制作,其次要被艺术界接受。⑧迪基偏爱的例子是杜尚(Marcel Duchamp)的《泉》(Fountain),即那只臭名昭著的小便池。杜尚的《泉》与同批次的小便池没有任何区别,即使存在某些细微差别也可以忽略不计,唯一的区别是《泉》上有杜尚签名。但是,杜尚的签名并不是《泉》成为艺术作品的唯一因素,决定《泉》成为艺术作品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它被美术馆即艺术体制接受。《泉》通过了两个必需的程序,于是从小便池变成了艺术品。根据迪基,《泉》的艺术身份完全是艺术界从外面赋予的,与它自身的功能和特征毫无关系。这样,丹托艺术界理论中的“关涉性”这个最弱的功能,也被迪基剔除了。某物要成为艺术作品,跟它自身的特征和功能毫无关系。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彻底消解了。⑨
但是,无论是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还是杜尚的《泉》,它们对艺术边界的挑战都是来自艺术界内部,因为杜尚和沃霍尔都是训练有素的艺术家,而且正因为他们是艺术家,他们的挑战才具有效力。不是任何人在小便池上签名,不是任何人重做一只包装箱,它们就能被艺术体制接受,进而成为艺术作品。显然,杜尚和沃霍尔的艺术家身份,在其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然而,杜尚和沃霍尔的艺术家身份的获得,本身又与艺术体制有关。由此可见,杜尚和沃霍尔跟艺术史中的艺术家一样,都经历了接受和挑战艺术边界的过程,在他们之后形成的或者正在形成的当代艺术的某种范式,也可以被认为是新的边界的产生。总之,在我看来,任何由艺术内部的挑战,都不可能将艺术边界彻底消除,因为这种挑战的力量本身,就源于艺术边界的维持。如果艺术没有边界,杜尚和沃霍尔就不能拥有艺术家的身份,他们的挑战就自动失去效力。
三、技术的外部挑战
对艺术边界的真正挑战,不是来自艺术内部,而是来自艺术外部,尤其是来自新兴技术的挑战。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到机械复制技术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本雅明注意到,机械复制技术会使手工时代的艺术作品失去“灵光”(aura)。手工时代的艺术作品的“灵光”,建立在作品的唯一性的基础上。使用机械复制技术制作出来的艺术作品,不再具有唯一性,因而不再具有让人膜拜的“灵光”。失去“膜拜价值”(cult value)的机械复制艺术,尽管不再能够发挥宗教仪式的作用,却因为具有“展示价值”(exhibition value)而可以发挥政治宣传的作用。由此可见,本雅明本并没有一味贬低机械复制艺术。⑩
与本雅明不同,阿多诺(Theodor Adorno)看到了机械复制艺术中的标准化或者“同一性”(identity)在获取最大利润的同时对消费者的控制。纳粹德国造成的灾难,让阿多诺对集体盲从尤其警惕。在阿多诺看来,只有体现个体性或者“非同一性”(non-identity)现代主义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这种真正的艺术具有将人从标准化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作用。机械复制艺术只是文化工业产品,它们不仅没有解放功能,相反它们的低级趣味造成消费者的逆来顺受,最终成了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的帮凶。(11)阿多诺的理论激发了20世纪后半期前卫艺术与通俗艺术或者大众艺术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前卫艺术被视为高级艺术或者真正艺术,通俗艺术被视为文化工业产品或者低级艺术。如果通俗艺术或大众艺术能够发动对前卫艺术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文化产品对艺术边界的挑战,是商品对艺术品的挑战。
尽管古德曼(Nelson Goodman)是个精英艺术的捍卫者,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却可以用来辩护大众艺术。古德曼发现,不同的艺术作品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地位,艺术作品是否可以被机械复制,与它们体现的趣味无关,与它们所属的类型有关。单数艺术是不能复制的艺术,复数艺术是可以复制的艺术。绘画是单数艺术,有原作与赝品的区别。音乐是复数艺术,没有原作与赝品的区别。因此,音乐适合机械复制,无论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现代音乐还是实验音乐,都适合录制。文学也是如此,无论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都适合印刷。录制的音乐、印刷的小说,它们之间并没有原作与赝品的区别,或者这种区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绘画则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复制。不管是机械复制如印刷,还是手工复制如临摹,都只能是生产赝品。(12)从古德曼的角度来看,阿多诺对于机械复制艺术必定低级趣味的指控,就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机械复制跟艺术趣味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可以将通俗艺术(popular art)与大众艺术(mass art)区别开来。通俗艺术指趣味较低的艺术,与高雅艺术(high art)或精英艺术(elite art)相对。大众艺术指可以经由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艺术。事实上,卡罗尔(Noёl Carroll)已经很好地将“通俗艺术”与“大众艺术”区别开来:通俗艺术是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术语,在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都可以发现通俗艺术。但是,大众艺术则不同,它“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性,它只是在现代、工业和大众社会的语境中出现的艺术,而且是专门为这种社会的消费所设计的艺术,就像实际情况那样,为了将艺术传递给巨量消费人群,它采用了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力,即大众传媒技术。”(13)根据卡罗尔的区分,只有采用大众传媒技术的艺术,才称得上是大众艺术。只有人类进入机械复制技术时代之后,才有大众艺术。由于能否被机械复制,与艺术趣味无关,与艺术类型有关,因此大众艺术不必是低级趣味的艺术。但是,由于卡罗尔将大众艺术视为通俗艺术的一个子类,他心目中的大众艺术就是采用大众传媒技术的通俗艺术。
正是在这里,我与卡罗尔产生了分歧。在我看来,就大众传媒技术本身来说,它并不会在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之间做出选择。同样是电影,既可以是趣味较低的商业片,也可以是趣味较高的文艺片。同样是唱片,既可以是趣味较低的流行音乐,也可以是趣味较高的古典音乐。同样是书本,既可以是趣味较低的通俗小说,也可以趣味较高的先锋诗歌。只要能够批量生产和传播的艺术,就都是大众艺术。由此可见,大众艺术的出现,将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之间的传统鸿沟填平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即使像绘画这样的单数艺术,也可以被批量生产和传播。传统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之间的区分,将让位给通过大众传媒平台传播的大众艺术与不通过大众传媒平台传播的小众艺术之间的区分。
大众传媒技术通过消解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边界,进而消解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在阿多诺看来,高级艺术或者真正艺术的敌人,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通俗艺术作品。当大众传媒技术将高级艺术作品与通俗艺术作品都做了同样的信息化处理之后,就从本体论上消解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它们都成了可以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就同为信息来说,它们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不仅如此,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信息化了。在信息领域,不仅高级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区别被消解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也不再存在。如果我们还愿意使用艺术这个概念的话,在信息领域,全部事物都可以称得上是“大众艺术”。
信息技术对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的消解,与杜尚和沃霍尔等前卫艺术家的作为不同。前卫艺术家的消解仍然是艺术界内部的事务,但是信息技术的消解则是艺术界外部的事务。将包括精英艺术作品和通俗艺术作品在内的所有事物数据化的,不是艺术家,而是工程师。如果说前卫艺术家在消解艺术边界时尚需借助艺术身份的力量方可有效,工程师就无需借助艺术身份的力量,工程师对于艺术边界的消解,是从外部进行的,从而也是前所未有地彻底的。
四、艺术边界的复得
信息技术将彻底摧毁艺术品拜物教,艺术品将不再为少数人独占。例如,谷歌艺术计划(Google At Project)正在将各大博物馆珍藏的艺术品变成人人可以共享的大数据。杜尚和沃霍尔等前卫艺术家是通过将寻常物变成艺术品而消解艺术的边界,谷歌工程师从相反的方向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即通过将艺术品变成寻常物而消解了艺术的边界。前卫艺术家与工程师的双重作用,将导致艺术边界的彻底消失。
但是,艺术边界的消失,只是意味着我们无法将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区别开来,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将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艺术品并不是我们替艺术划界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艺术家替艺术划界。事实上,在艺术品拜物教出现之前,艺术家是区分艺术与非艺术的主要指标。正如贡布里希指出的那样,“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14)尽管我们今天见到的艺术史多以作品为中心,但是贡布里希却告诉我们其实艺术家才是艺术界的核心。事实上,在以作品风格作为艺术史叙事基本线索之前,中西方有不少以作者为线索的艺术史叙事。例如,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艺苑名人传》,差不多都是以艺术家为中心的艺术史叙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前现代的艺术史叙事。今天从艺术品回到艺术家,实际上是艺术家不断挑战艺术边界的结果。我们今天强调从艺术品转移到艺术家来划分艺术边界,具有的意义完全不同。对此,我在《也许艺术家比艺术品更重要》一文中做了初步阐述。
任何一种行为都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行为的对象,一方面是行为的主体。艺术行为既会影响它的对象即艺术品,也会影响到它的主体即艺术家。艺术原创的结果是艺术品和艺术家,艺术复制的结果是复制品和机器或机器般的复制者。我们可以从传统美学和当代身心关系理论中找到许多理论资源来支持这种看法。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无法从对象的角度区分艺术品与复制品,但是如果艺术家与机器或者机器般的复制者之间的区别仍然存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就亦然存在。由此,给艺术划界的角度就从对象转移到了主体,艺术家成了识别艺术与非艺术的关键。从我的初步研究来看,“赝品制作者的人格是分裂的、不生动的、无风格的,而原创艺术家的人格是完整的、生动的、有风格的。因为赝品制作只是一种局部的、细节的模仿,制作活动不是一个有机整体,制作者的心灵不能灌注到他的活动之中。这样的活动是一种分裂的、由不同的局部或细节拼凑起来的,它必然会影响到心灵的统一性,将心灵分割成为无数的碎片。”(15)
由此,我们有了新的艺术边界,不是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的边界,而是艺术家与非艺术家之间的边界。要识别这种新的边界,显然不只是转移视角那么简单,这实际上是从艺术鉴赏到人物品藻的系统转换,除了视角的转移,还需要相应的词汇、观点和方法。传统的人物评鉴和当代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可以提供某些资源,但也需要一个新的平台,将现有资源整合起来进而发展出新的词汇、观点和方法,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个新的平台称之为新人类学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识别艺术家,有可能为失去边界的艺术重新发现边界。
①关于家族相似理论,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5—51页。
②Morris Weitz,“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15,No.1(Sep,1956),p.32。
③在《艺术与错觉》一书中,贡布里希多次引用波普尔。他承认,波普尔在科学活动历史中发现的猜想与反驳的公式,“非常适用于艺术中的视觉发现史。事实上,我们总结出图式和矫正的公式,所说明的正是这个程序。你必须有一个出发点,一个进行比较的标准,然后才能开始那最终体现在完成的物像之中的制作、匹配、再制作的过程。艺术家不能从乱涂乱画入手,但是他可以批评前人。”(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388页。)
④在18世纪艺术与科学分道扬镳的时候,欧洲思想家们就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比如,杜博斯(Abbé Dubos)就明确认识到艺术有赖于天才,科学有赖于知识的累积。有关考察和分析,见Paul O.Kristeller,“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Ⅱ),”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3,No.1(Jan。,1952),pp.18-19。
⑤关于后历史艺术的界定和分析,见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王春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⑥Arthur Danto,“The Artworl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61,No.19(Oct,1964),p.579。
⑦关于丹托艺术哲学的概括性描述,见David Novitz,“Arthur Danto,” in David Cooper(ed。),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Oxford,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1997),pp.105-106。
⑧George Dickie,Art and the Aesthetic: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34; George Dickie,The Art Circle(New York:Haven,1984),pp.80-82。
⑨关于迪基艺术哲学的概括性描述,见Noёl Carroll,“George Dickie,” in David Cooper(ed。),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pp.122-124。
⑩本雅明的相关思想,见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
(11)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批判,见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2页。
(12)古德曼:《艺术的语言》,彭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章。
(13)Noёl Carroll,“The Ontology of Mass Art,”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55,No.2(1997),p.188。
(14)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范景中、林夕译,天津:天津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5)彭锋:《也许艺术家比艺术品更重要》,《艺术评论》2004年第4期,第8页。

![大道至简,简而不凡——田生云书画艺术鉴赏[图文] 大道至简,简而不凡——田生云书画艺术鉴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yavv2qbh2i.webp)
![中国当代小虾王曹敏——灵动传神 清秀优雅[图文] 中国当代小虾王曹敏——灵动传神 清秀优雅[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vadnoi1i2r.webp)
![呈现近现代工美审美风尚[图文] 呈现近现代工美审美风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vm1m51c3yd.webp)
![浅谈张功慤画面中马的形象[图文] 浅谈张功慤画面中马的形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jhfws1uybg.webp)
![记最美夏季荷塘写生(生宣)——画家李芳林[图文] 记最美夏季荷塘写生(生宣)——画家李芳林[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y3h4sj0qod.webp)
![唐代鎏金摩羯纹多曲银碗跟丝绸之路有何关系[图文] 唐代鎏金摩羯纹多曲银碗跟丝绸之路有何关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30k5ar5z51.webp)
![化腐朽为神奇的赫普沃斯雕塑奖进行时[图文] 化腐朽为神奇的赫普沃斯雕塑奖进行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4x43jgdfsu.webp)
![人工智能之于美术高考[图文] 人工智能之于美术高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1soltk3hwc.webp)
![这处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图文] 这处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nvyfun0e2s.webp)
![当代著名画家胡金刚作品欣赏[图文] 当代著名画家胡金刚作品欣赏[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uorfrg4zez.webp)
![自然—自由:王清州彩墨艺术的穿行与回望[图文] 自然—自由:王清州彩墨艺术的穿行与回望[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c1vpbc0j4t.webp)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展中展——美好生活 奔现未来[图文]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展中展——美好生活 奔现未来[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rujxg5tjldl.webp)

![中国会不会也像日本一样面临艺术市场大崩盘[图文] 中国会不会也像日本一样面临艺术市场大崩盘[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hme2t1lss5.webp)
![闪光灯拍照 文物会受伤[图文] 闪光灯拍照 文物会受伤[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tu3vrmxfym.webp)
![在森美术馆读盐田千春[图文] 在森美术馆读盐田千春[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eyxlprg5hl.webp)
![仙鹤是一品鸟古时常入画[图文] 仙鹤是一品鸟古时常入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afa0wbz0vcj.webp)
![张大千艺术市场解析[图文] 张大千艺术市场解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y3abdhnp51.webp)
![荣宝斋(上海)拍品赏析:徐悲鸿《双骏图》[图文] 荣宝斋(上海)拍品赏析:徐悲鸿《双骏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vuzx5jpyxq.webp)
![井上豪:西域壁画中的粉本与使用方法[图文] 井上豪:西域壁画中的粉本与使用方法[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1rz3acb1hn.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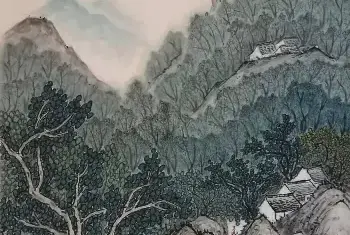
![六十名驹 华夏图腾 ·赵文元研究三[图文] 六十名驹 华夏图腾 ·赵文元研究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wrm55x4hsq.webp)

![陈振,以写意笔墨为精神气韵,把热带雨林花鸟描写的生动而传神,自由而生机[图文] 陈振,以写意笔墨为精神气韵,把热带雨林花鸟描写的生动而传神,自由而生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xmokwpvj2l.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