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 马国湘 整理 何玉新
马国湘是上海一位民营企业家,二十多年来,他从推土机下抢救保护了上千栋古民居,抢救移植了三十多万棵濒危大树。2012年,他在安徽蚌埠投资建设古民居博览园,为这些古民居和古树安了家。马国湘说:“粗略算了一下,抢救大树我们花费了数亿元,我付出的是时间和金钱,换来的却是无价的东西。万物都是有生命的,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和敬畏,这种生命价值、文化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今年年初,他在深圳登上了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和凤凰卫视举办的“2017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的领奖台,与现场观众分享他的心得和感受,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如果我不去救那些老房子
恐怕它们就会被推土机摧毁
二十多年来,我们从推土机下抢救保护的古民居超过一千栋,其中最早的是明代建筑。一栋古建筑就是一段历史遗存,是文明和文化最直观的体现,每一面粉墙、每一片黛瓦,都藏着一个故事。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言,中国古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了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
保护古建筑,起初只是我个人的收藏行为,以此表达我对祖辈的敬畏之情。我出生在上海浦东农村,那时候炊烟袅袅、小河潺潺的村落,让我对农耕社会村落邻里的生活念念不忘。军旅生涯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记得部队去雁荡山搞绿化建设,看到周边那些依山傍水的古村,我觉得太美了,好像我记忆中来过这里一样,看一眼就爱上了。后来我才想明白,可能那一刻,我基因里对古村落的爱就这么被激发了。
二十多年前,人们对古民居还没有太多概念,甚至还在破坏它的时候,我在旧货市场收了我人生中第一件古建筑构件,由此渐渐延伸到收藏整幢民居。后来,有些施工单位比较有意识,和我联系,希望我去收购,以求保住老房子。曾经有个地方联系我们,有35栋古建筑要打包卖给我们。我们过去一看,除了那35栋,边上还有一些民国时造的房子,也非常好,于是又从推土机下救出了4栋。然而有些地方的人,拆起自己的家园来毫不手软,比如在福建某地,虽然那里的人早早就富裕起来,但却要把整个村庄的古民居打包卖给我们,都是红砖大厝,这是中国有代表性的传统民居建筑,双曲线屋面,雕花封壁红砖,精美的门面石刻,屋脊檐口花饰,色彩鲜艳,喜庆吉祥。他们自己的家园、自己家族的历史,却要毫不留情地卖掉,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如果我不去救,那些老房子恐怕就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了。
每次看到这些老房子,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种种场景:当初建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住进去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现在很多人热衷于收藏房子里的物件,比如瓷器、铜器、字画,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些老房子本身是由那个年代优秀的工匠们修建的,比如雕工精美的门窗花板,要是放在一张纸上,不就是明清时期的字画吗?
我平时工作太忙,往往没有太多时间实地去考察和判断哪些建筑要收藏、哪些可以放弃,只能通过专人给我看的视频和照片来做决定,而最终放弃的那些,往往是一个大宅子里只剩下些快要腐烂的木头,一点儿故事都没有。
2016年,辽宁省凌源市一处有300年历史的古宅即将被拆。我去了当地,有人问我:“这些房子破破烂烂的,没有什么价值,您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说:“这是历史,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这个老宅子的主人也在东奔西走,希望能够把它保存下来,知道保存无望时,不禁黯然神伤,但听说我要把这座老宅子整体抢救、整体异地复建时,他老泪纵横,告诉我待到建好之日,一定要去看看老祖宗留下的宅院。
古民居体现了民间工艺
也传承了不同时代的家风
在地产行业,我应该是起步比较早的,只是我“玩物丧志”,一听说什么地方有古建筑要被拆了,我就把生意撂在一边,先去救古宅。我的想法很单纯:“只要是爷爷奶奶留下来的东西,无论好坏美丑,都有他们生活的印记,都有儿时的记忆,丢弃不得,所以我就竭尽所能去抢救它。”
很多古建筑的房梁烂掉了,很多门窗雕花被弄残缺了,需要尽快修复。所以我组建了一支一百多人的工人队伍,先从各地把古民居收购过来,拆下来运到仓库,修复以后再运到现场复建。现在从事古建筑修整的老师傅越来越少,以前盖房子的叫“大木工”,做家具的叫“小木工”,他们“各有一套”的师徒相授和家族传授方式,使得这门技艺始终没有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专业分工,渐有失传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古建筑维护、修复与管理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样至关重要。
广为人知的一些名人故居,可能早就被当地政府围拢起来做了旅游景点,但许多散落在各地的古民居,并非都能像皖南西递宏村般幸运,被成片成建制地保护起来。众多普通民居处在被保护与被放弃的中间地带,尽管民居未必如声名显赫的达官贵人府邸那般幽深精美,但同样有很多体现时代特征和当时民间高超工艺水平的精品,被拆下来当作柴烧,实在可惜。政府部门可能无法对每一栋古民居都实行有效保护,因此民间进行抢救性收藏、重建,是另一条保护之路。
为了给这些古民居寻找新时代的“灵魂”,我不断四处求教,找到冯骥才、阮仪三等古村落保护专家,也找到王蒙、张艺谋等文化名人,向他们讨教如何让这些古建筑与时代发生关系,注入当代元素。很多专家一直持有“古建筑要原地保护”的观点,但现实让他们的观点也有所转变,认可在不具备原地保护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易地保护。
将古民居仅仅进行现代化改建,成为餐厅、酒店,太过庸常,我们请来了改建团队,动用建筑师们的智慧,在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畔打造了一个古建筑群落,让这些古民居在历史灰烬中得到重生,在古宅里配上古树、古石,我的收藏就这样由此及彼地延伸开来了。
人们称我是“国内古建筑收藏第一人”,这么叫我,我既感荣耀也感无奈,因为这意味着古建筑的流逝,有流逝才会有收藏。古建筑保护是个紧迫的问题,一提到这个问题,我的心就压得紧紧的,因为老房子越来越少。我做的其实也蛮无奈的,抢救也是一种凝固,凝固的是国家记忆。我总在想,作为企业家,赚了钱,如何才能回报社会?我希望在艺术的范畴下挽救建筑,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些古民居能够再活六百年。人活不过一块砖、一面墙,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争分夺秒为这些古民居和大树安个家园,通过老房子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发生在老房子里的每个家庭的家风、家训、家教,传承我们的文化。
二十多年花费数亿元
保护了三十多万棵濒危大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除了古民居之外,一些古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它们就像一个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亟待收留、养育。二十多年来,我花费数亿元抢救保护了三十多万棵濒危大树,仔细想想,这些大树在每一个时代里的每一分钟,都为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人们提供着养分,提供了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我们有义务保护它们。
为抢救浙江某工地上一棵树龄在500年以上、外表已经枯萎的紫薇树,我们把大树连根移起,运到培育基地后,像医护人员救治病重的患者一样,首先给这棵树彻彻底底“洗了个澡”──用我们自己研制的杀虫剂一遍又一遍往树根、树枝上淋喷杀虫,调制“营养品”注入树根。栽种时,我们把这棵树浅埋轻培,保证树根氧气充足,工人们每天早、中、晚都要用高压喷枪喷一次水,不仅浇灌根部,而且树干、树枝上也要喷更多的水,这样有利于保持树干的湿润。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辛苦抚育,这棵紫薇树长出新芽,还开出了藕荷色、粉色、淡黄色三种紫薇花。
树是有灵性的,你用真心培育它,它就会用美丽报答你。如果哪项工程在施工时遇到大树,千万不要锯掉,要连根移出来,一定要把它抢救活。
三峡水库合拢前,有一批三峡移民被安置到上海市崇明区,崇明一位负责移民工作的领导告诉我,移民们说家乡有好多树移不走,马上要被淹了,特别心疼。我马上抽调了一百多号人,带着大型挖土机和吊车赶赴现场。到了那儿一看,那么多那么好的树,很多都活了数百年、上千年,却要在几个月后被淹没。我们开着车子一处处去看,看到大树就停下来挖,车子成了我们流动的旅馆,我几乎是住在车子里。我们从那年的12月份一直挖到第二年夏天,因为天热了,挖出来也种不活了,我们才停下来。这次我们一共抢救了一万多棵大树,最老的一棵罗汉松有1200多年树龄,很多大树都在百年以上。越大的树越难挖、越难吊,85%的树都栽活了。
这些年来,我们陆续地把大树捐赠出去。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里的大树园,方圆2600亩土地上的三万多棵树,都是我们捐的,不算树的钱,光施工就投入了数亿元。当时的大树园是整个公园里最破落的地方,地势低洼,而现在,每个周末都有近两万名游客去游玩,都说漂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些大树活了,安放在首都。我的心安了,这就是回报,一种最本质的回报。

![美国艺术家的牛肉干总统肖像画[图文] 美国艺术家的牛肉干总统肖像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ntx2xpt2xn.webp)
![富豪选妻只是一场行为艺术[图文] 富豪选妻只是一场行为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4l0fchmy3k.webp)
![奇台至唐山快递玉石中途被开箱 收货人拒收[图文] 奇台至唐山快递玉石中途被开箱 收货人拒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s30olrq5cun.webp)
![科幻世界中的建筑[图文] 科幻世界中的建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vjfmel1ncmc.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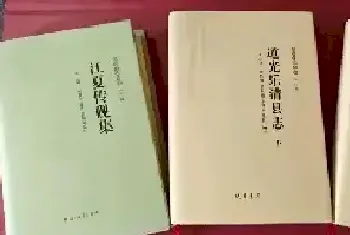
![探秘:走进真正的绿松石之乡[图文] 探秘:走进真正的绿松石之乡[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3zmlv5002ht.webp)
![明星同款链上实物,疯狂的数字藏品终于有了新样子![图文] 明星同款链上实物,疯狂的数字藏品终于有了新样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jddoln3xail.webp)
![沈阳故宫百姓最喜爱文物Top3[图文] 沈阳故宫百姓最喜爱文物Top3[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op4o5fhpow.webp)
![山水画家王晓作品受邀入编《荣宝斋》2015拾壹月刊[图文] 山水画家王晓作品受邀入编《荣宝斋》2015拾壹月刊[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zolukh54zpt.webp)
![老旧汽车新命运:艺术家巧手焊接废旧部件变雕塑[图文] 老旧汽车新命运:艺术家巧手焊接废旧部件变雕塑[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k22x0ys3j05.webp)
![唐代海兽葡萄镜上的“舶来品”[图文] 唐代海兽葡萄镜上的“舶来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4nsn4zhjig.webp)
![媒体曝100张全新连号一元纸币已被炒到120元[图文] 媒体曝100张全新连号一元纸币已被炒到120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kjvzq2rdrk.webp)
![特朗普大砍文化艺术补助 艺术家幽默回击[图文] 特朗普大砍文化艺术补助 艺术家幽默回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p5x5shu50m.webp)
![放飞梦想——慧雨宸教育第一届书画展暨朝阳校区开业[图文] 放飞梦想——慧雨宸教育第一届书画展暨朝阳校区开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lmwh5l4wmd.webp)
![黄永玉自喻晚上八九点的月亮 为什么不是50岁[图文] 黄永玉自喻晚上八九点的月亮 为什么不是50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r2az4qjkdz.webp)
![黄永玉配合一岁小孩画国画 无心之笔顿时有故事[图文] 黄永玉配合一岁小孩画国画 无心之笔顿时有故事[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mgcndtjcl5.webp)
![北京书画家砍女医生18刀被诉故意杀人获刑15年[图文] 北京书画家砍女医生18刀被诉故意杀人获刑15年[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jmt0p23rxt.webp)
![张之洞也曾以润笔受贿[图文] 张之洞也曾以润笔受贿[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xgaqv44dcpy.webp)
![古老纸片上暗示耶稣可能结过婚[图文] 古老纸片上暗示耶稣可能结过婚[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1i1r2uvtwe.webp)
![湖北行为艺术家巴黎悬空 所拍照片爆红网络[图文] 湖北行为艺术家巴黎悬空 所拍照片爆红网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myd0z3mahuq.webp)
![再说丰梦忍和丰子恺润格[图文] 再说丰梦忍和丰子恺润格[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lgr4qbspmp.webp)
![《蒂凡尼早餐》房间卖585万美元[图文] 《蒂凡尼早餐》房间卖585万美元[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1j00po1w43.webp)
![拍卖史上最血腥的画3.5万英镑成交[图文] 拍卖史上最血腥的画3.5万英镑成交[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uu0sbcen2re.webp)
![英国网上发布4000页牛顿手稿[图文] 英国网上发布4000页牛顿手稿[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oq14urlzcb.webp)
![藏友收藏两块奇石疑似化石[图文] 藏友收藏两块奇石疑似化石[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24ulwj00axe.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