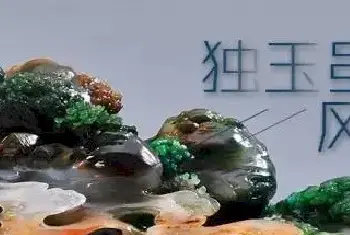史前文明是民族国家的种族身份、民族文化的出生证明,也是文化荣耀感的来源。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表明中华文明在新石器时代的大大向前延展得到世界认可。
其中,良渚玉器作为良渚文明的杰出代表,是我国先民制作生产工具时撞见特殊石材后的艺术加工,坚韧、美丽、有光泽。审美之心既出,中华艺术史从此奠定格局。
良渚的玉器由外及内,启蒙了儒家文化的人格审美,可谓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有序的聚落形态,发达的艺术审美,构成了良渚社会最重要的两大支撑,叙说着中华文明在新石器时代的美好。
考古发现环太湖地区大约有35个大聚落群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也有“睿哲文明”语句,取光明、有文采之意。现代汉语“文明”一词,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文化昌盛状态,与“野蛮”“未开化”“蒙昧”相对。
《文明史》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法国年鉴学派灵魂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布罗代尔指出,文明是一个地域范围,要有一定的地域空间,包括气候,动植物种类,农牧业,衣食住行方式等;文明可以等同于社会,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
同时,文明就是经济。每个社会、每种文明都有着自己的经济、技术、生物和人口情况,物质和生物的状况常常决定着文明的命运、人口的升降,经济和技术的兴衰等则往往影响着文化和社会结构。
此外,文明还包含着思维方式,也就是集体心理。每个时代,固定的世界观与心智掌握着社会群众、支配着社会态度、领导它的选择、确定它的偏好、决定它的行动。更进一步,布罗代尔总结说:“文明事实上有两层意义,它指的是精神的和物质的价值。”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也有类例思考: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我们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
我们知道,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秋。原西湖博物馆工作人员施昕更在良渚镇荀山及棋盘坟一带进行发掘,并写出了《良渚》报告。1959年,考古学家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概念。主要发掘的遗址范围,除荀山之外,还有吴家埠、反山等处。今天的研究显示,良渚文明广泛分布于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北至苏北、南至宁绍平原、西到江苏宁镇、东达舟山群岛的广大地区,距今约7000年至4000年。
古老的良渚先民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经考古发掘,现今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早期文明产物,如石器、陶器、玉器及稻谷等农产品。良渚时期,环太湖地区已有发达的农业、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尤其是开创了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先河。同时,考古人员还发现被称为“中国式土筑金字塔”的高台墓地。其间,有了原始文字的萌芽,出现集体人殉,出现神权、军权、财富集中的迹象,是中国文明时代的体现。
良渚考古的大量新发现,对揭示家庭私有制形成、国家起源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它进一步表明,中华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演进的脉络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原,而是显现多区域、多系统、多源头的特点。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就明确提出“区域类型”的考古理论,将上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系;以山东为中心的东部区系;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部区系。
良渚文化恰恰处于环太湖中心地带核心区,具有独特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它与各区系内其他分支有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又相互影响、交相辉映。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家伦福儒高度认同良渚文化的意义。他认为,通常人们认为中国的文明略晚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后两个文明的起源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的文明仅仅在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才开始。这种说法仅以文字作为衡量,大大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丰富性。
我国考古学者推论,良渚文化的聚落和聚落群及其代表的各层社会组织,在内部和不同层级之间都有相当程度的分化。良渚文化的一级墓地至五级墓地,每个级别墓地内部的墓葬之间都有差别,“首领主导式”布局非常明显。
除了社会分化外,良渚文化的社会竞争也比较激烈。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发生战争,从而导致高等级聚落的废弃和兴建。从良渚文化的宏观聚落形态来看,高等级聚落控制的大聚落群,即良渚文化中的最高政体,在环太湖地区大约有35个。
以以色列社会和埃及早期社会为例,古代以色列社会以游牧生活为基础,经历了“家庭一村落一城市”的转变,以政治和经济手段为武力条件,以精神文化产品形成区域内部的共同认识。其中,尤以宗教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并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酋邦和宗族国家形式中交织发展,最终形成了统一的社会霸权。而在埃及早期社会,法老的权威达到顶峰。个人独裁的过早出现,使得权力和神性彼此交织。
良渚文化较早地发展出了复杂、有序的稻作农业生活。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良渚社会主要运用“共识”的手段,并主要以玉器所代表的宗教为表现形式来维护社会稳定。
东西方史前文明在纹饰创作上有相似之处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玉,石之美者,有五德”。就自然材质属性而言,玉是一种特殊的石材,坚韧、美丽、有光泽。视觉上,玉石色泽丰富多变,通透清澈有光泽;听觉上,敲击时声音脆甜、悦耳;触觉上,温润清凉。先民用“玉”字给这种石头进行新的登记,审美气息跃然于纸上。
目前,良渚遗址出土的多为玉琮。在良渚文化西南边的广东石峡文化以及江苏北部的花厅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存中也出土过玉琮,但数量等级与良渚文化不能相提并论。
良渚文化的玉琮,主体纹饰外多饰以卷云纹、弦纹、鸟纹等。研究认为,良渚早期遗址出土的玉琮纹饰简单,而后慢慢烦琐,到中后期逐渐简化,标志着神权与皇权的分离。纹饰主要分为六型,即兽面纹型、神人纹型、“异眼”神人兽面纹型、“同眼”神人兽面纹型、简化神兽纹型和神人兽面纹+鸟纹型。
2000年10月至2001年8月,186件玛雅文物在中国巡展,有一件太阳神雕塑吸引了人们眼球。它出土于墨西哥坎佩切州的琼乌武夫,高67厘米、宽79厘米、厚46厘米,是一个建筑构件。螺旋形的眼睛,翅膀形的羽毛披饰,表明它是太阳神的象征。其中,双手僵直拄在腿上的这种姿势以及羽毛饰物,与良渚玉琮纹饰中神人兽面纹极其相似。
艺术无国界。东西方史前文明在纹饰的创作上,还是有诸多相似之处。
其一,夸张的描绘。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大多是管钻眼或刻有椭圆形眼角,眼角内或填刻纹饰,凸鼻,阔嘴,嘴内或两对獠牙外露。美洲人印第安人的图腾面具也大都是重圈圆眼,且有小三角形的眼角,宽鼻,阔嘴,嘴内两排十八颗牙齿。夸张手法创造能营造一种神秘变幻的气氛,使人更易产生敬畏之心。
其二,神、人与兽混合作为创作的题材。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便是神人与兽面的组合。
其三,敬畏太阳。良渚文化玉琮上神人兽面纹上的眼睛,大都以管钻的手法来突出眼睛的部分,就是对神(太阳)的崇拜和敬畏。太阳神在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中也有所体现。
可见,世界各地的先民们在艺术思维和创作手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不同文明发生发展之时,所处地域不同,种植作物差异很大,但由于史前文明所处时代生产力相对较低,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却彼此相通。
于是,在神性和艺术价值的双重作用下,良渚玉器承载了多重文化内涵,首要的是祭祀。原始社会进行巫术活动,巫觋具备沟通神灵的能力,沟通所用的重要器物的载体就是玉器。于是,玉器有了新的身份——“玉神器”。
国家出现后,“玉神器”的身份转变成为“王玉”,常被当作“礼器”用于帝王的祭祀活动。《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可见,玉器在古代祭祀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玉器种类丰富繁多。
它还是权力、等级、财富的象征。原始社会墓葬中,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尊卑贵贱通常可从随葬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来予以识别。国家出现后,对玉器的实用礼仪和配器进行严格规定,并写入典章作为书面判断,为的就是维护王朝礼制、避免混淆和逾越阶级等级。
在艺术上,玉作为审美装饰,很早就受到人们的赏爱。在中国古代文化里,“玉”字是形容美好的修饰词。《礼记》里提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清俞樾说:“古人之词,凡甚美者则以玉言之。《尚书》之‘玉食’,《礼记》之‘玉女’,《仪礼》之‘玉帛’,皆是也。”
《国风》有言:“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于是,子贡问孔子:“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寡而珉之多与?”孔子明确回答: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
在孔子看来,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拼瑜,瑜不拼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从子贡与孔子的这番对话可以看到,玉器的审美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道德标准,不仅是“君子佩玉”,而且是“君子如玉”。
总之,良渚的玉器由外及内,启蒙了儒家文化的人格审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