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旷神怡的感受,来自于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画山水画不走进大山中去写生,是很难把握住山水的灵魂的。在中国画发展历程中,有的人们对笔墨的见解和标准,有时还是浮在表面的。然而,在这个表现的背后,是画家对表现对象抒发来自内心的情绪。单纯在画室里画临摹与到大自然中写生,不是一回事,王中年先生说过“临摹只是给写生打基础的,写生是给创作而服务的”。恩师雷显平先生曾对我说“要多观察大自然、多画、多读、多背、多记,你一定要走写生路”,过去我只是在画室里钻研临摹,第一次外出写生感到有些无从下手,因为脑袋里全是古人的技法,根本无法运用到实景之中。于我而言,那一阶段的写生是痛苦而挣扎的。面对自然,眼见为实。时间久了,才沉下心来从自然这一实相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领悟到其中的辩证关系,若光练笔墨,不直接对景写生,实在是体会不到这些道理的。绘画时对丘壑、树木、山径、房屋造型上的把握,以及对气候、季节等的体验,若不深入实际中去,感觉从何而来? 第一次的外出写生使我体悟到了写生的重要性。那时,虽然写生还比较笨拙,却也认认真真的画了一些,多少也拉近了写生与传统技法的一点距离。
对于绘画,我是偏向于色彩学和透视学,我的老师杨玉象先生说过“画山水画不光要结合大自然还得一定要符合大自然的生长规律”,我把第一次写生作为今后绘画努力的方向。自那以后,我尝试顺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不断深入对自然实景的提炼和自己内心对此的体悟。曾读到李可染先生的国画语录,说到了“对景创作”,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也曾听陆俨少先生谈他绘画的起因及其独到的观察方法,我均视为高人真言。我都把这些作为座右铭和我对艺术创作的行为准则。以后每一次写生,都力求强化空间和笔墨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写生中,才可离固有的观念稍远一点。写生多了,已学成的技法会不知不觉的又回到笔下,此时的技法已然成为本能,个人风格也就自然显现。尽管这个过程可能会用去大量的精力,也因为如此,在以后的创作中才会是自在和快乐的。

写生是快乐的,无论生活条件多么差,只要遇到好的景致,兴奋是必然的。带着画夹去写生,不走寻常路,漫步深山野水。没有人为痕迹的自然之风景是最入画的。不加修饰、依地形而建的建筑,也是最入画的。千岩万壑,即便是极简极平常的景色,融入气候,融入人情,定会意趣无尽。蜻蜓点水式的写生往往是浮光掠影。那时我就在想,等自己有时间了,一定要在某个写生点待上一阵。从当地的风土人情开始,全方位地对描绘对象注入自己的观察和情感。透过外在的形态,从精神内在本质上去把握描绘一座山或是一个村落。写生不单是对景描摹,而是从中获得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中国山水画的写生,让我着迷的不是技法,因为这不是山水画的本质。

每次写生归来,画面上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从形式到色彩,从肌理到语言,从技术到表现,还有画面构成及绘画中精神层面的感悟和提升都不断激起我对绘画的热情。从我开始拿起画笔以来,我感觉像一个独自远行的少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开始画不好却也执着。
绘画直指人性,他是人情感和状态的自然流露。一幅画,体验出你的学识,品格,胸怀。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奇妙的世界,面对大山,你若有情,它便有意,你若无私,它便宽广,你若豪迈,它便阳光。说到底,绘画不仅是视觉与自然碰撞的结果,更是心灵和意识形态借助客观物象在画面上的直观再观,它可澄清一个人被世事界缠绕的心,人性的美好和光辉在绘画中可以得到提高和升华。中国古人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及“天人合一”的艺术思想不仅需要我们借助“外师”去造化,我们的心灵也只有在不断的历练和感悟中才能回归到自己本性的精神家园。同一个“外师”,不同的“心源”,一千个画家就有一千张面孔和不同的画面精神,你想说什么,喊什么,爱什么,恨什么,表现什么都需在大自然的秩序中去寻找和发现,在不同的感悟和技术语言中去表达和再现。
大自然是上帝为我们创造的美丽家园,是一曲永无休止的赞歌,在我的作品中,我力图想构建的是:没有污染,没有战争,没有罪恶,没有贫富的世外桃源,那是我心中所祈祷的理想之国:山恋相依,水天一色,云雾飘渺,茅舍相依,鸡犬相闻,万物竞长,各显其类。我想是人已近中年,心有所指吧,亦或是画中的感觉映射了我的心灵?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要画下去。

![丰子恺:远功利 是艺术修养的一大效果[图文] 丰子恺:远功利 是艺术修养的一大效果[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p5eurryjbx.webp)
![傅抱石秋拍为何能二度破亿[图文] 傅抱石秋拍为何能二度破亿[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tpzcdsxw5au.webp)
![去年艺术品市场流拍率近六成:创历史新高[图文] 去年艺术品市场流拍率近六成:创历史新高[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oiudy01au1.webp)
![国泰民安 同贺祖国71华诞——画家李秀峰[图文] 国泰民安 同贺祖国71华诞——画家李秀峰[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q4kjqj4bjmp.webp)
![惠勒笔下的明艳色彩[图文] 惠勒笔下的明艳色彩[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fb4vx43q3qf.webp)
![一张罕见的齐白石20世纪40年代牵牛花作品[图文] 一张罕见的齐白石20世纪40年代牵牛花作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bttrinh0ln.webp)
![2020年艺术先锋人物:画家谈龙[图文] 2020年艺术先锋人物:画家谈龙[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edcew53vev1.webp)
![乔治·布什的画作:这是阿甘的艺术[图文] 乔治·布什的画作:这是阿甘的艺术[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4zqyxkywciy.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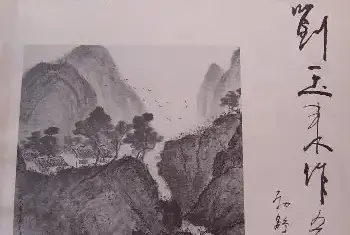
![青年书法家杨吉兵[图文] 青年书法家杨吉兵[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5z3fr4qphsy.webp)
![他的肖像艺术叱咤拍场 与毕加索平分秋色[图文] 他的肖像艺术叱咤拍场 与毕加索平分秋色[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qtsxvufhqi.webp)
![冷军临摹的俄罗斯油画《春潮》赏析[图文] 冷军临摹的俄罗斯油画《春潮》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wx5juvwbpih.webp)
![清代紫砂方葫芦壶赏析[图文] 清代紫砂方葫芦壶赏析[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13h44craafe.webp)
![了庐:董其昌的笔墨精神与抽象表现主义[图文] 了庐:董其昌的笔墨精神与抽象表现主义[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0o1ff3dzab.webp)
![浅谈30米巨幅明代绢本《丝绸之路大地图》[图文] 浅谈30米巨幅明代绢本《丝绸之路大地图》[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dvf2rziu4kw.webp)
![陈履生:博物馆是面镜子 创造和维护特色很重要[图文] 陈履生:博物馆是面镜子 创造和维护特色很重要[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gmnliuebg3w.webp)
![古壁画描绘盛唐贵妇的闲适生活[图文] 古壁画描绘盛唐贵妇的闲适生活[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lwaj0iih3ii.webp)
![一个自由艺术家 吉尔格楞[图文] 一个自由艺术家 吉尔格楞[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hivr1c0zecb.webp)
![齐鹏:生活与色彩的真相[图文] 齐鹏:生活与色彩的真相[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pk15syjszdp.webp)
![冯少协:油画写真千年古镇[图文] 冯少协:油画写真千年古镇[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0i0dftsimsn.webp)

![刘玉来:提高素养更上一层楼[图文] 刘玉来:提高素养更上一层楼[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ynutks51auq.webp)
![观物取象--翁道胜绘画艺术创作方式研究[图文] 观物取象--翁道胜绘画艺术创作方式研究[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iwxvd1s1cyb.webp)

![陈振,以写意笔墨为精神气韵,把热带雨林花鸟描写的生动而传神,自由而生机[图文] 陈振,以写意笔墨为精神气韵,把热带雨林花鸟描写的生动而传神,自由而生机[图文]](http://zuopin.meishuziliao.com/file/zuopin_img/nxmokwpvj2l.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