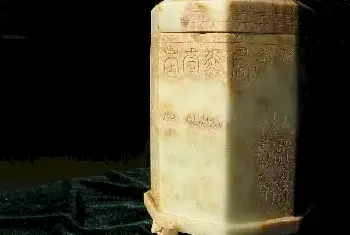五月燥热的下午,时有微风。邯郸路800号的小楼里,我们和几大箱仪器、密密麻麻的书籍资料一同挤在办公室里,听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王荣老师讲述他与文物的故事。
很多人对修文物的认识,来自于2016年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而对于文物与博物馆系的师生而言,《我在故宫修文物》中记录的文物修复工作,仅仅是冰山一角。
与玉结缘:千年磨砺,温润有方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副教授王荣老师,长期致力于硅酸盐和漆器文物的科技考古和保护研究,在复旦从事文博教学和研究的10年中,主持承担了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他是理科出身,选择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完全是兴趣使然。
“15年前,研究生导师了解情况后跟我说,你就学这个吧!我也没多想,就学了科技考古。”非常偶然地,王荣老师就这么开始了玉器方向的科技考古和保护研究,“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玉,它有很深的文化积淀。”
“你们会说,玉不就是个石头吗?在我眼里不是的。”王荣老师是爱玉之人,说起玉,他可谓是如数家珍,从《说文解字》的“玉,石之美者”到西方过去没有“玉”的说法,王荣老师都娓娓道来。“玉算得上是中西方文化最古老的分水岭了。”
2015年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附近发现了距今九千年、形状较为规整的玉器,这暗示着中国玉器的历史比我们想象中更为悠久。
而玉作为无机质文物,兼具有形价值与无形价值。保护有形的玉器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传承玉器背后的无形价值。
去年他在复旦倡议发起了首届古代玉器青年学术论坛,并在发言中说了这么一句话:“能去博物馆亲眼看一看文物,可以说是一生有幸;能亲手捧着它,则是二生有幸;能利用先进设备采集资料来深入地研究它,可以说是三生有幸了。”
学生时代的王荣老师一下子完成了从一生有幸到二生,乃至三生有幸的跳跃,不可谓不满足了。
推着箱子去考察:文物不会主动来复旦
由于科技考古和保护工作要进行大范围的实地考察,王荣老师当年学习时就要全国范围地跑,经常可以接触到第一手史料。因为研究玉器,也得时常在各大博物馆之间奔波。为了提升效率,多地的考察工作通常会被安排在一个时间段,强度较大。“学习文博要身体好,文物资源分散在全国各考古所和博物馆,要主动联系前往调研,文物不可能主动来复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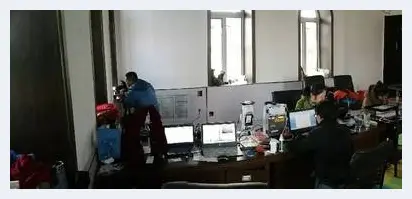
黑龙江饶河博物馆
办公桌前的六个神秘黑箱子装着考察必需的仪器,箱子尺寸适中,即使远程需要乘飞机时也无须托运,可以直接放在行李舱内,便于保证仪器安全。此外,为了外出节省体能,团队还会带个折叠手推车,把黑箱子一个个摞上去。“这个东西好,有学生累了我们就直接推着走;我累了他们也能推我走。”王荣老师开玩笑说。
在各省市实地考察的过程中,他看了许多,也学了许多。
从乌苏里江一路南下,王荣老师对沿途的玉器进行过一系列考察,发现各地均分布着不同程度损伤的玉器,表现在外部最明显的特征是变色。

集黄化和绿化于一身的出土玉戈(春秋)
一般情况下,变绿、变黑、变褐的玉器是由于游离的金属元素(如铁、铜、汞等)进入玉器内部。

出土黑化玉环(商代)
而白化是对玉器质地改变程度最大的情况,发生白化的玉器由于内部结构变得疏松,透明度下降,稍经触碰就会掉下层层粉末。普通白化时,玉器的纹饰会逐渐模糊;严重白化时,玉器会直接散成类似粉状的物质,原来的形状也不复存在,玉器实体的“消亡”是可以预见的。

严重白化玉环(战国)
万里长征:修复只是“第一步”
“如果要谈‘我在复旦修文物’的话,我想我做的第一件工作应该是修复性的,第二件则是预防性的。”
关于修复,王荣老师介绍了四种与玉器相关的方法。
第一种修复工作是针对有外覆物的玉器,一般用酒精即可擦除出土玉器的外附物质,当无法用酒精去除时,就要“对症下药”,先检测外覆物的性质,再采取相应措施。处理白化的玉器的外附物质时要格外小心。

有外覆物的出土玉环(新石器时代)
第二种修复工作针对残断的玉器,使用稳定且可逆的粘接剂将玉器重新粘合。
第三种修复工作叫 “补配”。“我其实不大赞成这类修复。”因为文物修复的原则是“尽量保持原样”,这种“原样”也包括文物本身的破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这些有着自然断口的文物给文保工作者提供了认识文物内核的宝贵机会。”许多白化的完整玉器从表面上无从观察,但是却可以从断口发现端倪。王荣老师认为,大可选择保存相对完好的文物进行展出。
第四种修复工作是针对白化异常严重的玉器,需要首先采用合适的加固剂对异常疏松玉器进行渗透加固,这种抢救性的修复保护工作要符合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可辨识性、修复可逆”的原则。
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便是“预防性工作”。王荣老师向我们展示了同一玉器在2007年和2011年的照片,在此期间,该玉器一直被保存在博物馆。但短短四年内,它整体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白化。这说明,我们现行的指导意见中提及的文物保存条件并不完全适用。
2011年王荣老师在试验中发现,玉器文物真正的适应保存条件和传统熟知的保存条件存在偏差。这可能是因为汉代以前的玉器质地多样,有的比较疏松,易受白化影响,与汉代以后质地较好的和田玉的适应条件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类玉器数量巨大,因此从事预防性工作的相关研究相当重要。
一方面,通过预防性工作了解玉器损坏的原理,有助于修复工作;而修复工作可以为预防工作提供线索,二者相辅相成。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修复工作,仅仅是文物保护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出来怎么让文物长久地保存下去。” 因此,全国文保工作者都格外重视根据玉器特点、制定相应保存条件的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
地大物博,人文荟萃
文博专业的研究往往是各学科交互的成果。王荣老师很喜欢复旦文理交融的综合学术环境。常说“隔行如隔山”,而在文博,不同的研究方向往往是天壤之别。不同方向的文物研究,可以和物理学、化学、地质学、艺术史等多个学科共同交叉。“我是理科背景出身,就特别喜欢和文科同仁打交道。我很喜欢他们大开大合的思维方式。”
中国地大物博,文物资源丰富,进行大工程项目时,通常会请考古队前去勘探。国内考古的环境也相对宽松,资源充足,给予研究者以充分的实践机会。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国家层面上也给了考古研究项目许多支持。事实上,中国考古的发现数量和质量已然是轰动级了。

河南安阳殷墟工作站
“我觉得我们国家研究水平挺高的,我们不要妄自菲薄。”王荣老师说,“西方很多研究者都很羡慕中国,因为国外很少有像‘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样国家层面上的大考古项目。”
“你会发现现在的研究者关注到各个领域,有些前人根本无从涉足。”比如说,现在有学者会研究古代人的排泄物,以了解他们的饮食与健康状况。“现在很多年轻学者研究一个点时都会钻研得很深,我觉得国内研究环境真的挺好的。”王荣老师对于中国文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文博事业作为关照人精神的事业,在当今社会需求量很大。然而中国地大物博,并且由于文保工作的特质,必然面临着行业内部精英化的要求,因此难以大面积招生,国内文保工作面临着人手不足的困境。
“虽然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如果有更多来自不同专业的人才加入文博,我们还可以变得更好。文博系欢迎来自任何学科的对文博事业有兴趣的同学。”王荣老师笑着说。
“含耀且流英,灵韵亘古长”
如同《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所说,文保工作者要时刻保持一种“历史中的纵深感”。文物的传承是长久的,每个文保工作者不过是时间的漫漫长河中的小小一环。这份饱含责任感的初心必须贯彻文保工作者的整个职业生涯。
就像王荣老师所说,通过修复文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心存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在那时候,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文物中挖掘文物背后告诉我们的历史故事,每个人能够通过文物获得对历史和人生独特的体会。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地保护好每一块玉、每一幅画、每一尊像。

通过文物,创造者和观赏者得以跨越时空进行对话。文物背后,镌刻着一代代文物保护者漫漫的生命时光。通过它,你能了解一个人,甚至一个时代。
除特别标注,文中图片均由王荣老师提供
江依梵 费美林 蒋依伶丨记者
赵凯慧 尤彤瑶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