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君诺·简介:
潘君诺(1906—已故)江苏镇江人,名然,中国美协会员,擅作花卉草虫。幼年家境贫寒,辗转至扬州就学。由于环境影响,少年时就酷好美术。初临石印画谱,后于裱画店见诸多名家真迹,遂背临所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于扬州画派有所了解。年十五六,过秦更年宅,见案头有一空白扇面,即挥毫为作花卉,掷笔即去,更年见而大异,之后若干年,君诺竟为花卉高手。
幼年家境贫寒,辗转至扬州就学。由于环境影响,少年时就酷好美术。初临石印画谱,后于裱画店见诸多名家真迹,遂背临所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于扬州画派有所了解。年十五六,过秦更年宅,见案头有一空白扇面,即挥毫为作花卉,掷笔即去,更年见而大异,之后若干年,君诺竟为花卉高手。1930年就读于上海美专,专攻花卉草虫,临摹了大量宋元工笔花鸟画及近代任伯年、吴昌硕、王一亭、齐白石等名家的作品,并对青藤、白阳、石涛作品的意境和笔墨进行研究,艺大进。美专毕业后复受业于赵叔儒、郑午昌。叔儒弟子凡72人,以符仲尼杏坛之数,其中陈巨来入门最早,徐邦达今最着名,潘君诺为关门弟子。黄蔼衣、郑午昌之花卉,有时由潘君诺为之。花鸟画外开始进行草虫的研究和创作,并自署“演雅楼”、“虫天小筑”,表明他在草虫方面的抱负。
二十世纪海上画坛风起云涌,山水画花鸟画各领风骚,潘君诺先生作为海上画坛的一员,尽管后半生境遇坎坷,可他的艺术瑰丽多姿。公平地看待潘君诺,称他为近代花鸟草虫画大家,应该没有异议。
潘君诺,江苏丹徒人,又名潘然。少时喜好涂抹初露聪颖。上世纪早期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了十分正统的规范的学艺生涯。他治学严谨,广泛涉猎宋元明清名家山水花鸟草虫画,练就一手好字、好画。他仰慕赵叔孺的学养,诚惶诚恐拜其为师。那时候的花鸟小品业已显现潘君诺的才情才华。转而师从郑午昌,因循着自己的志向,遇到范畴的扩大化,趁年轻广学博取。潘君诺在郑午昌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在中国绘画进程发展史上,山水画是以宏大的胸襟为目标的,气韵心境在山水之间忽然开朗。而潘君诺学山水想借鉴山水画中的笔意蕴涵,为自己的花鸟画创作增加养料,拥有大胸襟。潘君诺以绘画为职业生涯,在三四十年代纷繁的海上画坛,画艺日进崭露头角,很快融入主流社会。花鸟草虫画趣味鲜特,游刃有余,大幅尺牍有声有色,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他的润格颇高,名列鹿台仙馆入室弟子之首。曾听朋友讲述,刘海粟夫人夏伊乔问起那时画花鸟草虫谁为首推,刘海粟毫不犹豫地讲:“当属潘君诺。”日后据说托人请潘君诺画了一套册页,并作为夏伊乔学习花鸟画时的摹本,可见潘君诺花鸟草虫画的影响力。当时获知堂堂刘海粟校长求画受宠若惊,并十分认真地很快完成了,显然潘君诺的艺术成就在前半辈子是凸现无异的。
进出画院
有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查找有关资料记载,五十年代上海中国画院成立时的大名单中,清清楚楚有着潘君诺的名字。细细想来,已过不惑之年的潘君诺绘画成就与其社会地位相符,生活应该是平淡安逸的。以平稳心态抒写着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可感情韵,憧憬着美好未来,在完美上做好做精。潘君诺个性温和风流倜傥,出言幽默。不光在花鸟草虫画上造诣颇深,而且会当“大像”,就是现时称谓人物写生。听许多曾经给他做“模特”的老人后辈们讲过,他的画像形神兼备,问题是他的白描功夫好生了得,让人读了啧啧称奇。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几乎没有查阅到一件存世作品。在上海中国画院成立之初,潘君诺的热情和兴奋是难以溢表的,被聘为首批画师更让他彻夜未眠。每每有雅集聚会,有潘君诺参加则合座尽欢。可惜的是这样祥和融洽的日子短暂地过去了,画家的命运是不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随着阵阵风暴降临,本来就脆弱的潘君诺,他的归宿前途霎时变得渺茫无助。看来他是无力支撑了,头戴几顶“帽子”悄然凄楚地离开了画院。他的前后半生的遭际就是这样荒唐跌宕。从潘君诺现象来说,悲凉凄苦的生活,对人生对艺术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假如当年他没有离开画院,那么将是怎样的潘君诺和他艺术展现在人们面前呢?事实确切地证明,遭遇不测的潘君诺迅速从江湖上湮没了,人们也就渐渐地把他淡忘了。虽然潘君诺并未停止他钟爱的绘画,只是再也没有露头的机会了。
陋室怡情
从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终,潘君诺在海上画坛消失后,在干什么呢?画家的心思,不会在吃尽老本的基础上求生存的。他终日足不出户,躲在万航渡路简朴的居室里,好像摆脱了一切尘世纷争,反倒心情平稳了许多。但是,面对不断严酷的现实,人的求生欲望就会显得特别强烈。潘君诺在画室兼卧室的逼仄情形下,学会了调剂时间,白天画画,完成后即在房里拉一根绳子挂上,静坐观赏,是他唯一的心灵空间。生计来源靠朋友介绍有志青少年到家里教授中国画,按每次收费5角,并当场画一张课徒稿送学生回家临摹用。我们现时能够读到的作品大多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从花鸟草虫到山水小品,看得出潘君诺落魄后的无奈和沉寂,心态的微妙奇异导致他反而更加落拓明净,画出的画旧气新韵兼容,着实掩盖了他的郁闷和不安。当然也有昔日旧友暗中接济,如编造个美丽的谎言,说有朋友欲求册页之类,出资一元一通。于此,潘君诺总会把价格降之再降。生活窘迫潦倒的画家,被发落到社会底层的一介书生,真是难为他了。实实在在的清苦到了极限,买不起国画中的主色花青,竟动出脑筋到中药房购买一种叫“青黛散”的中药来代替,画出效果不能同正宗花青媲美。然而,潘君诺却在他身后几十年依然活着。苦难时期的花鸟草虫画是琳琅满目寓意悠远,大开生面,笔端始终洋溢着生命活力。
淡然余辉
潘君诺的人生沉郁孤寂直接或间接成就了成为大家的基石,我们无需去责怪这样那样,相信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是金子总会发光。潘君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只是时间问题。记得在他黯然去世若干年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潘君诺画花鸟草虫小画集》出版。虽是一个稍为迟到的信号,可以预示潘君诺的艺术是有读者和市场效应的。前些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拟出《上海美术全集》,苦于没有潘君诺作品,东找西找总算在一位藏家手里,发现一册品相内容画艺俱佳的十通精品,有荔枝蝉鸣、柿子蜘蛛、芦荻蜻蜓、葡石蟋蟀等等,基本上能涵盖他的创作思路和精神内核,乐得编辑们喜极而泣。《荔枝蝉鸣图》与《鸡虫得失》造入全集,严格地讲,填补了上海近代美术史的一个空白。其实所有画家有一个共性,是传承传统还是有所创新,艺术上的成功不能同现实生活的渊源割裂开来。坎坷与不幸、沧桑与历练恰恰是生命中非常沉重的负担。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绘画就是做梦。潘君诺因为有梦,苦涩的生活变得如此充裕,原本窄小的心灵变得如此宽厚。真的,我们用他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甚至鼓励我们用他的经验来拓展自己的精神边界,仿佛我们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
以绘画为一生的潘君诺当然知道他会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潘君诺到死也没有加入美协,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大家,艺术家塑造的物象是生灵,而艺术家自己就是纯粹之至的生灵。明明白白做人,面对潘君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倏忽间想起这样一句话:“年代是一小片岁月,它的珍贵在于关于它的尘埃或许已经落定,而人们对于它的怀念,依然缤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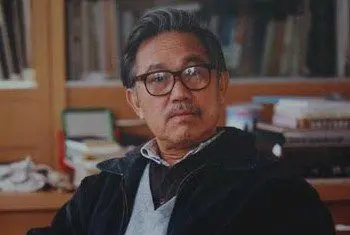









![[湖北] 湖北美术学院 艺术类院校名录 [湖北] 湖北美术学院 艺术类院校名录](/file/imga/small17204056198405971720405888.png)
![[辽宁] 鲁迅美术学院 艺术类院校名录 [辽宁] 鲁迅美术学院 艺术类院校名录](/file/imga/small17204036232733221720403719.jpg)







